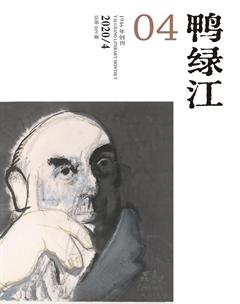江边上(短篇小说)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秋天一个阴暗的日子里:
吃过晚饭,想到隔壁的小店里去坐一会,顺便向掌柜和店客打听打听这两天桦甸县城里,日本人活动的消息。刚跨出房门,就看见一个人影在学校院墙外边,向里面探头探脑地望着。这样子,很使我怀疑:“是来侦察我的吧?!”我站在台阶上,定了定神,然后,大声的问:
“谁?”
被我这一问,就再也没有影子了,我想也许是被我吓唬跑了吧?这么一来,我的胆子倒似乎也壮起来了,我倒想要看一看这是什么人才行。因此,不容分说,我马上走下了台阶,迈开大步向着大門口走去,我打开校门侧着脸从门口向外望了一眼,在黑暗的门边,一个穿着绿上衣白裙子的朝鲜姑娘站在那里。
“刚才是您在墙头上向里边看吗?”
“是我。”朝鲜姑娘看了我一眼,局促不安的用中国话回答说。
“你找谁?”我立即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一种热切的焦灼的神情,于是就紧接着问一句。
“我找——你……你是这学校的于老师?”
“我?”我打了个顿,马上转了一个念头,接着回答说:“不是,我姓杨,你这么晚找于先生干什么呢?”
“我找他——……”
朝鲜姑娘叫我这一下问的窘住了,她用眼睛打量又打量我,半天回答不上来,最后憋的实在没办法了,她才不得不说了:
“不是我找他,是我爸爸让我来找他,我爸爸认识他……”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有点诧异了。但我有意克制着自己,不动声色地问她说:
“你爸爸认识他?你爸爸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呢?”
这一连几个追问,倒把这个大约有十八九岁的朝鲜姑娘问烦了,她低下头用眼睛看着挎在胳膊上的筐子,然后用十分不高兴的声音说:
“你看你这个人……这干你什么事……你总这样问来问去干什么呢?人家又不是找你,请你躲开门,让我进去!”她说着,就向着我身子旁边挤过来。
看她这么急,我也就有些急起来了。从她脸上的表情,和眼光看来,确是不像一个怀有恶意的人,我一边在心里想,一边把身子躲过来,等她走进学校院子以后,我才把她叫住了。把我的姓名告诉了她。
“你就是于先生吗?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呢?”她像非常抱怨似的说。“我爸爸让我来给你送个信,”她向四下里望了望,小声地说:“今个下晚,日本人到学校来抓你,你得赶早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屯子,越快越好。”
“你爸爸让你来的?可是——你爸爸是谁呢?他怎么认识我?他怎么知道日本人要来抓我呢?”
“你别问这个啦?快吧!快点把要带的东西收拾一下,我爸爸说你一定得在点灯离开这个堡子才行。”
“你不要和我开玩笑吧!我又没犯什么罪,为什么会有人来抓我呢?你不说明白我就不能相信你的话。”
朝鲜姑娘看我这样固执,似乎感觉有些为难了;但她抑制着自己不使露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最后,她严厉的用责备的口吻说:
“你这个人真太不近情理了,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信,你却总是盘问来盘问去的。好,这么的,咱就告诉你吧,你赶快把你藏在房后大树窟窿里的五颗手榴弹都拿出来带着走……这回你该相信了吧?”
我的秘密,一下子全被她戳穿了,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发了一会愣;但立刻我就感觉我和她中间的关系起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我感觉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刚才那个朝鲜姑娘了,而是和我们一道战斗着的一个亲爱的同志,马上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温暖的亲切的感情,但因为当时她催的我很紧,不容我细问,也不容我捉摸这些了。可是,我往那里去呢?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日本鬼子一定把我们全部夺取区公署武装的计划都探到了,显然到附近村子的小学校里去找那两个小学教员的同伴也是很危险的。这当中也许有人出卖了……我一边沉思一边在院子里打着转,朝鲜姑娘看着我迟疑不决的样子又连忙说:
“你还犹豫什么呢?眼看着天已经黑了,再晚了,恐怕就走不出去了。”
我把我的困难告诉了她,她沉吟了一下,然后就很慷慨的对我说:
“好吧,你实在没场去,今晚上就到咱家去躲一夜吧。”
“你家住在那里呢?”我突然像得了救似的惊喜地问。
“离开这三四里路,就在江边上——一个小打鱼棚。”
“鬼子不会到那里翻吗?”
“翻的时候再说,我爸爸把救你的任务交给我了,我无论如何——”她没有再接着说下去,停一会就用命令的口气说:“你赶快把你要带的东西收拾好,不能带的东西藏起来——马上跟我走好啦,咱们一前一后,你不要离我太近了,能够跟上就行……去收拾吧,我在街上等你。”
她说着,一转身就走了出去。
天黑以后,我跟着这位朝鲜姑娘一口气走了三里多路。朝鲜姑娘走在我的前面,头连一回也不回,把我拉得很远。我因为背着我那五颗宝贝,加上几件衣裳,简直就赶不上她。我心里真有点不好意思,却又止不住暗暗地埋怨起来:“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近人情?”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又怕她把我拉下,因此,也只好拼命的追她,但是就是这样撵,我们当中总还是保持着一个相当距离。她好像故意和我开玩笑似的,但,我却从没有看见她回过一次头来看看,这也是事实。
走着走着,越走天越黑,天越黑路也就越看不见,我跌筋头绊脚的跟着她越走越累。不,这简直不是走路,而是跑路,跑得连口气都喘不上来。脑门子上出汗了,跟着背着手榴弹的脊背也出汗了。我心里想:“这是见的什么鬼,她到底领我到哪里去呢?”我有些后悔,为什么当时不问个青红皂白,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跟她来了呢?假使这是日本特务摆的圈套,那自己——不是白白的给送到老虎嘴里去了吗?自己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怎么叫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一说,就信以为真,一点都不怀疑地跟着她跑起来了呢?我越走越感觉不对劲,末了,我高声叫喊着说:
“喂!你站一会,等一等,我有话跟你说。”
“你有什么话说呢?再走就到了,到地方再说吧!”黑暗里,我隐约地看见她回了头,话一说完,马上就又把脸转过去,向前走了。
“不行,快到了也不行,我不想再跟你走了。”
这下子真好使,她不但不往前走了,并且马上就抹回来,走到我的跟前,问我说:
“怎么样?于同志,你是走不动了吗?”她没有等我说话,就又接着说:“是不是你背的东西太沉了,来,我帮你背着!”
“不,不沉,我背得动。”我听她叫我一声于同志,心里唰的一下子,好像从那里搬出去一块大石头似的,立刻轻松了很多。这两个字当时对我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在我来说,只有我们那几个情投意合想干一番事业的朋友,在私下开会商议点什么事的时候,才偶尔这样的称呼一下,想不到朝鲜姑娘却用这个来称呼我了,这对于我真有点突如其来,而且她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真挚,那么出于至诚,因此存在我心上的疑团立刻都消逝了。
“不累,不累,我能拿得了,我想问你,还有多远才能走到呵?!”我不愿露说出我那种胡乱的想头,因此就假意的应付的说。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再走一会就到啦。”
“是吗?再走一会到哪里呢?怎么还看不见呢?”
“等你一看见,也就到了,我给你背一会吧,你不想找抗日联军吗?这可是机会呵!”她一边走着一边和我说,好像我的什么思想都被她看穿了,这一点真使我感到奇怪,她接着更关切的告诉我说:“我知道你有点怀疑,可是现在还是走路要紧,你为什么不做声呢?想什么呢?这时候你的学校恐怕让日本特务完全抄了,你也许现在还不信,可是日后你总会知道的。还是要快走呵!再迟了这条道路上也会危险,那时候就糟了。”
我听了她对的话,心里真是把一百二十个信任都给她了。这样一来,脚也有劲了,就使力的跨着大步跟定她向前走。
又走了一会,我们来到一个柳树丛很浓的地方,突然从前面不远的处所,出现了一个火亮,红光一闪一闪地,我想这一定是鬼火。孩子的时候,听讲的一些鬼的故事,在脑子里常常作怪,直到长大起来,虽然知道事实上没有鬼这个东西,但在黑夜里一提到这些总有点忌讳,而且要是黑灯吓虎的一个人走过坟圈子,也总有点胆悚的。这时节,我到没什么,因为还有朝鲜姑娘走在我的前头。我只感觉脸上和身上有些凉飕飕的,我睁大了眼睛看着火亮,听着仿佛有人在吹口哨。是的,是口哨,很清亮的声音,接着。我听见走在我前面的朝鲜姑娘也吹起来,我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江边上,怪不得我越走越感觉脸上和身上都有些凉润起来。
“毛丫头,你咋才回来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用次中音说,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从这声音里,可以使你感到这是一个心地朴直的人。他还没等他的女儿回答,就朝着我说:“怎么,于老师到底一块来啦,没出什么岔子吧?!”他亲切地招呼着我,就像我自己的什么亲人一样。
“没出什么岔子,就是于老师……他总不大相信我,耽误了一下……”朝鲜姑娘望着我笑笑,给我介绍说:
“于老师,见见吧,这就是我的爸爸。”
“老大爷,多亏您打发您老的姑娘给我送信,我一下子没处躲藏,就和她一起来了,这行吗?对您老没什么危险吗?要有些不便当,我就在半拉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蹲一晚上也可以,别连累您老人家——跟着我……”
“这,这,于老师,你说到那里去了,走吧,到窝棚里去……说起来咱们是见过的,我认识于老师,于老师可没有注意我……”
“在什么地方?”
“就在达连屯黄老师那里?”
借着从江对面黑黝黝山岭上升起来月亮的光线,我看清楚了这位站在我前面的朝鲜人,中等身材,穿着朝鲜人平常的服装,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我端详了半天,突然,记起来了……
“哦!你是给他煮过饭的那个金仲山吗?”
“不错啊!于老师你的记性挺好!”
“不,我……”说到黄振刚我再也不能说了。“金大爷!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们两个人呢?你快告诉我吧!”
“你别急,年轻人,他们都疏散了,日本鬼子这一次想一网打尽。可是却一个也没抓着,这是我们情报知道得早,一点没受损失,你们的计划,听说全部都被日本鬼子知道了,说起来长了,咱们到窝棚里边去唠吧!”
那里是窝棚呢?在这个时候,在月光底下,我才看清在我前面不远地方土岗上的一个像高粱船子的打鱼窝棚,金大爷走在前头,我跟在后边,那引我的朝鲜姑娘早在我和金大爷说话的时候,就走不见了。
窝棚里黑漆漆的,那位引我来的姑娘看我们进来,就赶忙把墙台上面的一只小油灯点着了。窝棚里看上去是很窄小的,除了一面大矮炕和一个锅台,简直就没有转身的地方。金老大爷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似的让我坐在炕上,然后十分亲热的和我唠起今天发生的事情来。
“我在烧晚火的时候,才得到这个消息,当时我很着急,怎么办呢?你们有三个人,而我只有父女两个,要在天黑以前把事办好真是很急哪!我就和我女儿商议,让她到你那里去。因为离区公署近。我去给黄先生送信,让他再通知李教员去,我回来的时候,黄教员已经走了,这样他们今天晚上就完全扑空了。”
“金大爷!你怎么听来这个消息呢?这件事情一定能可靠吗?”
“这,我不能详细告诉你,也许等不到明天你就会知道这是可靠的了!”
“明天。明天,我怎么办呢?金大爷,你说我到那里去呢!”
“你不是早就有心找抗日联军吗?从这过江下游不远的地方,听说有他们一小队在那里打游击,你要去,我倒是可以送你去。”
“好!那可真是再好没有的了。”
从他这几句简单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懂得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的态度是那样纯朴,那么沉着,对人那么亲切,说起话來那么有分寸,而讲起日本人,又那么充满仇恨。怎么看怎么像,我在心里想,他一定是个共产党里的人。我过去听人家说过共产党员如何革命,如何不怕死,如何神出鬼没,如何沉着勇敢等等……我为一种年轻人的好奇心所牵引,很想追问明白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终于在谈到别的问题的时候,我有意岔开话头,逼紧了一步问:
“金大爷!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你问我吗?共产党不共产党现在都一样,共产党反对日本人,不是共产党的也要反对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都一样,反正在日本欺压下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你不必再问了,你以后慢慢会知道。”
“这位先生就是喜欢追根问底。老象是信不着别人似的。”那位朝鲜姑娘,取笑着说,向我瞅一眼,然后又转向她爸爸说:“爸爸,你没有看我到学校给他送信的时候呢,他就是不信,一定要追问你的名字,追问你在那认识他,我又不敢说,怕一说出来,他说不认识不就更麻烦了,逼问实在没办法,我才叫出手榴弹来,我想这样他一定肯信了,结果真是这个办法好使……”
“应该是这个样子呵,应该问个明白。”金大爷慢慢点头说:“日本鬼子是狡猾万分的,你一不小心就不行,这叫做警惕性呵!没有这样本领就是不能干革命工作呵!就拿这次事情说,到底从那里走露了消息,现在还没弄明白,以后还要更加小心一些才行……”
这时我突然想起我还没有请教这位朝鲜姑娘的名字哩!但,事到如今,也好像不便再问了,我踌躇了半天,终于问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才对呵?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那五颗手榴弹搁在房子后面那棵大树窟窿里的呢?”
“她叫金小凤,你以后叫她凤子好啦!”金大爷代替他女儿介绍说。凤子也赶忙地接过来说:
“你问我怎么知道的呀?”她又向我看一眼,笑了笑说:“中国不是有句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吗?不过我从哪里知道的我也不想告诉你。”
“算了吧!别唠这些了。你去安排安排,咱们都睡下吧,明天一早起五更还要送他过江去呢?”
我很想留恋这个夜晚;很留恋他们父女对我这番好意;很留恋这晚上映照在江上的月色。我那时已经把刚过去的危险忘记了,对于明天如何我也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只感觉这一切对我都非常新鲜,非常富于传奇性的意味:在这样一个江边的小窝棚里,对着这样两个人——他们是不同于寻常人,他们的谈话和举动行为,都让我生出一种景慕的感情,我想我如果能像他们一样,和他们这种人在一起,那就是我一生当中的最大的幸福了。我想着想着,不由地困倦起来……
刚合上眼睛不大时候,就听见窝棚外面有人敲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被惊醒了。
“金大哥,金大哥!”声音是十分急促的。
“来啦!”
金大爷蹑手蹑脚的走下地,好像怕惊醒我似的。没来及点灯,借从窗户上透进来的朦胧的月光,走去开门。
“是谁?”我爬起来问。
“你躺着吧,不要紧,是自己人……”
金大爷悄嚒声的说。这时凤子姑娘也醒过来了,她好像很习惯似的翻身坐起来,一言不发。
门打开了,一个人从月光照耀下的外面钻了进来。我从他们的穿着衣衫的轮廓,立刻便认出来是一个朝鲜人。他一进到窝棚里来,就用朝鲜话和金大爷啦起来,我虽然听不懂,但我从他喘吁而又急促的声音里,听出他们说的是有关于我的事情,而且看上去好像危险马上就要到来一样。
金大爷听他说完话,就一挥手,不知让他干什么去了;而他自己却像思量着什么似的,一直没做声。我这时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就咕噜从炕上跳下来。向金大爷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和我有关系你也和我说一下呀!金大爷,你老也别难心呵!”
金大爷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要慌,听说你们俩出来的时候有人看见,说是日本鬼子朝着这一带搜过来了。”
“那让我走吧!省得连累你老人家。”
“走,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这大月亮地,一看老远,你往那里走恐怕也走不出去,沉住气,年青人,事到临头不要乱了脚步,敌人就盼着咱们这样。”
“那可怎么办呢?金老大爷!”
我真有点急了,因此说话的声音也大起来了。
“于老师,你别着急,他们真要来咱们还有办法对付,就是要冒点险,事到临头,也只有这样了,你沉住气好啦!凤子,你赶快下地把柴火堆收拾收拾。”
金大爷像怕我着慌似的,直劲用话安稳我,当时我实在是心急的不得了,看着凤子姑娘跳下地,就扒到锅台后边柴火堆里边去了。我也看不出他们父女要怎样安排我,我就像一个等着揭盖头的新媳妇似的站在屋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沉重而又急促的脚步声从窝棚外面传来,接着,门被推开了,一个人影冲进来,看得出还是刚才那个朝鲜人,他急切的用朝鲜话说了两句,我感觉出来他是说人已经走来了,还没来得及问,金大爷立即就翻译给我说:
“他说日本鬼子已经从三面包围上来了,柴火堆下面有一个地窖,你带着你的东西先进去躲一躲,避避风头,凤子,你也下去。”
“我?”
“是的,你带着于老师下去,我和你二叔在上边,省得麻烦,快……”
金大爷命令地说。
我等凤子下去以后,才弯着腰下到地窖里边去,把金大爷留在窝棚里,我真的有些放心不下,我不知道他将要遭遇到什么,日本鬼子会因为我而特别拿问他的。因此,当他要盖地窖盖子的时候,我真想让他也躲藏起来,但,没有等我说出话来,他就拍的一下子把盖子盖上了。随后我就听着一阵土和柴火沙沙的声音,我没有离开浮盖地方,我用耳朵贴在盖子旁边凝神的,听着上面。不一会工夫,一切都静寂了。
“你往里边来一点,那靠盖的地方太低,连我都直不起腰来。”凤子姑娘说,用手拉了我一下。
“没什么,我想听一听。”
过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就听见了打门的声音,像擂鼓似的越来越猛烈,這是用枪把子和皮靴击撞在门上了。接着我听见金大爷好像刚从炕上扒起来的样子,大声答应着,点着灯,下了地。门打开了,很多人拥进来,皮靴咯咯地踩着僵硬的地面,就在我的头上踏的直响。听不清楚的话声,咿哩喔啦的日本话,好像是叱责怒骂,当中还夹着朝鲜语,像在审问似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像是发疯了的样子。
我的心不住的跳,跳得很厉害,我很为金大爷他们两个人担心,只听见日本鬼子在叫嚣,却没有听见金大爷回答什么。我的两眼迷黑,地窖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凤子姑娘紧靠着我坐着,我们几乎完全屏住呼吸,共同地担心着那在地面上进行着的查问和搜索。
“怎么听不见金大爷的声音呢?他们把他拉到外面去了吧?”我悄悄地向凤子说。
“你别怕,爸爸是不会怕他们的,你安心好啦。”
果然,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不是用中国话,而是用朝鲜话说的,我一样也听不出他说些什么,但他的声音很大,是一种一点也不怯懦,理直气壮地强硬的声音。我不由得从心里生出了一种敬意。
“是爸爸答复他们了。”朝鲜姑娘说,“他们压服不了他的。”
凤子的话刚说完,我就听着地面上的声音有些不对了。日本鬼子高声怒骂起来。“不打他不能说实话。”一个人大声的喊叫说。
“我没藏就是没藏,你打死也还是没藏。”金大爷用中国话反抗着说。
“你敢抢嘴!”啪——啪,是手打在脸上的声音。
我这时候有些忍耐不住了,我想马上跳出去,用我带着的手榴弹把他们一下子炸死,省得连累金大爷。凤子姑娘好像了解这种心意,她用手紧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动一动,地面上殴打的声音还在继续着,但却听不见一点呻吟和呼叫,我心里真是难受到万分了。“使劲给我打,看他叫不叫,多喒打叫唤了多喒住手。”噗咚一下子,给人摔倒地上了,接着是更剧烈地拳打和脚踢。但是,我还是没有听到金大爷发出一点声音,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决然地对凤子说:“让我上去,这样下去是会把金大爷打死的呀!”“你不能出去!不能向敌人屈服!爸爸是不怕他们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人是不怕折磨,不怕死的!死都吓不住我们。难道打能吓住我们吗?”
仍是没有声音,连一点哼声都没有。殴打虽然仍在继续着:但从声音上听起来已经显得非常无力了。过一会,像轮到另外那一个朝鲜人的身上了。同样是斥责,叱骂,审问,但也同样毫无结果。末了,他们就在窝棚里乱翻一阵,有人用皮靴和枪把子在屋地跺着。有一回一个人走到柴火堆上來,并且用刺刀向柴火堆挑了两下。但他立刻就被叫到了别处去了……他们这样足足闹腾了有半个多钟头,实在有点没什么趣味了,才像一窝蜂似的走掉了。
我听到最后一个人走出去的时候:用很大的声音威胁着说:“金老头,今天便宜你了,我可告诉你,你要把这个窝棚给我拆了,不准你在这里住下去,三天以后要是不拆,我就让人来把它烧掉!你听见了没有!”
没有等到回答,皮靴声咯咯地踏着硬地,走出去了。
屋子里静默了好一会,没有一点声音,这一会的工夫,对于我简直是不可忍耐的长久。我恨不能一下子跳出去,看看金大爷被打成什么样子。我想喊叫,但是我又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形,日本鬼子、特务、警察是不是已经全走了,也许他们会留一两个人在附近监视着,因此,我只好耐着性子等着,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声音,我怕的是他们把金大爷和另外那个朝鲜人都打的不行,打的没气了呢?如果真的这样,老是等下去也是不行的。我把我这一个想头如实的对凤子姑娘说了,她仍是阻拦着我,不许我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听她的话。这样一直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听见金老大爷喘了一声,然后两个人就一问一答地用朝鲜话说起来了。凤子姑娘把她听清的一些讲给我时,我才知道,是另外那位朝鲜人到外面去挨着排看了,他们在推测日本鬼子特务和警察因为害怕一两人留下有危险,所以就全部走了。我听见凤子姑娘这样说,我一下子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提高嗓子从盖子向外边叫着说:
“金大爷!快把我们放出来吧,我们实在憋的不行了。”
从地窖里爬上来,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金大爷,我像什么都顾不了一样的立刻走向他。他这时已经被打的不能动了,但却还挣扎着站起来,扶着墙走到炕上去,我一下子摸到他的前面,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他的脸被打肿,红一块紫一块的,鼻梁被打青了,血从鼻孔流出来,脑门子被打破了一块,渗出血滴来。我拉住金大爷的手,眼睛不自觉被泪蒙住了,十分难过的说:
“这都是为了我,金大爷!你为我受苦了。”
“这不是为了你,年青人,你弄错了,这是为了反对日本人呵!”
我站在他面前,还想说些什么话来表白我的心意,安慰安慰这个老人,但他不等我开口,就向我介绍了另外那位朝鲜人:
“于老师,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朴永烈同志,这位是于老师。”他介绍完毕之后,接着就对我说:“这地方还是危险,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还会来,我建议你连夜从下游过江,到那边赶过二三十里路,天一亮就到山里去了,那些地方虽然特务活动不怎么厉害,但白天走恐怕还有危险,不如夜里走好,我不能送你,就让朴永烈同志摆船送你过江……你必须马上就走!”
金大爷的脸色非常严肃,从他那里找不到一点伤痛的感觉,这会,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他为我受了这样残酷的毒打,折磨,我难道一点都不……我怎么忍心离开他呢?可是我又不能说我不走,因此,只好答应了他。
当我背起我的包裹从小窝棚走出来的时候,他忍着疼痛爬起来,把我送到门外,我不由地挽着他的胳膊哭出声来,我对他像宣誓一样说:
“金大爷,我这一生也不会忘记你,你对我这样,我将来要怎样才能报你的恩呢?”
金大爷,抬起头向四下里看一看,然后说:
“年轻人,你不要这样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受日本鬼子压得活不下去,才豁出命来和他们拼!这不是我对你的恩德,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记着我;路这么长,危险是很多的,你也许不会碰见我了,可是人民是不死的,你记住朝鲜人吧,我们朝鲜人现在和中国人一同受日本鬼子压迫,我们就共同来反对他,和他斗争,将来我们朝鲜人也要和中国人一同站起来。记住这个吧,记住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生死友谊。再见吧!”
我实在太激动了,我不知道说句什么才能表达我的这片心意……终于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握了一下手,就被那个朴永烈同志拥着走下江边。
上船之后,回过头来望着远处的两个高大的影子:金大爷和他的女儿——凤子姑娘。我才想起来,我刚才忘记了向凤子姑娘告别了。我呆呆地坐在船头上,直到他们的影子模糊了,我才转过头来和朴永烈同志说话,并且希望他回去能向凤子姑娘说一声。
一九五零、十一、二十四。
【按照原文重排,保留原样。】
【责任编辑】 洪 波
作者简介:
蔡天心(1915-1983),沈阳人,193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历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员,中共辽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大学教授,辽宁学院院长,《东北文艺》主编,东北文联秘书长,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专业作家、副主席。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大地的青春》《浑河的风暴》,中短篇小说《长白山下》《东北之谷》《初春的日子》《扶持》《蠢动》,诗集《红旗颂》,文艺评论集《文艺论集》,诗词集《晴雪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