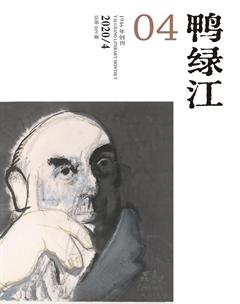赵松,《盒子》(评论)
0
似乎很早之前就“认识”赵松,然而真正安静下来阅读赵松却是最近的事儿。赵松让我意外。赵松是那样不同,面目清晰地不同,他让我偶尔会“想到”另一位居于上海的作家孙甘露。当然赵松的写作风格与孙甘露的写作风格差异性明显。我说的不是模仿和师承的关系,我说的是他们的独特和“孤立”,几乎让你在中国作家中少见同类的那种“孤立”。如果说相似性,我倒觉得赵松的那本《积木书》与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寓言集》有几分相似:那种精致和微妙,那种片断式的集中,那种对语词的敏感和语词里的丰富贮含,那种在头和尾都阔大的“意犹未尽”……说实话刚刚开始阅读的赵松让我着迷,甚至让我“后悔”之前对他的错过。需要说明,“着迷”这个词我不可能轻易地用出,它可是一个必须苛刻和吝啬的词儿。
我想,我会更多地阅读赵松的文字,从现在开始。
1
《盒子》,赵松选择了难度。难度之一,他放弃了惯常的故事讲述的样貌,它不是围绕着故事来讲的,而是围绕着情绪——尽管某种“故事”的因素还暗暗地包含于其中。难度之二,他选择了第二人称,“你”,他在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事实上用“你”来讲述对小说写作难度巨大。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选择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小说众多,而使用第二人称的小说屈指可数,并且成功率极低。为何如此?因为在讲述关于“你”的故事的时候,它会或多或少地遭到作为阅读者的你的轻微抵抗:不是我,我没有,我不这样想,我不……它动摇的是阅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契约关系,如果没有超强的技艺能力你绝无法做到将阅读者带入,让他“身临其境”并“感同身受”。也就是说,《盒子》,赵松要做的是双重冒险,而且是最具难度的那种,或许是失败率最高的那种。他需要,动用所有的能力和手段才能保持住小说的危险平衡。
当然文学需要试错,就像威廉·福克纳所说的那样,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每一次的写作都应面向陌生和冒险,在这里轻车熟路是无效的甚至是无聊的,所谓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但我们也需要承认任何冒险都需要深思熟虑和高超的技艺能力为支撑。
和赵松的难度选择相匹配的是他具有深思熟虑的才华。他做的,比我预想的要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边将自己投入一边又暗暗抽身,猜度他后面将要写到什么,如果交给我来写后面的内容我会如何如何——我身上的作家身份在起作用。我说他具有深思熟虑的才华也正是基于此,我的所有预想要么和他大致不差要么在比对之后略显逊色,他的貌似随意甚至无序的穿插其实包含着精心,他“不讲故事”的故事里其实包含着更为纤细而有效的掌控。王小波谈到《情人》时说过,“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她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她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我的看法则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对于赵松的《盒子》,王小波的这句话同样成立。
我想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层的精心,在结构之外、有意识针对于难度而完成的精心:针对于“不讲故事”可能造成的散乱和无序,赵松强化了情感和情绪的线,他有意让“你”的情绪在其中起伏,抬升或降落,这就形成了和故事同质的吸引力;同时他又有意“陌生”,让叙述在多个国度和城市之间展开,在多个空间时间里展开,这种陌生同样构成和故事同质的吸引力。还有,每一个小章节,故事性因素会偶尔地显现一下,就像隐在海水之下略有露出的冰山,它成为“不讲故事”中的故事辅助,别轻看它的力量。而针对于讲述“你”的故事而造成的契约受损,赵松策略性地做出了有效弥补:一是先由场景进入,让阅读者先进入到他所营造的环境和氛围中,让阅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先建立起身处其中的感觉,这样,阅读中的“抵抗”就会减弱。二是反复的、有效的场景、氛围和情绪描写,它们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能够让阅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并参与、认同,《盒子》中那些略顯盈余的场景描述在我看来实属必要,实属手段,它对阅读者的带入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语言和思考的魅力。它同样构成吸引,构成故事的推进,让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没有因为故事的某种匮乏而感觉疲惫,也没有因为反复对“你”的抵抗而与故事脱出。事实上对于我这样的阅读者来说,最最能吸引我的,最最让我着迷的,恰恰是赵松在小说中所给予的语言和思考的魅力,是它让我生出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期待。
赵松的语言那么纯正。纯正这个词,指的是某种经典的气息。它雅致,丰富,有细细的光泽,耐人回味并且回味悠长。许多时候,我只在某些翻译的经典作品中才能读到它。
2
什么是盒子?
是小说中她所设计的美术馆?是她的那种“默片”的、更多时候交付给沉默的生活?是她内心里可能的、无法探到的茧,还是无可交流、难以真正被领略的内心深渊?是她,在给JOY的信中说的另一重的“爱上”,那重“爱上”强力地拉扯她将她封进了盒子,这个盒子使她更多地拒绝了外面?是她们说的“自然脱落”?她把自己的人生想象成……
“盒子”,是她一个人的意象,还是属于“你”的?还是“你们”所共有的?“你”是不是以默片欣赏者的名义,也将她放进了盒子里?随后的寻找是补偿性的,还是——选择一个更为坚固些的盒子将已经消失的她装入里面?“盒子”,属于记忆还是属于纪念?属于建立还是属于消解?
毫无疑问,“盒子”充满了歧义,也正是因为歧义而充满了可能。在故事的层面,最最明晰的叙述层面,赵松的讲述尽管周折颇多但并不复杂,它在故事层面只是一个关于记忆寻找的爱情故事,用拼贴的方式完成对一个人的多侧面讲述,当然这些讲述依然是碎片的,模糊的,甚至是无法连接的……它在情感层面似乎也并不沉重,与以往的言情小说和时下的网络小说不同,这里的“你”似乎心有止水,赵松写下的这一情感故事似乎有着间离,它更多地作用于健全的大脑,更多的是与人的智性感觉相呼应,而不是叫人泪水涟涟,有某种所谓的揪心之痛。没有,赵松的《盒子》书写了爱情和逝去却没有在情感表述上用力,他始终克制,保持一种间离化的平静,让其中的波澜只有小小的微调。真正复杂的其实处在思考的层面,它的丰富和多意也多寄贮于此……
赵松在小说中布满枝杈丰富的线,这些线,就像一株茂密生长的树,延展着,有着同样丰富的意趣和思考的乐趣。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盒子》的叙述搭建起“她”的基本生活和个人的某些面目,不过我的注意力却不在此或者说并不仅仅在此,我更感兴趣和更愿意在阅读中继续的却是赵松所提供的思考。他们是如何接受一个盒子美术馆的?里面的世俗因素重还是别的?而这个美术馆,对于它的设计者“她”来说又意味了什么,指代了什么?她看重它么?她,真的不看重它么?“盒子”是外化的还是内化的?这里的“设计”是不是还有别的寓意,而“你”的存在又为这设计提供着什么?
“使我着迷的那些小说更多地是因为书中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这正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即:变成以某种方式摧毁我心中批判能力的故事。这些故事迫使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这正是我喜欢阅读的那类小说,也正是我愿意创作的小说。因此,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一切智慧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在小说中出现,从根本上来说,都以某种方式要溶化到情节中去……溶化成可以吸引读者的逸事,不是通过作品的思想,而是通过作品的颜色、感情、激情、热情、新颖、奇特、悬念和可能产生的神秘感。”巴尔加斯·略萨曾如是说。我觉得,赵松在《盒子》中所做的,也正是这样的活儿,正是这种思考的、智力上的丰富埋设,才“迫使”我也跟着说出“着迷”这样的词来。
3
在赵松的《盒子》一文中,飘溢着一种极为独特的艺术气息。这种气息让我沉浸。是的,气息是难以把握也难以用另外的词来精确描述的,但它在,我想任何一个阅读了《盒子》的人都会认可我所说的。气息,它在。
精致,经心,在文字的经营上赵松展示了他的才能,在我看来他的这一才能是卓越的。在阅读他文字的时候,我时常“出神儿”,安静地想一下然后再继续——这种出神儿,只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小说中才能让我如此。它让我不得不偶有停顿,仔细地想一下,回味一下,咀嚼一下。小说中的那种独特气息往往会在这时候更显充沛。
事实上,《盒子》依然有着故事,就像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小说依然有着故事构成一样,只是,赵松有意解开了故事之间的链条,让它们变得松散,移动了旧有位置而已。这里,我看到了赵松的文字把控,也看到了他的故事把控。《盒子》是艺术的,它是一件有着良好质地的艺术品。
我还必须要说,赵松在他的小说里置放了“玄思”,而这恰是《盒子》最为高妙和最可称道之处。赵松有意地推移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而让属于形而上的某些思考借助小说的样貌、故事的样貌呈现,形成小说追问的点。是的,对于《盒子》的思忖不应只止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其实有着更为超拔的审视和追问,它甚至占據着核心,并将可能的爱情故事压在了下面。“也许确实有什么她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但也完全可能并没发生任何事,她仍然可以做出那个选择,就像接受了自己的自然脱落。在她们看来,一个人选择活着还是不活,都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理解,而理解本来也不需要什么因为所以的道理。”小说中说。“你说得对,我是个喜欢随时拆除跟别人的关系的家伙,你说我就像国内那些拆迁办的,到处拆旧的建筑,而且比他们拆得更彻底,甚至都不会去做点说服工作。吊诡的是,我竟然学的是建筑设计,是要谋划建设的。”小说中说。“你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计划,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你自个儿迷失在里面,被那些数不清的照片淹没,窒息……”小说中说。它指向生活的具体,但,更指向形而上的寓意。我觉得,相对于建构一种生活,赵松可能更倾向于建构一种指向不明、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寓意,这,更是他的乐趣所在。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李浩, 1971年生于河北海兴。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作协副主席。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计20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