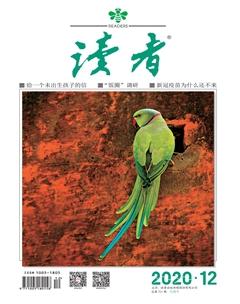夜航船
2020-06-19 08:54王开岭
读者 2020年12期
王开岭

这些年,每当夜色愈浓,我愈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夜晚。
同时隐隐发觉,走水路的时候更多些。
平生第一次乘船,二十三岁。傍晚,背着包,撑着伞,在杭州的運河码头上了船。整整一夜的梅雨,混浊的河水,简陋的堤坝,低沉的马达声,我并不沮丧,一宿未眠,枕旁是明人张岱的《夜航船》,脑子里想着“江湖夜雨十年灯”“夜半钟声到客船”等句子。曙色初现时,我看见了苏州,看见了她的脸。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
第一眼即喜欢上了她。
当脚离开甲板,跨上湿漉漉的石阶时,我留意到了自己“向上”的动作。我很满意这个仪式:我是乘船来的,我是登上她的。
是的,我登临了姑苏城。
我想,许多年前,那些油纸伞,那些长衫客,应是以同样的方式抵达她的:这座城,你须慢慢来,无声地、寂寞地来,在雨天。
这是一座因爱情而繁忙的城池。
桨声柳影,藕花深处,许多清凉的女子,进进出出。
西施、虞姬、叶小鸾、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她们皆踏波而来,泛舟而去。美,适合走水路,旱地太粗粝。
她们是文学和时间的恋人。
凡美,无不以悲剧存档。
爱情教人幸福,但它让人快乐吗?不,它只是在事后看来,在阅读者看来,仿佛有一种快乐。爱情在其大部分时间里,乃是一种生命凌乱了的状态,一种眩晕、刺痛和折磨,类似于疾病。
爱情的降临毫无逻辑,仿佛一朵杏花,从高处坠落,你刚巧路过,被砸中,不省人事。
男女间的亲密有两种,一种拥抱了皮肉,一种拥抱了骨骼。在线装小说里,在深夜古琴声中,在苏州评弹、昆曲唱腔间,你常听见骨骼撞击的声音,像玉碎,让人痛彻心扉,隐隐动容。
真正的爱情,参与者稀少。大部分人只是观众,一辈子偷享别人的故事。
猜你喜欢
意林·少年版(2020年21期)2020-12-10
疯狂英语·爱英语(2020年5期)2020-10-23
摄影与摄像(2020年11期)2020-09-10
摄影与摄像(2020年11期)2020-09-10
扬子江(2019年6期)2019-12-02
时代英语·高一(2019年4期)2019-08-27
东坡赤壁诗词(2018年6期)2018-12-22
东坡赤壁诗词(2017年3期)2017-07-05
视野(2017年12期)2017-06-30
诗林(2016年5期)201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