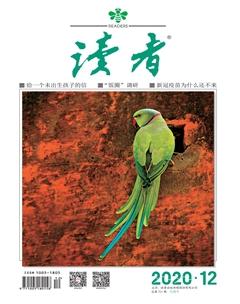塬下写作
陈忠实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得,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一九九一年腊月二十五日的下午。在塬下祖居里专业写作的生活过了将近十年,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习惯了和乡村人一样用农历计数时日,倒不记得公历的这一天是几月几日了。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意味的冬日下午。在我画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眼前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我坐在小竹凳上一动也不能动,是挺着脖颈木然呆坐,还是趴在摊着稿纸的小圆桌上,已经不记得。待到眼睛恢复光明、人恢复知觉,我站起身挪步移到沙发上的时候,才发觉两条腿像被抽掉了筋骨一样软而且轻。
我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在我刚刚感到力量恢复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抽烟的本能欲望。我点燃了雪茄,那是我抽得最香也最过瘾的一口烟。眼前的小圆桌上还摊着刚刚写成的最后一页手稿,我仍不敢完全相信,这部长篇小说真的就这么写完了!我在这一刻,不仅没有狂喜,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篇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我此刻的感觉,像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被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承受不住而发生晕眩;又如同背负着一件重物埋头远行,走到尽头卸下重物时,业已习惯的负重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反而不适应卸载后的轻松。直到现在回想并书写这种始料不及的失重情景时,我还是有点怀疑这一系列失明、晕眩和失重的生理现象,似乎与《白鹿原》最后的人物结局不无关系。当时的情景是,在我抽着雪茄的时候,眼前分明横摆着鹿子霖冻死在柴火房里的僵硬尸体。这是我刚刚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天明时,他的女人鹿贺氏才发现他已经僵硬,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这个被我不遗余力刻画其坏的《白鹿原》里的坏男人,以这样的死亡方式了结其一生。写到这一行文字时,我隐隐感觉到心在颤抖,随后就两眼发黑,脑子里一片空白了。在我喷吐出的烟雾里,浮现出鹿子霖僵硬的尸体,久久不散。这个浮现在烟雾里的坏男人的尸体,竟然影响到我写完《白鹿原》时应有的兴奋情绪,也是始料不及的事。
南窗的光亮已经昏暗。透过南窗玻璃,我看到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暮色笼罩。尚不到下午五时,正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时月。我收拾了摊在小圆桌上的稿纸,便走出屋子,再走出小院。村巷里已不见人影,数九寒天傍晚的冷气,把大人小孩都逼回屋里的火炕上去了,游走在村巷里的鸡也都归窝上架了。这是冬天里日落之后天天重复着的景象。我已经难以像往常一样在这个时候守着火炉喝茶。我走下门前的塄坎,走在两排落光了叶子的白杨甬道上,感觉到灞河川道里如针扎一样的冷气,却不是风。我走上灞河的河堤,感觉到顺河而下的细风,颇有点刀刺的味道了。不过,我很快就冷得没有知觉了。

我顺着河堤逆流而上。这是一条自东向西的倒流河。河的南边是狭窄的川地,紧贴着白鹿原北坡的坡根。暮色愈来愈重,塬坡上零星的树木看起来已经模糊,坡塄间的田地也已经模糊,只呈现出山坡和塄坎粗线条的走势,这个时月里干枯粗糙的丑陋全部模糊了,反倒呈现出一种模糊里的柔和。我曾经挑着生产队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大葱、韭菜等蔬菜,沿着上塬的斜坡小路走上去,到塬上的集市或村庄里叫卖,每次大约可以赚一块钱,到开学时就装着攒够的学费到城里的中学报名。我曾经跟着父亲到塬上的村庄看社火,或秦腔。我曾经和社员一起在塬坡上翻地,割麦子。我曾经走过的熟悉的小路和田块都模糊了。我刚刚写完以这道塬为载体的长篇小说。这道熟悉到司空见惯的塬,以及我给这塬上虚构的一群男女老少,盘踞在我脑子里也盘踞在心上整整六年时间,现在都倾注在一页一页的稿纸上,身和心完全掏空的轻松竟然让我一时难以适应。我在河堤上快步走着。天色完全黑下来了。在黑夜微弱的光色里,我走到了河堤的尽头。我不知累也不觉冷,坐在临水的石坝上,点燃一支烟,脚下传来河水冲击石坝的婉转的响声。鹿子霖僵硬的尸体隐去了。我的耳朵里和脑海中,不间断地流淌着河水撞击石坝的脆响。数九腊月的灞河川道里,大约只剩下我在欣赏这种水流的妙音。
我不记得坐了多久,再站起来转身走向来路的时候,两条腿已经僵硬到挪不动步子,不知是因为坐得太久还是天气太冷。待到可以移步的时候,想到又要回到那个祖居的屋院,尤其是那间摆着小圆桌和小竹凳的屋子,竟有点逆反甚至恐惧。然而,我还是快步往回走,某种压抑和憋闷在心头涌起,真想对着南边的塬坡疯吼几声,却终于沒有跳起来吼出来。走到下河堤的岔口时,我的胸间憋闷压抑得难以承受,想着这样回到小院会更加不爽快,索性又在堤头上坐下来抽烟。打火机的火光里,我看见脚下河堤内侧枯干的荒草,当即走下河堤,点燃了一丛菅草。火苗由小到大、由细到粗,蔓延开去,在细风的推助下,火苗顺着河堤内侧往东漫卷过去,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我重新走上河堤,被烟熏呛得大咳不止、泪流不止。在四散的烟气里,我嗅出一阵蒿草的臭味,一阵薄荷的香味,自然还有菅草、马鞭草等杂草的纯粹的熏呛味儿。火焰沿着河堤内侧往东烧过去,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我的压抑和憋闷散失净尽了,鼻腔里还残留着蒿草的臭味儿和薄荷的香气儿,平心静气地走下河堤,再回到小院。
我打开每一扇屋门,拉亮电灯,还有屋前晾台上的照明灯,整个屋院一片亮光,我心头也顿觉敞亮。我打开录放机,特意选择了秦腔名段《花亭相会》,欢快婉转的旋律和生动形象的唱词,把一对青春男女的爱恋演绎得淋漓尽致、妙趣迭出。这是我平时放得最多的磁带,它往往能改变人的情绪。我开始动手点火烧水,为自己煮一碗面条。
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晚的一顿晚饭,也是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且不论香或不香。尽管从草拟到正式写作的四年里,我基本保持以沉静的心态面对稿纸,然而那道塬却时时横在或者说堵在心里,虽不至于食不甘味,但心理上很难感到从容。现在,横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堵在心里的那道颇为沉重的古塬,完全腾空了,经过短暂的不适和诸如烧野草的释放之后,挑着面条的时候我心中已经是一派从容了。我只能找到“从容”这个词来表达吃着面条时的心态。我做完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在写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时费劲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只是尚不敢预测它的最后结局,或者说还不到操那份心的时候,仅仅是做完了这件事。做完以后的轻松和从容,我在蹲在火炉旁吃着面条的这个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