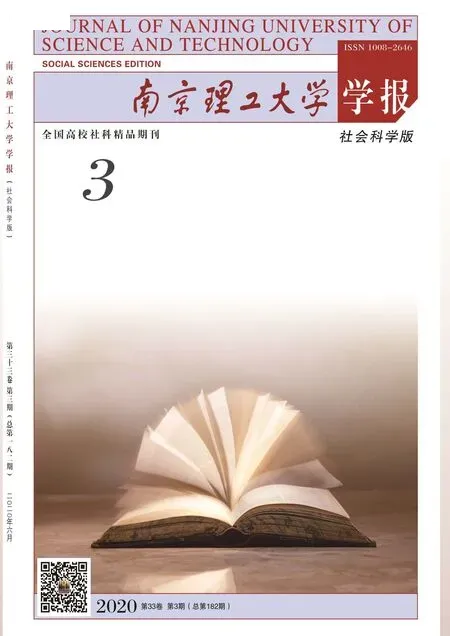微型大义:论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新加坡华人历史
谢征达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 999077)
一、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与希尼尔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从马来西亚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建国后的新加坡发展迅速,特别是工商业,在经济起飞后,市容环境亦有转变。20世纪70年代后,新加坡人的生活步伐日渐快速。其中,华文文化受到的影响最为深远,尤其在实行单一英语媒介语学园的教育制度后,南洋大学在1980年并入新加坡大学,华校生走入历史。全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关闭,原本活跃的学生团体如南洋大学中文学会、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南大诗社等群体同时退出舞台,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以下简称新华文学)可谓影响不小。[1][2]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包括希尼尔、谢裕民、张曦娜、梁文福、韦铜雀(吴耀宗)等,他们被称做“新声代作家”,其中有好几位是新加坡的“末代华校生”,对新加坡独立后的语言教育的转变颇有感触,在创作上开始书写新华文学的困境。同时,新华文坛出现了另一现象,即微型小说的崛起。微型小说在新加坡的发展可从两个层面解析:一是前文提及的生活步伐加速与华语教育的变相,华文文学读者的阅读时间紧缩,长篇小说的需求量则逐年减少。微型小说的简洁精炼,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独立后新加坡人的阅读风气,可说是顺应市场而崛起的文体;二是从全球华文文学场域发展脉络观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微型小说与台湾的极短篇或小小说开始盛行,新华微型小说则呼应了华人区域的文学趋势。
新华微型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以“小小说”与“极短篇”的名称登上文坛。1979年, 华文报章如《南洋商报 · 文林》与《星期日报》最先刊出了“极短篇”小说;至1988年,双月刊《大地》成为新加坡第一本在形式上专以诗歌及微型小说为主的刊物[3];1992年至1997年间,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微型小说季刊》则是新加坡微型小说的另一高峰。《微型小说季刊》的出版时间虽然只有5年,但对于微型小说在新加坡的推广多有帮助,后来也在整合刊物后,成为目前新加坡重要的文学刊物《新华文学》[4];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晚风》《千字盒》《文艺坊》《城市文学》等报纸副刊和《新加坡文艺》《新加坡青年》《热带文艺》《赤道风》等刊物都陆续推出微型小说特辑,形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微型小说写作风气。[5]在出版方面,新加坡也陆续生产出微型小说的合集与作品,如周粲的《恶魔之夜:微型小说》(1988)与他主编的《微型小说万花筒》(1994)、黄孟文的《赤道边缘的珍珠:新加坡微型小说》(1990)与《安乐窝》(1991)、贺兰宁主编的《幸福出售:新加坡微型小说选》(1990)、希尼尔的《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微型小说》(1992)、胡月宝的《有缘再见:胡月宝·微型小说集》(1994)等,这些作品使得微型小说在20世纪末的新华文坛窜升成为一股新兴势力。
在大力推动微型小说的作家中,希尼尔是关键的人物之一。1957年出生于新加坡的希尼尔从1970年开始创作,在作品上,早期与其弟谢裕民合著了散文集《六弦琴之歌》(1978),12年后,希尼尔出版了诗集《绑架岁月》(1989)。1990年后,希尼尔在微型小说的成绩上取得了突破,出版了两部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及《认真面具》(1999),此后更陆续推出许多微型小说,成为新华微型小说的代表人物。希尼尔获奖无数,他曾获新加坡全国书籍发展理事会颁发的“书籍”奖(1990),以微型小说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1992),金狮奖新诗首奖(1993),“书籍奖”(1994),新加坡国家文化奖(2008),在海外也曾获东南亚文学奖(2009)。同时他也是《文学半年刊》(1994)、《微型小说季刊》(1996)、《新华文学》(1998)的主编,亦担任过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历史元素在希尼尔的小说中受到了许多评论者的重视,特别是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张松建与南治国对战后出生的一代人逐渐遗忘新加坡的历史表示担忧,他们从“创伤记忆”视角展开论述。[6-9]另一方面,金进与朱崇科则对希尼尔小说中的历史公义提出解读,强调作者为了历史而发声的用心。我们能从不同学者的论述中阅读到希尼尔对历史的关注,这也是他在书写中最不可忽视的一部份。然而,本文希望能够开展微型小说与历史对话的可能,甚至探究极短篇幅的微型小说如何成为历史真相的平台。上述学者论述希尼尔的二战主题书写,意以铺展希尼尔的书写全貌;然而,希尼尔对二战记忆消退的独特关注是本文重要的论点。令人关注的是历史记忆的快速流失,他以微型小说反映了历史与文学间的备忘作用。
故此,本文论述冀望以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为讨论核心,从新加坡华文文学场域出发,思考微型小说与历史的互动,以及产生的文学能量。文章集中检视希尼尔小说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主题,特别是创伤书写与对新加坡人历史意识缺乏的批判。简言之,本文试图以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日本形象与二战主题为个案,解读其中的历史呈现,时隔近半世纪后重述二战历史的意义。具体的开展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希尼尔微型小说的文本中,探讨作者对历史多义性的思考,检视他小说中对历史的批判,以及微型小说作为平台带来的力度;二是从“历史反思”的批评论述出发,思考微型小说作为检视现代人对历史意识的认知之外,应该更重视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与多重情绪的再现 。
二、断指岁月:以二战主题建立“微型”论述
希尼尔的微型小说模式与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是本文关注的要点。值得思考的是,文学模式,特别是微型小说的极短论述,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历史思绪,以文学再现的历史批判是否具有意义?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回看美国历史学者海登·怀特思考历史特质的论述。怀特在《叙事的回归线》中集中批评了历史作为学科在性质上的偏差,并提倡历史应保有文学性质的内涵。怀特表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10年始,西欧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然对“历史意识”一词深怀不满,人们对于历史只在“过去的废墟”中进行挖掘表示质疑,并认为此举无法增加对当下的理解,反而带来更多对于未来的恐惧。[10]怀特批评历史已经失去了原本所应该具有的文学想象。因为历史学家为了让历史看来客观且更具科学性,反倒失去历史所拥有的力量。他强调,应将史学与文学再度进行关系连接,无需担忧意识形态的扭曲。 怀特强调历史应具有文学特性,其隐含意义在于,强调历史不应该是单纯由事实、数据或档案等堆积而成的。可以进行反向思考的是,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论述呈现对历史的思考,其意义对原来的历史论述是否具备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是,在希尼尔的小说世界中,历史元素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以二战为背景的微型小说为数可观,甚至可说是不厌其烦地论述二战。或许我们可做思考的是,二战主题对于一位新加坡作家而言,意味着什么?
从华人群体的历史认知层面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华人地区带来的是晦暗与惨痛。 新华历史研究学者周维介曾在《新马华文文学散论》(1988)中对新加坡不同的历史时段进行陈述。他将二战期间的新加坡历史描述为“断指的岁月”,并作出以下论述描述新马文坛的沉落: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南下,攻下新马,将历史纳入一个黑暗的时代,为时3年8个月,新加坡易名“昭南岛”,开始度着漫长的岁月。日军的统治,灭绝人性,大屠杀中,肃清两地的华人抗日分子,日军占领新加坡一个星期后,便接管所有各语文报馆,另创《昭南日报》,由日寇出版,成为那时期仅有的华文报章。《昭南日报》纯属日军统治新马的传达工具,以刊登日军行令,战功为主,于是思想言论陷入黑暗期,文艺的指掌断落,除了血外,便是一片空白。[11]
在新加坡,华人的死伤人数相较其他族群惨重,日军在此展开一连串残酷的屠杀行动,称为“肃清事件” 。(1)关于“肃清事件”,《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年》中有以下描述:“在宪兵队榜上有名或被告密者指认的嫌疑人,几乎肯定会被行刑队枪决。而幸运地被当局放过的人,手臂或一块布上被盖上印章或符号,可以回家。在检证行动中受牵连,并迅速被日军杀害的人,估计最保守的有5000人到5万人不等。”马尔柯姆·默费特等著,陈新才、张清江译,《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年》,新加坡:亚太图书有限公司,2011。在新加坡的历史发展中,二战作为在殖民统治时期与新加坡建国之间的一段历史,除了创伤论述之外,我们不应忽视该论述所具备的多重意义,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与家园意识之间产生的多重论述。大量的回忆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战后长达数十年的进程中形成哀伤、仇恨、愤怒、沉重等各种语调。以下是希尼尔的《始凌湄》(1982)一诗,更可与周维介对“昭南岛”的叙述对照,看出当时悲凉的氛围。
长长的血路从这里划起 / 无辜或无知 / 茫茫命运不知从何折起?
无情铁腕下 / 千般愤慨往上冲 / 三年又八月,满城皆英豪
犹如昨夜的我们 / 守着千疮百孔的堠垣
总想该有把剑 / 向这星灿星灭的江面 / 追魂[12]
《始凌湄》中 “血路”“茫茫”“无情”“愤慨”等关键词皆说明了历史的沉重与哀痛。“始凌湄”位于新加坡的西北岸,是日军最初踏进新加坡的位置,诗歌以此为名标志着沦陷时期的开始。(2)《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年》中指出:在1941年12月8日凌晨4点30分,新加坡的各个空军基地面对了日本空军的猛力炮轰,这便是新加坡持续三年战乱的开始。关于新加坡沦陷过程的相关论述请参阅Raymond Callahan, The Worst Disaster: The Fall of Singapore,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1 .英国守备军战略的失误加上日军速战策略的奏效,1942年2月15日的新加坡正式开启了3年6个月的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为了表明这座岛屿的新身份,取名为“昭南岛”,意思是“辉煌的南方岛屿”。(3)“昭南岛”(新加坡)当时也是日本帝国南部的中央执行区,成为一座“特别市”,并由东京委派来一位市长,其管辖权除了昭南岛之外,也涉及了廖内及苏门答腊。Tsu Yun Hui,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in Singapore to 1945”, Edited by Tsu Yun Hui, Japan and Singapore: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6):47 — 48.然而,日军统治后,这座小岛并不辉煌。相反地,恐惧环绕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当地的华人。在昭南岛沦陷的日子里留下了深深伤痕,也让这座小岛经历了最黑暗、最多怨恨的时期。
因为战乱,除了当时同样以“血”进行书写的抗战文艺外,新马华文文学在二战的三年中近乎陷入寂静。然而,从战后到21世纪,以日本二战为主题的新华文学作品繁多,如丁家瑞的《怒吼吧,新嘉坡!》(1947)[13]中对日本入侵的怒吼,苗秀《太阳上升之前》(1953)中妓女黑凤逃离觊觎她的“东洋鬼子”、刘培芳《犯规的女人》(1977)中主角对日本友人裕子个性前卫的诧异[14-15]、郭宝昆《灵戏》(1998)中带兵攻进”大岛”的将军[16]、丁云《攀绝峰》(2014)[17]中与日本女子的不期而遇等,在不同年代里的新华文学中几乎都有着二战的魅影。
其中,希尼尔更是书写二战日本形象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其针对日本的书写在1980年以降异常突出,从1982年的《退刀记》至2006年的《陪の手》,希尼尔小说中的日本魅影重重。一位出生于战后的新华文学作家,在距离二战近半个世纪后,持续对日本二战历史“穷追不舍”,这与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思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新华文学的发展脉络下,像希尼尔这般“执着”对某时期历史事件开展小说叙述的作家并不多见。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刘坤华副教授探讨了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的现象。他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人开始在当下与未来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与归宿,而非殖民地的历史。[18]换句话说,新加坡的写作朝向“向前走”的层面。然而,在20世纪的80年代后,希尼尔为何执意返回二战的历史现场,且不厌其烦地以该主题进行书写? 1980年后的新加坡在历史与现代进程中游走,再度回望近半世纪前的二战历史,找寻历史真相的声音此起彼落,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官方企图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侵略东亚的史实。
1985年,日本文部省要求送审的教科书,淡化了该国对亚洲国家侵略的史实,亦将在中韩等国之侵略改为“进出”,同时删除了对“慰安妇”之记载。(4)从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在26本教科书中只有8本对此做出指涉,就算是使用最广的教科书也只简单说明暴行在新加坡与其他地点发生。此外的其他课本虽提及日本军在新马屠杀了上万的海外华人,但当中叙述也仅限于一至二行。Hayashi Hirofumi, “Massacre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Its Coverage in Postwar Japan”, Edited by Akashi Yoji & Yoshimura Mako,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1941—1945(Singapore: NUS Press, 2008):245.希尼尔在《中日友好》一诗中的“无需耿耿于怀 / 侵略或进出 / 照样染红历史!”,显然是对于教科书词汇的讽刺。人为修改历史必然带来遗留后代的严重后果。其实早在1967年,针对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的家永三郎教授出版了《太平洋战争》,重新反思并论述了发生在新加坡的大屠杀。1970年,月刊《中国》刊登了一期“血债:在新加坡的华人大屠杀”专刊,详尽叙述了日本在新加坡大屠杀的举动。
希尼尔的《异质伤口》(1992)便是日本修改教科书的直接投射。该故事叙述一位新加坡国籍的男主角与日本女友早春芳子的分手过程。过程中,男主角突然陷入疯狂状态,不断怒斥日籍女友,指责她“忏悔、自责,是你们的词汇里缺乏的!” “那些历史教科书都没有记载吧?”[19]显然,男主角是另有所指,日籍女友仿佛成为二战时期侵略南洋、大量屠杀百姓的暴徒。在男主角歇斯底里的背后,犹如在发泄祖父母辈二战时期所遭受的冤屈。在提议修改教科书的1982年,希尼尔写下了《退刀记》与《野宴》两篇具有日本二战元素的小说。《退刀记》是希尼尔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主角是一位在二战时失去丈夫与亲人的老太太。故事谈到老妇在商店买了把刀,随后突然异常愤怒,急喊退货,怒斥那把刀杀了她的亲人。最后,故事才揭晓缘由,那是因为刀上印着“日本制造”的字样。故事从店员与老妇间看似荒谬的对话中,揭露出一段历史悲剧。日本制造的刀穿梭于古今,批评日本二战中屠杀的意图不在话下。[20]另一篇小说《野宴》讲述的则是一位母亲极力地阻止儿子与日本人做生意,却也充满着经济需求与历史责任之间的纠葛。希尼尔的小说是如此触动人心,王润华便评述希尼尔的作品:“处处都感觉到被连根拔起的悲痛,被连根拔起后之恐惧感” ,而吴耀宗则认为希尼尔的写作是“以其惯性的高度警觉和锐利目光去审视、勘察现实的结果。”
希尼尔努力呈现出小说中被“扭曲”的历史图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中不只是作为受害人后代的华人子孙,就连日本人的后代也被遮蔽。 希尼尔的书写与多数批评二战日军行为的作品的不同处在于,他在小说中关注日本官方在“扭曲历史”后对日本方面的与影响。具有高度历史反思意识的《横田少佐》是希尼尔在1987年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中的获奖作品。《横田少佐》的主角横田先生与叙述者分别是日本与新加坡在战后出生的一代。横田先生认为其祖父在新加坡是名英雄,坚称他负责保护“八十万市民”的日常生活;叙述者则强调他的祖父在二战时期遭受日军杀害的事实。各持己见的结果让氛围变得凝重之外,也似乎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 小说从两人对二战历史理解的差距中展开,两位后代存活在两段全然不同的记忆影响中,横田先生带着对于祖父保护新马市民的荣耀,而叙述者则是存有祖父被害的愤怒,形成历史留下的一大问号。类似的情节也发生在另一部小说《认真面具》(1992)中。故事讲述浩源与祖父到了新加坡圣淘沙岛参观二战展览时,发现了惊人的凶残场面。二战时期在日本出生的“祖父”在当下竟是一脸困惑。当然,孙子浩源的历史认知源于祖父,对于日本的二战历史更加没有头绪。历史的消失就连身处二战期间的日本人都浑然未知,这带出了巨大的思考面向。故事的结尾处突然出现一位老妇,并说“正要赶上明早一场追悼五十载冤魂的春祭”。老妇人的出现犹如一次招魂仪式,也强调了历史真相的挖掘仍未完结。换言之,日本战后第三代对于日军在新马的屠杀事件实属“一无所知”。地方性的差异并不改变二战历史所带来的创伤。在另一部微型小说《运气》(1992)中,两位长者,一位是二战时期在新加坡的外公,另一位则是在中国的老人家。两人在对话中忆起战乱时的“死里逃生”,结尾处主角的外公透露自己当时 “已落户到比江南更南的昭南岛”。 在中国与新加坡的两个老人家的历史记述,尽显了历史创伤对世界的共同影响。
如艾略特曾指出:“文学的意义是将血转化为笔墨”,希尼尔透过微型小说的多重论述,其视角不只局限在华人的创伤情绪,也诉说着日本人自身所面对的历史缺陷,当文学在再现历史的多面性时,其具备的历史意义不再是转述事实,更进一步带出了人的现状与情绪产生的缘由。希尼尔在以日本或二战为背景的书写中,其关怀面也集中在下一代人对历史认识的议题上。下文将讨论历史认知缺失的成因,并讨论小说中如何批评年轻一代在历史认知上的偏差。
三、”反思历史”:给未来者的历史叙述
进入到21世纪末,从1960年至1990年的短短30年间,日本已累积了可观的贸易盈余与外汇储备,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经济第二强,俨然是个经济强国。[21]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撰写了《日本第一》,书中表示从各项衡量国力的指标因素来看日本应为世界第一,确定了日本作为经济强国的地位。该书后来甚至在新加坡成了公务员的必读材料,以确保新加坡能够对这个高速发展的日本保持认知。此外,新加坡推展了“向日本学习”的活动,在不同场合中都对日本多有赞许,劝导新加坡人向他们学习,根据1981年4月12日《海峡时报》的报导,“向日本学习”口号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制造出新加坡正在让自己成为“东南亚中的日本”的印象。可见,新加坡在世界趋势的影响下与日本产生了微妙关系,而这尊敬与敬仰的姿态显然与不到半世纪前的二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日本官方少有正视历史的言论,在希尼尔的小说中,这无疑是一种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以《其实你不懂我的伤!“至诚的忏悔”回响录》(1991)为例,故事反映的是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在1991年访问新加坡时提出“忏悔”之说,但后来又表示是个人而非代表日本的忏悔,引发舆论。 然而,小说重点在于展现不同论述者的不同立场。当中有立场不一的六位叙述者。其中有对日军恨之入骨者,也有对日本二战毫无所知者,或是毫不在乎者。该文对“历史健忘症”的批判最为明显。该文提及日本时联想到的是高效率、科技先进、洁净等优良特质,不再强调回看历史的重要。故事中的不同声音透露出参与者对历史面貌的不解,及对历史事实的忽视。 最后一位叙述者甚至说让历史“改一改也好”。历史面貌在新加坡并非被掩盖,而是受到了选择性的忽视与放弃。希尼尔小说中,也看出他讽刺性地表达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轻浮。希尼尔的小说经常以轻松笔调带出一篇篇沉重的故事。1989年的《新春抽奖》则是将讽刺笔调推到极致,内容是一场“配合日皇驾崩及明仁太子继位”的抽奖活动,故事内容只有奖励与细则。无论是第一奖的“南京屠杀城二十日欢乐游”或第二奖的“珍珠港偷袭地十日海上逍遥游”,甚至是礼品“24k镀金模型军刀一把” 等,皆明显借用二战元素进行对历史的讽刺,不再以一般论述,而是以类似活动广告带出批判的力量,这或许是微型小说比一般文类更能直接施展的力度。
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不断重复着对二战历史的诉说,此一模式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更像一位历史学家。这里可以再次回到怀特的论述中进行解析,怀特指出历史学家的特质之一是他们试图“重新”熟悉我们遗忘的事件,无论是意外的、忽略的或是压抑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会处理历史事件中的文化层面,特别是具有“创伤”性质的,探讨这些事件对当下生活的影响。前文提及的《横田少佐》与《异质伤口》,无论是《横田少佐》中的主角对两个侄子急往“西城秀树的演唱会” ,或是《异质伤口》男子翻阅报纸中见“一大版的SONY,不见SORRY……”,新加坡人崇“洋”媚外的例子不断出现,只是这里的“洋”从西洋已然转为东洋。日本对新加坡的“入侵”卷土重来,可是,这次不是一种统治的强权,来到新加坡的是经济上的刺激与科技现代化。此处论及的历史记忆的遗失是一种选择性的决定。与日本的情况一样,在新加坡战后一代人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不追求历史真相及失去对历史全貌的理解。
希尼尔对于下一代掌握历史知识与对历史文化的尊重非常重视,如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对希尼尔的小说指出:“华人移民数百年历史之所以维持不坠,有赖强烈的语言、教化传统的延续,然而追昔抚今,希尼尔却看出这一传统的后继乏力。”[22]希尼尔在小说《我的来世不是梦》(2000)的创作过程中了解到一份社会调查指出新加坡年轻华人有10%在来世都想当日本人,希尼尔在小说中尽述新加坡青年对日本科技的崇拜,“你没注意到我们周围都是Japanese products:路上的汽车,家里的电器,办公室里的电脑、电话,街边的餐馆、卡拉OK,哪一样不比他人强?日本高科技引导新潮流,年轻人都很cool,很in!” 故事具有讽刺性,但也充分展现出日本的现代性对新加坡华人的影响力。在现代化对传统的冲击中,《咖啡小传》(1987)对日本有着暗讽成份。一间二三十年历史的“福州咖啡店”重新装修为“富士山咖啡座”。 “福州”改成了“富士山”,咖啡座开启了现代化的转变,但传统格调却流失,传统咖啡座也失去了意义。
在文章结束前再对希尼尔在微型小说中的日本符号“の”字的负面性进行再延伸思考。《陪の手》(2006)中飘洋过海到新加坡从事按摩工作的妈妈最终妥协提供 “Extra Service”(特别服务)。“の”的采用在希尼尔的文章中,逐渐不再与日本或二战有着对应关系。令人惊讶的是其“祸”的意涵,成为了一种来自日本的负面符号。“の”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其实也充满着张力与冲突。它既是链接,也是罪恶的原初,无论有意或是巧合,如同憧憧魅影与幽灵般的文字始终没有离去,希尼尔用这样的文字来表现对日本朦胧的畏惧与担忧。
四、结语:当“微型历史”成为认识
微型小说虽然不能够进行大的历史铺述,但却在书写中重构出一幅历史的图景。意大利的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提过一句有意思的话:“当历史事件经过再三思考时,它就不尽然是一个‘时间中’的事件了,历史成为了一种对永恒现在的认识”。[23]在希尼尔微型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同的历史事件的论述,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再现的不只是历史事件的对与错,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对人的情感的关注。从小说中,我们也可以对现实进行审思,二战故事不断在读者的阅读视域中浮现对人性的思考时,俨然已投注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
如前述引用怀特的论述,希尼尔的小说带给我们的是对历史进行的一种“新”的阅读。作者透过小说关怀的不只是孤岛上后代对历史知识的曲解,更批判了对历史的无视与偏见,其故事中的日本图像犹如新加坡在战后不愿离去的回声。希尼尔对于历史的流传有着深度关怀,其书写时而讽刺,时而幽默,但更大程度上看到的是忧心忡忡,可说是异常沉重的在地情绪及历史的包袱。这也是希尼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提供的自己的诠解,以文字补足缺漏的历史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