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崔颢《黄鹤楼》
黄天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在蘅塘退士(原名孙洙)所选《唐诗三百首》的七律中,崔颢这首《黄鹤楼》被列为第一首。严羽早在《沧浪诗话》中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又据《唐才子传》载,李白曾登上黄鹤楼,也想赋诗,但当他看到墙壁上已有崔颢的这首诗,便敛手不作,于是有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传说。后来李白到了南京“凤凰台”,才写了《登金陵凤凰台》。在李白的这首诗里,明显有比拟《黄鹤楼》的痕迹。我认为,无论是否真的发生过连诗仙李白也佩服袖手的事情,崔颢的这首诗确是不可多得的神品。

现存崔颢的诗作,约有四十多首。有写宫怨闺怨的,有写游旅登临的,有写边塞生活的,有写与僧侣交往的,内容比较驳杂。而且诗风多变,有绮丽纤巧的,有通俗流畅的,有激越慷慨的,有清淡平实而意境深远的。在他所有现存的作品中,《黄鹤楼》是写得最好的一首律诗。
据《唐才子传》所载,崔颢出生于河南开封的名门望族,他青少年时,作风轻薄,风流成性,诗风也浮艳。据说,有权有势的李邕,听说崔颢颇有才气,约他会晤。崔颢便把《王家少妇》一诗呈上。谁知思想保守的李邕看后,拂然不悦,认为这诗写得佻?轻浮,转身便走。不过,后来崔颢北游边塞,诗风大变,写出了《雁门胡人歌》《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等作风刚健的诗篇。《河岳英灵集》也提到他“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他早年声誉不佳,后来仕途蹭蹬,一生只到处游逛,做过几任不三不四的官职。坎坷的经历、眼界的拓展,让他逐渐觉得前景渺茫,看透世事沧桑。《黄鹤楼》一诗,应该是他在晚年感到人生虚幻的作品。
人们很容易看到,《黄鹤楼》虽然被视为七律,但又和一般七律诗所规定的格律有所不同。特别是前四句中,“黄鹤”一词连用三次,“去”字和“空”字各用两次。字的重复出现,本属格律体之大忌。至于第三、第四两句,也不作律诗所规定的对偶句;第四句末尾的“空悠悠”,连用了三个平字,又“犯三平”之忌。这些都有悖七律这一特定体裁的规定。但是,人们却不以为忤,反而赞赏有加,这是为什么?
从南朝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以后,人们注意到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在声调上一字一音、在词性上一字一义的特点,发现诗歌创作,除了句子字数齐一和需要押韵以外,还可以利用声调的“平”与“仄”,以及句式上对偶与非对偶的矛盾统一,进一步强化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和形式美。约定俗成,便出现了区别于不太讲究声调节奏、只需押韵的“古体诗”,被人们称为“近体诗”或“格律体”的诗。

到唐初,格律体的“五律”“七律”逐渐流行。盛唐时期,近体诗更成时髦。对于平仄的规定和颔联、颈联的设置,固然能大大提高诗歌作品的美感,但也会成为约束创作的思维定式。于是,有些诗人想到古体诗随意性较强的好处,尝试着把“古体”与“近体”适当结合,一般是在律诗的前四句,只讲究押韻,第三、第四句之间,也不讲究对偶。比崔颢早出生约半个世纪的沈佺期,写过一首七律《龙池篇》,前四句是:“龙跃龙池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这几句诗,全不管用字重复,一味拍皇帝的马屁,为大书特书那条“龙”,有意破格。至于后面的四句,又基本上符合七律的要求。有人便赞扬他的这一尝试“前四语法度恣纵”(《唐诗镜》),意思是说他打破了律诗的成规,敢于自由地纵笔挥写。
崔颢的《黄鹤楼》,有意模仿沈佺期的做法,这是人们早就注意到了的。赵宦光说,对《龙池篇》,“崔颢笃好之,先拟其格,作《雁门胡人歌》……自份无以尚之,别作《黄鹤楼》诗”,“然后直出云卿(佺期)之上,视《龙池》直俚谈矣”(转引自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一)。的确,如果把《龙池篇》和《黄鹤楼》两诗的前四句做一比较,不难发现,虽然两者都不在乎字词的重复出现,但前者“用经语入诗,非具化工手段,未易融洽”(见《卶庵重订李于鳞唐诗选》),反显得冬烘呆滞,后者则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黄鹤楼》前四句,首尾连贯,一气呵成,明显把格律诗的句子散文化和“古体诗”化。但后面的四句,在转折中又与前面相互配合,在格律方面,分明符合格律诗的规定。也可以说,崔颢的《黄鹤楼》是七律的一种变体,正如《删订唐诗解》评说它“不古不律,亦古亦律”。从这里,我们可以体悟,古代一些优秀的诗人,包括李白,既懂得格律的重要性,同时又不想囿于格律,敢于在形式上有所追求、有所创新。
人们登临赋诗,多是从描写所见的景色入手,像王之涣《登鹳雀楼》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杜甫《登高》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等。而崔颢登上黄鹤楼,他首先着眼的,不是黄鹤楼上的景,倒是“黄鹤楼”这名字。
据说,这濒临万里长江的黄鹤楼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有人说费文祎,有人说王子安,在楼上跨乘黄鹤,飞上天去,成了仙人。这当然是虚无缥缈的故事。崔颢竟从这神话传说入手,把虚的事看以为真,巧妙地以黄鹤的具体形象,引导读者思入微茫,跟着他浮想联翩。这写法,确属新颖而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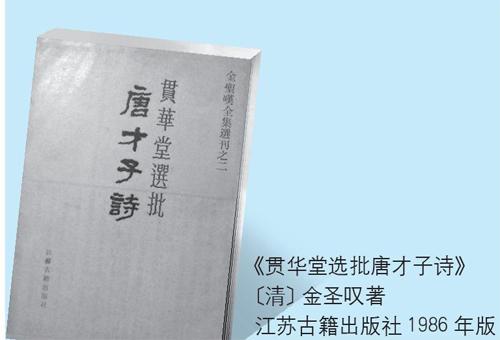
《黄鹤楼》的前面四句,完全是崔颢抒发对这名胜古迹的感慨。他让“黄鹤”一词重复呈现。这散文般平白的语句,一气呵成,让人很容易理解。正如金圣叹说:“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又说:“通解细寻,他何曾是作诗,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见道理却是如此,于是立起身,提笔濡墨,前向楼头白粉壁上,恣意大书一行。既已书毕,亦便自看,并不解其好之与否,单只觉得修已不须修,补已不须补,添已不可添,减已不可减,于是满心满意,即便留却去休回。”(《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金圣叹从诗人和评论家的角度,想象崔颢当年创作《黄鹤楼》的情景,十分有趣,却也表达出人们在阅读这诗时,感觉到崔颢在粉墙上文不加点、一气挥成的印象。
但是,金圣叹没有注意到,这连贯而下的四句,其中,崔颢又不露痕迹地让每句诗有所转折,它连中有断,贯中带变。像第一句,说仙人已乘黄鹤走了。本来,走了就走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但第二句,则说黄鹤虽然走了,但黄鹤楼依然存在,这就是一变。可是,雀鸟飞去了,往往是会飞回来的,李白不也在《赠闾丘宿松》中说“飞鸟还旧巢”吗?然而,崔颢在第三句则强调,这黄鹤是永不回来的了,这又是一个曲折。最后,他才归结说自己登上高楼,仰天望去,只觉得千年万载,黄鹤楼上的天空一片空空荡荡,只有几片白云,徒然在这里悠悠飘忽。于是,黄鹤楼兀立江头,它像是一根孤独的标杆,恰好反衬出岁月无情,世世代代,留下的只是空虚寂静。清代的朱彝尊有词云:“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千百年来,茕茕孑立的黄鹤楼,不也像秦淮河畔那根渔竿,见证着时间的永恒、人世的沧桑吗?
《黄鹤楼》前四句,一气呵成,却又蕴涵变化,就像瀑布,飞流千尺,而绝壁凹凸不平,这让奔泻而下的洪流,冲击突兀巉岩,溅起阵阵水雾飞花,更能引人入胜。这欲断还连的语势,让读者更能感受到作者思想感情的冲击力。其实,这也是崔颢惯用的创作手法。像他的《长干曲》:“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四句诗,写一位在水上行舟的少女,碰上一个男子,自问自答的过程。它明白如话,一句连着一句,流动自然。看来,这少女大概是舟行寂寞,恰好遇上了对眼的男子,便主动搭讪,提出“君家在何处”的疑问,但回心一想,自觉有点唐突,便赶紧自我介绍。这语气,是一个转折。看来那小伙一下子愣了,少女赶紧解释停船借问的原因,这又是一个转折。于是,一位天真大方又有点羞涩腼腆的少女形象便在语如贯珠却又转折变化的诗句中展现无遗。《长干行》与《黄鹤楼》前四句的写法相似,同样收到奇妙的审美效果。
《黄鹤楼》第五、第六句,承接着前四句,崔颢的笔锋做了个大转弯,他写自己的目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如果说,诗的前四句,是诗人写他遥望天际,那么,这颈联便转为写他眼光朝下,从仰望苍穹回过头来,细看黄鹤楼下的景色了。
首先,他写黄鹤楼下的近景。在地面上,他看到汉阳的树。这些树,一株一株,历历在目。在楼的另一边,鹦鹉洲上,芳草茂盛,欣欣向荣。地面上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这景色,和他仰视天空时只见白云悠悠,一片混茫,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认为,崔颢写到芳草萋萋,写到鹦鹉洲,是想起了《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诗句,是想起了身世辛酸的祢衡写过《鹦鹉赋》,因而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这意见,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
要说明的是,崔颢写这颈联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是大转折,和上面的四句又是连贯的。就像乐曲在进行中忽然移调,整个调子转移为另一个新调,感情色彩出现了猝然的变化,但由于旋律的音程、和弦并没有变,因此乐曲的主题又是连贯的。在《黄鹤楼》中,崔颢首先写自己从楼上望天,跟着目光大转移,从楼上望地。但无论怎样,也都紧紧环绕着“望”的旋律。因此,这颈联是全诗“移调”的枢纽。在颈联中,崔颢又着意用“历历”“萋萋”的叠字,和上句的“悠悠”相对应,这清丽的描绘,也收到气韵连贯的效果。所以,清代的方东树指出:“崔颢《黄鹤楼》,此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可贵。”(《昭昧詹言》)这判断是准确的。
崔颢清晰地描绘他所看到的黄鹤楼前的近景,固然是点染出这一带景色的秀美,但其最终用意却不在于此,而在于表现他往下望时,从地面上近处放眼到远处。因此就有了第七、第八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显然,第五、第六句写近景,又是为第七、第八句写视界延伸做准备。
在近处,黄鹤楼地面上的景色一目了然,而由此远眺乡关,就不是了。崔颢的家乡在开封,他登高远眺,怀乡之情顿生。但是,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他怎樣也望不到。加上日暮之际,长江上笼罩着一片烟波,朦朦胧胧,渺渺冥冥。他的视野,即使放尽,也只能感觉到开封远在天涯。在这里,崔颢特意提出“家乡何处是”的疑问,正是要表现他在一面努力思索,竭力寻觅,一面又表现出伤感情怀。如果他直说“日暮乡关看不见”,直来直往,那就无法细致表达远望思乡的情感了。在句末,崔颢下一“愁”字,概括了他向地平线上遥瞰的心境。其实,这“愁”字也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黄鹤楼》的上半首,似乎只叙述了一个神话,并以“空悠悠”三字,稍作人去楼空的感慨,而到诗的最后,诗人便索性点出“愁”。这“愁”,贯串全诗,在结构上起到千里来龙,到此结穴的效果。
为什么崔颢这首《黄鹤楼》一经写成,就受到历朝评论者的普遍盛赞?我认为,这首诗的写作技巧是高明的,抒发思乡怀古的情绪也是明显的。从创作技巧的角度去赏析它,固然是需要的,但如果仅着眼这些方面去研析它,似还未能理解崔颢创作这诗的深意,也还未能理解它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只有从古代诗人普遍存在着矛盾心态的角度,去观察它,研究它,才有可能理解它所独具的典型性价值。
崔颢在黄鹤楼上,愁什么呢?他仰视长天,觉得四周空空漠漠,物是人非,百年千载,时间就这样“不复返”地过去。而当他俯瞰大地,景色历历在目,延展到远方,则莽莽苍苍,望不到头;空间就这样横无际涯,可望而不可即。崔颢遥吟俯唱,在怀古思乡的情绪中,更主要是出于登上高楼,环视四周,俯仰今古,触景生情,发现时空渺茫和人生的无助与孤独。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朴素的辩证思维,认识到“天人合一”,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同时,有不少人又认识到,天与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方面。《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既然“天”与“人”是不同的方面,便有不一致的地方。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宇宙时空是无限的,人生则是有限的。陶潜早有这样的诗句:“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二十首》)在初唐,陈子昂浩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实,从魏晋以来,嵇康、阮籍等人在认识“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人”和“天”的矛盾。当他们无法解脱个人的失落时,便借酒佯狂。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似是开玩笑的话,其实明显地强调以“我”为主,意识到“我”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
事物的进展,是有反作用力的。就认识论而言,也是如此。老祖宗们越是强调“天人合一”的理念,越是有人意识到宇宙时空的无穷与人的个体和人生的有限,存在着一对矛盾。当人们越是研究、探索、叩问这一极具哲理性的问题时,对“天人合一”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大。反映到传统文化观念上,恐惧短促,伤感孤独,也成为诗坛上的另一种声音。当然,这声音有消极的成分,却又反过来说明,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时代,有这种想法和情绪的人,实际上是透露出对个人生命和价值的依恋。
从陈子昂的喟叹,我们看到,魏晋以来显然更多人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更多人认识到宇宙、天地是无限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与崔颢同时期的李白,也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到宋代,苏轼把天地与个人依存而又对立的关系,说得更清楚:“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自古以来,越是有才能、有抱负的人,若未能有所施展,仕途坎坷蹭蹬,便越感孤独与无助。当他们俯仰天地,环视古今,慨叹时空茫茫而产生的孤独感,就愈突出。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他们逐步认识到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是“有志不获骋”,认识到这依附于“天”而独立于天的“人”,其价值无法实现而已!
上面说过,崔颢曾呈给李邕看过《王家少妇》一诗,这首诗说嫁给了王昌的少妇闲得无聊,“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其实,他不过是借描绘王家少妇的情状,说自己闲得发慌,希望李邕能提携他,抬举他而已。谁知这块敲门砖,反砸了他自己的脚。这种以妇妾身份自譬的态度,反而证明他有急切向上攀爬的心态。后来愿望落空,他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四顾茫然。时空无际无涯的存在感和个人寄蜉蝣于天地的孤独感,便各成反方向骤增。盛唐之际,容纳佛道的思想观念,也在他的腦海里骤增。经历人生的波折,他和怀一上人等宗教人士,多有交往,接受了“观生尽入妄,悟有皆成空”的想法。在他另一首名篇《行经华阴》中,当他看到太华山的高巍险峻时,竟然发出了“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的感慨。
《黄鹤楼》不就写到有人跨鹤成仙吗?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作者思想发展的痕迹。在崔颢之前,王勃曾经说:“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滕王阁序》)他以骈文的形式,叙述时间空间的无际无涯与人生的有限这既统一又对立的状态,透露出对人生无奈和孤独的慨叹,也派生出对个人存在价值的认知。崔颢的《黄鹤楼》,则是以七律的诗歌体裁,以古体诗与近体诗结合的方式,以神话传说虚中有实的想象与眼前景物具体视像的实中有虚相互结合的写作手法,抒发他的落寞感和孤独感。就这一点而言,他和王勃的观念是相通和相承的。
实际上,封建时代许多诗人在怀才不遇,感到“天之道”无法实现的时候,反而或模糊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许多人的出世思想,不过是虚幻化的入世思想的折射。有些人,或从愤懑走向消极,或从忧愁走向空虚,或从宇宙的永恒认识到人生的渺小。这实际上是对人生自我价值无实现的抵触。反过来,也说明了他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崔颢写作《黄鹤楼》时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在整个封建时代的诗坛上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受广大人群的推崇,甚至出现了连李白也甘拜下风的传闻。我认为,这一切,不单纯是赞扬它的创作技巧,也不仅仅是推许它在审美观念上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人们感受到它透露出的对人的价值的认知,不同于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观念。到封建时代后期,不少具有异端思想的人,像李卓吾、徐文长等辈,也往往兼具出世之思。可见,包括崔颢在内认识到人的价值存在的观念,也可以说是明清时代诗坛异端思想的端倪。
不过,崔颢在《黄鹤楼》中所抒发的“愁”,只是淡淡的、隐隐的。它不同于杜甫“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哀伤,不同于岳飞“凭栏处,仰天长啸”的悲愤,也不同于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抑郁。说实在的,崔颢的经历和心态与杜甫等人不同。在安史之乱发生的前一年,他就死了,没有受过颠沛流离的痛楚。在封建时代,他只属擅长创作却又是很普通的小官。他在人生中所受的冲击,并不算太强烈,这又和多数士人的命运相似。我认为,《黄鹤楼》所呈现的心声,恰好是封建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个人存在的价值,想表达却又无从表达。崔颢在《黄鹤楼》中,却能恰切展现许多人欲说还休的情感。这一点,正是它受到读者们普遍欢迎的缘由。
在叙事性文学中,能塑造“熟识的陌生人”的典型形象,是达到创作水准最高的标志。抒情性文学,不以描绘人物为主,当然与叙事性的作品有不同的追求,但道理是相通的。如果作品能抒发出“熟悉的陌生情”,把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以独特的方式融汇表达,是否也可以说是达到了诗歌创作水平的最高境界?
在《黄鹤楼》中,崔颢要抒发的,只是登高望远怀古思乡的感受。问题是,为什么他既写怀古,又写思乡,这具体意象的背后究竟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它蕴含着什么样的意念?不同的读者,可以从自己的感悟中引申出许多想法,从而呈现出“象外之象”。明代谭元春认为:“此诗妙在宽然有余。”(《唐诗归》)所谓宽然有余,是说审美客体可以从这诗怀古思乡题旨的引导下,生发出更为深远的意境。金圣叹说得更清楚,《黄鹤楼》这诗“只一意凭高望远,别吐自家怀抱,任凭后来读者自作如何会通,真为大家规摹也”(《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古代的评论家,虽然未能从《黄鹤楼》在俯仰时空时产生的孤独感中,认识到它对个人价值认知的深刻意义,但他们已经觉察它到达了唐代七律的最高境界,真可说目光如炬,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