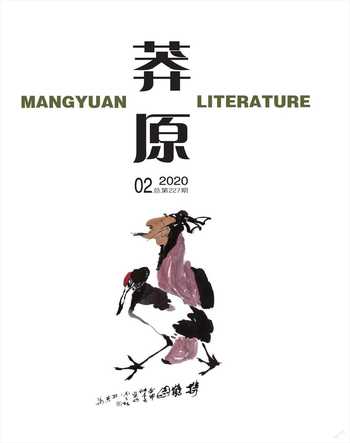轻如萤火
非鱼
1
我在健身房刚活动开身子,微微出汗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微米打来的:唐丽,我在健身房门口等你,快点,有事。
她并没有问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口气不容置疑。奇怪,她怎么知道我在健身房?尽管很不情愿,我还是换了衣服出来,微米果然在健身房门口站着。
暮春的天,阴雨加上冷风,要不是路边一排梧桐树泛着脆生生的绿色,给人的感觉更像秋天。
微米说,他死了。
谁?
我爸。
咋死的?
应该是突发心梗吧……反正是死了。
你不去看看?
已经送去太平间了。明天再说,今晚咱俩一定要喝一杯。微米口气里没有一丝悲伤。她不止一次给我说过,希望她爸赶紧死,她快熬不住了。
吃饭的时候,微米点了很多菜,还要了一瓶“天之蓝”。你确定我们两个人要喝完这瓶酒?我问。她点点头,对,你要是不想让我喝醉,就尽量替我分担些。
從晚上六点开始,我们一直喝到夜里十一点,才把那瓶酒喝完。还没走出房间,微米就吐了。那些饭菜、茶水和白酒,混在一起,经过胃的短暂发酵,变成难闻的混合物,倾泻而出。她的衣服和鞋子,被溅得斑斑驳驳。可她却一个劲咧着嘴傻笑:告诉你,唐丽,我爸死了,真的死了……
她的话吓了服务员一跳。当时,那个短头发的中年女人端着一杯水,正准备给微米漱口。她瞪了微米一眼,你爸死了你还来喝酒?还能笑得出来?微米回瞪了服务员一眼,要你管?我喝酒怎么了?就喝!服务员“哐当”一声把杯子墩在桌子上,不肖子孙,小心遭雷劈。微米嘴角垂着长长的一根涎水,冲着服务员的脸喊,劈就劈,劈死拉倒。大概是她的口水喷到服务员脸上了,服务员手一挥,正打在微米鼻梁上,立马鲜血直流。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发生的一切,脑子里异常清醒,腿脚却动不得,当然也懒得跟她们理论。就那么一直看着她们,直到派出所的警察到来。
由于我和微米都处于醉酒状态,警察无法正常做笔录,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才让我们离开。
走出派出所,我彻底清醒了。坏了,从下午见到微米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给刘会天说;而这十几个小时,他居然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掏出手机,却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
我推了一把摇摇晃晃的微米说,赶紧把手机给我,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电话接通,我刚“喂”了一声,刘会天就炸了,唐丽,你跟谁鬼混去了?半夜不回,手机关机,孩子不管,想干吗你?
听刘会天吼完,我一个字也懒得跟他说了。跟他说有什么用?反正他也不信。这个四十五岁的男人,比我更早地进入了更年期,发量锐减,体重飙升,心眼却越来越小,多疑,暴躁,遇到问题除了抱怨,就是吼。
凌晨四点的街头,陪着我们的,只有路灯。偶尔有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略有减速,见我们没有乘车的意思,又疾驰而去。
哎,你闻到没?
什么?
槐花的味道。
一缕甜丝丝的香味从远处飘来,没错,是槐花的香味。循着香味,我们找到了一棵老槐树,在公园靠墙角的地方。靠着这棵槐树,在一团香甜的包围下,我和微米等来了黎明。
去安排你爸的后事吧。我跟微米说。
那你怎么办?
回家,还能怎么办……
2
儿子已经上学走了,刘会天坐在沙发上等我。
我看了他一眼,换好鞋,坐在他对面。
你疯了不是?这一夜到底去哪儿了?电话关机,浑身酒气,跟谁鬼混去了?
跟微米。她爸死了。
她爸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爸死了,至于整夜不回家啊?
刘会天,你会说人话不?她爸死了,她找我出去喝酒;喝多了,让服务员把她鼻子打出血了,去了派出所;我手机也没电了。就这么回事,你爱信不信。
刘会天脸上的表情不断发生着变化,他的嘴一张一合,眉毛跟着动来动去,牵得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都能放下一根手指头了。额头上两边的头发像霜打的茅草,稀疏干枯,中间那块头皮油腻发亮,像刚出锅的一张凉皮。
她爸死了,你们竟然还出去喝酒?
是啊。怎么了?
你每次都这样搪塞。我问你细节,细节,一晚上待在外面,我不相信就你和微米两个人?
你既然不信,还问什么。
一夜没睡,我竟毫无睡意。想去卫生间冲个澡,然后去上班。刚关上门,他一把推开了。我坐在马桶上说,出去。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出去。他靠着门,死死盯着我。我却盯着墙角的那桶洗衣液:蓝月亮,深层洁净护理洗衣液,护衣护色……后面几个字是什么,看不清了。薰衣草香味,我喜欢这个味道。好多年了,我一直用这个牌子,这个香型。我半个月洗一次床单被套,不是因为脏,而是喜欢闻洗过后床单被套的味道,就好像钻在一团香气四溢的花丛中。我喜欢把脖子、肩膀塞得严严实实,甚至贴着耳朵。
唐丽,你准备在马桶上蹲一辈子?刘会天喊了一声。
你出去,我要洗澡了。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应该是定的闹钟。他瞪我一眼,转身出了卫生间。正常情况下,他此刻应该还在书房的那张床上打呼噜,等待闹钟把他叫醒,然后翻个身,等待闹钟十分钟后再次把他叫醒,他才会起床。
当年篮球场上的追风少年,才四十五岁,就早衰了。从上班到现在,他没有换过单位,甚至连岗位都没有换过。每天按时上下班,按部就班地在单位得过且过。用他的话说,闭着眼睛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的主管领导,他的科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唯有他一直在那个位置上,除了调整过办公室,他的桌子、椅子都没有动过,甚至连电脑摆放的位置,都没有变化。我曾劝他换个科室,别像一头磨道里的老驴似的,他也找领导说了,领导说现在的岗位离不开他。
热水从头顶淋下,流过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毛孔舒张,困意渐渐来袭。
微米,她会如何处理她父亲的后事呢?就像她之前说过的,火化之后,把骨灰撒入黄河,或者随便找个树坑埋了?
我闭上眼睛,有些眩晕。
刘会天又在客厅喊我,听不清楚他说的什么,我干脆装作没听到。
3
我给微米打电话,问她在哪儿,她爸的后事准备怎么处理,要不要帮忙。微米有点心不在焉,身边好像有很多人说话,很嘈杂,她说:回头打给你。就挂了。
要说,死者为大,我不应该对微米她爸有任何不敬,但那老头又实在可恨。
我见过微米她爸,总喜欢穿一件卡其色的风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双手插兜,走起路来腰背挺直,步履潇洒,头发打着发胶,丝丝不乱。那年他已经七十岁了,依然风度翩翩。微米说,她爸年轻时非常帅气,是他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学的是英语专业,还精通俄语、法语。难怪他总是一副绅士派头。当时,微米她爸双唇紧闭,目光凌厉地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没有说一个字。微米给他送钱,他接了钱,转身就走。转身的那个动作,也是潇洒至极。
微米对她妈几乎没什么印象。她一直不明白,她爸当年为什么会和她妈结婚,父母离婚时,她还不到一岁。
父母离婚后,微米就被送回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乡下的那些日子,她很快乐,她从没有学过“爸爸、妈妈”这两个词,她以为她是爷爷奶奶的孩子,一直到七岁该上学了,她爸才来接她回城。
微米怯生生地跟着她爸,拉着他风衣的带子,坐汽车,倒火车。一路上晕晕乎乎的,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树,还有高低起伏的大山,身边拥挤的人,说着听不懂的话。她很害怕,但不敢告诉她爸。一路上,他们两个人基本上都不说话,她想撒尿了,就拉拉他的衣服。他买来饭,递给她,她接过来就吃,反正这些饭都比爷爷奶奶做得好吃。
出火车站的时候,是清晨,到处雾气蒙蒙的,她爸告诉她:这是银川。
微米说,在银川的那五年,她一直跟做梦一样,感觉恍恍惚惚的,很不真实。她甚至经常怀疑,是不是真的在那里上过学,是不是真的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五年。
那五年,他们父女也很少说话,家里整天死气沉沉,她甚至不知道她爸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她爸很少问她的事,只看考试成绩。考得好了,他一言不发,把卷子还给她,如果考不好,他会训她几句。微米说,四年级寒假前那次期末考试,她明明都会,但故意把卷子写得乱七八糟,她想让她爸多问几句,多说几句,哪怕是训她也行。但她爸拿到卷子,认真地看了看,并没有多少愤怒,而是长叹了口气,又还给了她。
小学毕业那年,她爸带回一个女人,让她叫妈妈。微米从小到大都没叫过妈妈,叫不出口。女人生气了。她爸动手打了她,一巴掌下去,她的脸就肿了。等到放暑假,她爸又把她送回了爷爷奶奶身边,让她在老家上初中。
微米说,一看到老家村口的那棵大槐树,她就想放声大哭,想跑,想喊,想叫。但一看到她爸的脸,又赶紧用力紧闭嘴唇,老老实实地跟在他身后,回到了老屋。
从银川回来后,微米发现爷爷奶奶突然老了,爷爷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奶奶的一只眼睛也已经失明。她非常害怕,怕爷爷奶奶死了没人管她,怕再回到銀川,回到她爸和那个女人身边。
初中毕业,微米报考了市里的护理学校,半个月才回去一次。一直到她毕业,在市人民医院找到工作,就再也没有和她爸联系过。她好像又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个爸爸存在。她从没有问过她妈是谁,为啥他们结婚又离婚,为啥生了她又不要她……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就是在医院认识微米的。我生孩子住院时,微米是我的主管护士。第一眼见她,在白帽子、白口罩遮挡下,她的两只眼睛楚楚动人。微米长得像她爸,脸型、姿态,都像,唯有嘴巴不像。微米有一颗小虎牙,喜欢咧着嘴笑,不像她爸那样嘴唇紧闭,像故意跟谁作对一样。
从工作一直到后来再见到她爸,是微米最开心快乐的时间。她谈过一次又一次惊天动地的恋爱,却一直没有结婚。我说她有婚姻恐惧症,她笑了笑,并不否认。
忽然有一天,她爸回来了。
她爸在医院找到她。父女俩站在楼后的小花园里,很久没有说话。微米恍恍惚惚的,眼前这个人,真的和自己有血缘关系?
她爸说他退休了,卖了银川的房子,回来了,要和她一起生活。微米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爸说,那边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只有她。微米这才突然想起那个撵她走的女人。她呢?谁?就是你后来找的那个。早离了,她是个骗子。
后来微米才知道,她爸是两手空空回来的。他和那个女人离婚后,房子归了女人,他一直住在单位宿舍。好不容易攒了点钱,买了套小房子,又一个女人出现了。他再次结婚,然后离婚,失去了第二套房。所谓的退休,事实上是他和领导闹矛盾,拿刀子要和领导拼命。警察来了,他挥来挥去,误伤了一个警察的胳膊,被拘留了十五天。从拘留所出来,他就被单位开除了。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他才想起来还有个女儿。
你说他可恨不?
我一直记得微米当时的表情,大瞪着眼,虎牙把嘴唇都快咬破了。
4
下午四点多,微米打来电话,唐丽,你过来一趟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医院的太平间设在一个角落里。微米蹲在门口的雪松树下,一身黑衣黑裤。
出什么事了?我问。
人死了,讨债的来了。
什么情况?
今天早上突然来了一个女人,还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说孩子是我爸的,是老李家的苗,要分遗产。
真是搞笑,你爸还有遗产?
他们说的是老家的院子。你知道,我爷爷奶奶去世后,我爸从来没回去过,老屋房顶漏雨厉害,椽子也被虫蛀了。那个女人说他们要继承祖宅,否则就不让我爸火化。
哎,等等——她说那是你爸的孩子,你就信啊,从哪儿冒出来的?
她有结婚证,还有一张亲子鉴定。
微米向我示意,我看见不远处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女人,旁边站着一个孩子,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表情,一脸茫然。
我想起来了,李家的祖宅在他们县城棚户区改造范围内,那块地、那几间老屋,应该还是值一点钱的,女人和孩子显然是奔着这个来的。
你爸还真有本事,居然,居然……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微米的爸就在太平间的一个铁柜子里躺着,他的灵魂应该还没走远,会不会听到我说的话?我打了个哆嗦,冷。
还真是个棘手的问题,但这里也不是没有漏洞——她爸生前一直住在微米为他租的一间民房里,每个月微米给他一点生活费,他何时与这个女人结婚、还生了孩子,微米不会不知道啊?更何况这个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微米给的那点生活费也仅够她爸自己生活,怎么能养活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微米说脑子已经彻底理不清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对老屋的感情比谁都深,既不想拆迁,也不想被谁分走,她童年所有的快乐都在那里。
我上前问那个女人,你和李叔叔结婚也没几年,那房子是祖宅,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
女人面无表情,说出的话却很强硬,老李生前说过,老宅是留给儿子的。再说,他是李家唯一的男孩。
你看,能不能先让李叔叔入土为安,再说这个事?
我是他妻子,我说不行就不行。
微米冲女人说,既然你是他妻子,后事一切都归你了,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又对我说,我们走吧,不要管了。
微米拽着我的胳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直到坐在我的车上,她才泪流满面,压抑地哭起来:他们为什么要生我?就是为了折磨我吗……
我把车径直开出城区,过了黄河桥,拐上了一条盘旋曲折的山道,一直开到山顶,才停了下来。放眼望去,是无尽的山川沟梁,那些被植被覆盖的地方,生机勃勃,而那些黄土裸露处却荒芜苍凉。这里已经是另一个省了,我心里烦闷的时候,会经常一个人来这儿,要么在山上待会儿,要么在田野里走走,要么干脆坐在车里,什么也不做,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后,再开车下山。
人已经去世了,就别计较了。我试图劝慰微米。
你说,他这一辈子是不是就为了找我讨债?怎么处处和我作对,我到底欠了他什么?微米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
微米她爸回来以后,安静过大半年,他整日待在出租房里,几乎不出门,就在屋里坐着,看报纸,看电视,自己做饭自己吃。微米偶尔会去帮他收拾一下,给他带点吃的、穿的,也会给他留点钱,但很少跟他说话,她不知道跟他说什么。那种感觉怪怪的,一点也没有亲人的温情,他就像她负责照顾的一个病人。
大半年后,微米她爸突然变得喜欢出门,天天去公园,早上一趟,下午一趟,任何时候都穿得很齐整,衬衣、长裤、风衣、皮鞋,俨然一个体面的绅士。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他要钱的次数多了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陪微米去给他送钱。后来听微米说,如果钱送得不及时,或者钱少了,他会去医院找她,就站在病房门口等,一直等到她给了为止。最过分的一次,是微米刚值完夜班做好交接,准备回家,他来了。微米说兜里没带那么多钱,他却不肯通融,当下就要,让微米去给他借。两个人在醫院吵得不可开交,他甚至动手打了微米,直到病号家属报了警……那一次要钱的结果,是我从派出所把微米领回去的。
我一度怀疑微米她爸是不是老年痴呆,或者有什么精神问题,劝微米带他看病。微米说,她也这么想过,但一说去医院,他爸就生气,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说微米是企图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或者养老院,门也没有,让她别痴心妄想。
现在看来,微米她爸应该是那个时候与那个女人好上的,或者早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他需要钱,却又不能明说。
微米一直盯着远处,嘴唇紧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一刻,这个动作,和她爸真像啊。
手机响了,是刘会天打来的,他问我在哪儿。听到这句话,我就烦。为什么每次打电话,第一句话永远是问我在哪儿。
在单位。我说。
唐丽,你嘴里有没有一句实话?我刚给你办公室打了电话,同事说你接个电话就出去了。你到底在哪儿?
在山上,陪微米。
又是微米。刘会天不相信,说,你让她接电话。
凭什么?微米她爸去世了,我陪她上山散散心,你爱信不信。
唐丽,你怎么天天跟吃了炸药一样,能不能好好说话?
刘会天,你能不能有点正事?
给你打电话就不是正事?你被抓进派出所才是正事?到处乱跑才是正事?你也不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挂了电话,我恨不能把手机扔进沟里。为什么天天要面对这样一个男人?就像微米要面对她那个阴魂不散的爸一样。可是,她爸已经死了,她解放了,彻底解脱了。而刘会天,我还要跟他继续过下去,三十年?四十年?想到这里,我浑身汗毛竖立,打了个冷战。
离婚!这两个字,第一次在我脑子里闪过。
回到家,儿子在里屋写作业,刘会天在沙发上看电视,厨房是中午吃过饭后的一片狼藉。离婚的念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让我失去了和刘会天吵架的欲望,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想与他多说。我关上厨房门,慢慢收拾,洗菜、熬粥,准备晚饭。
吃饭的时候,儿子说起今天学校组织听讲座,一个教育专家给他们讲如何从高一开始备考。
专家怎么讲的?
哎呀,妈,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专家可逗了,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何伟洲,何是人可何,伟是伟大的伟,洲就是五湖四海的洲,哈哈。
有什么问题吗?
洲,洲啊,五湖四海的洲?
噢……我突然明白过来,不由扑哧一乐。刘会天也明白过来,哈哈大笑,儿子也跟着笑。
看着氤氲灯光下大笑的两个人,我又恍惚起来,这样的气氛是不是也叫其乐融融?我真的要打破它?更何况,两年后,儿子还要面临高考,离婚,会不会影响到儿子?
5
刘会天没有给我思考和犹豫的时间。他住院了。
他是被同事送进医院的。我赶到的时候,他躺在急诊室,医生在做检查。
同事说,我们和刘哥正说着话呢,突然他开始摇晃。问他怎么了,他说头晕,然后一下子就趴在桌子上了。嫂子,之前刘哥有什么病没?
没有啊,最近也没听他说哪里不舒服。
在急诊室门口,我坐立不安,心很慌。这是对我的惩罚?我才刚有离婚的念头,还没跟他说过,他就这么吓唬我?不,不会有事,不会有事的。我左手掐着右手的虎口,告诉自己,冷静,冷静。
家属,进来一下。
拉开白色的布帘子,我看到双眼紧闭的刘会天,胳膊上、腿上缠满了各种导线,手背上扎着液体。
医生,他怎么了?
初步怀疑是脑梗。病人之前有高血压史吗?
没有。
是没有?还是就没有量过?
应该是没有量过,他也没说过不舒服。
高压都180往上了,你们的心也真够大的。人过四十岁就应该定期体检,经常量血压了。
那,现在怎么办?
还好,问题不是很严重,住院吧,应该不会有后遗症。
我打电话向单位请假,又通知刘会天的妹妹赶紧过来,顺便给家里说一声。把他从急诊转到病房,他妹妹刘会霞也到了。我让刘会霞盯在医院,自己回家找他的医保卡,拿银行卡。
一路上,我不断提醒自己开车小心,但心里还是很慌,脑子里各种念头交缠着,此起彼伏。我强迫自己冷静,再冷静,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再说。
从早上离开家,也不过两个多小时,再回到家里,居然感到有些陌生。沙发,电视,跑步机,阳台上挂的衣服,沙发上儿子的外套,昨天晚上刘会天堆在茶几上的花生皮,掉落在地上的花生衣,餐桌上没有来得及盖上的蜂蜜罐,还有半个苹果……转了一圈,才想起来是要拿医保卡。
手机在包里响。是微米打来的,她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没有。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愣了一下,说,那,算了吧……就挂了。我顾不上她了,也不能给她说刘会天住院的事,她本来就自顾不暇了。
医保卡、銀行卡,刘会天的睡衣、拖鞋、剃须刀、洗漱用品……还需要什么?一时想不起来,算了,需要了再回来拿吧。
回到医院,护士已经开好了各种单子,刘会霞说她去办手续,让我看着她哥。
液体一滴一滴,不紧不慢,病床上的刘会天安静得像个孩子。我忽然觉得他的脸有些陌生,左侧脸颊上多了一块黄豆大的斑,一根眉毛似乎比别的都要长,头发细软,好像还有些卷曲。
另一张床上的病号一直在哼哼唧唧,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吃香蕉。他说话不太清楚,一说话就流口水,就那么哼哼唧唧地比画。照顾他的女人不像是他爱人,对他提出的要求从不反驳,也不跟他有任何交流。也许是个护工,虽然手脚麻利,但有些生硬。床头卡上写着脑出血,五十二岁,比刘会天大七岁。
刘会天一只手动了一下。我问他需要什么?他摆摆手。我伸出手,他抓住了,握着。我们俩就这样面对面,他躺着,闭着眼睛,我坐着,看着他。脑子里满满当当,各种念头纷至沓来,但这些念头刚刚出现就被我掐断了。每一条假设的路,都充满了恐惧。
刘会霞办完手续进来了,说,都弄好了。她盯着她哥看了一会儿,说,嫂子,没事的,我问过医生了,轻微脑梗。你别着急,我先回家给爸妈说一声,也让他们放心。中午妈做好饭了我给你送过来,放学了让爸去接轩轩,这几天就住那边,晚上我让磊子过来换你,一个人吃不消的。
好。
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小姑子被公婆宠坏了,好吃懒做,还啃老,啥都要从父母家里拿。为此,我很看不上她,也多次对刘会天和公婆表达过对她的不满。今天再看她说话办事,还真得佩服她,有条不紊,面面俱到。
嫂子,这边有事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啊。
好,辛苦你了。
刘会天应该是听到了我和他妹妹的对话,他的手轻轻捏了我一下,我也捏了他一下,表示回应。
6
十天后,刘会天出院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遗症,医生说再休息几天,就可以正常上班。他这突然一病,好像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重新来——我开始关注他的血压、血糖、血脂,关注一家人一日三餐油盐糖的摄入,蛋白质、蔬菜、粗纤维的比例,督促他按时吃药,每天拉着他和我一起锻炼。
儿子说,妈,你早就该陪我爸一起锻炼,他血压也就不会高了。
是,怨我。
刘会天看了我一眼,破天荒地没有顺着儿子的话抱怨我。不怨你妈,她喊我我没去,就像你妈以前说的,心懒身子沉,肥膘养闲人,怨我自己。这次突发脑梗算是给我提了个醒。
晚上在黄河边散步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微米她爸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最近一直没顾上问。
问问吧,微米也挺不容易的。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和我提起微米。
站在河堤上,远处有星星点点的灯光,我拨打微米的电话,居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事实上,从上一次她给我打电话,还不到半个月。也许,在医院的时间,不是用天来计算的吧,应该用分,用秒,用输液器上的水滴,用病人一根指头、一个表情的变化,一个含混不清的词语,一管血、一袋尿、一盒大便和一张检查单来计算,每一天,都格外漫长。
电话接通了,微米的情绪听起来还好,跟平常没什么异样。我问她爸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她说,都处理好了。她问我忙什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了刘会天一眼,说没啥大事,回头见面了细说。她说,不会是真和老刘离了吧?能凑合就凑合着过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都经不起挑剔,远看是青山绿水,仔细一看都是满目疮痍。我说,行了行了,别瞎说。最后我们约了周末进山休闲。挂了电话,我问刘会天去不去。他说,算了,你和微米去吧,在医院累了这么长时间,放松一下。
开车一直向南,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山区。天空蓝得很不真实,空气里弥漫着各种温热的味道,仔细辨认,有草香、花香、泥土香,还有牛羊粪便的味道,竟也是香的。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打开车窗,让风吹进来,伴随着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歌声。
目的地是一个叫九龙源的村子,村口有两株柯南树,村中央有一条小河,一个小小的賓馆,宾馆门口种了一大片红豆杉,还有一小片月见草。
月亮从山尖尖上冒出来时,我们看到月见草在五六秒钟的时间内瞬间开放,似乎能听得见那一声“砰”的怒放声,是真正的怒放。微米一直在惊呼,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老板娘告诉我们,沿河走走吧,河边有很多萤火虫。
我们沿着河边的石子路,向前走。月光清亮亮的,星星也很亮,很大;河道里、草尖上无数个光点闪烁;河水的声音脆而轻,小虫子和青蛙的叫声也很轻,但清脆玲珑,像在敲击马林巴琴。
走了很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微米先开口:我把老家的房子给小亮了,无论如何,他是我爸的儿子,是我弟弟。
你舍得?
不舍得。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爸已经死了,我还能怎么办?
是啊,微米又能怎么办呢?她爸死了,在太平间某个柜子里冻着,微米能做的选择,要么给房子,要么让她爸一直冻着。
我去收拾我爸的屋子给房东退房时,才发现他真的是一无所有。那么多年,他留下来的东西,除了衣服被褥,两个纸箱子都装不满。我找到了一张他和一个女人的照片,应该是我妈吧。他们好像只有那一张照片,照片里没有我。两个人都很年轻,朝气蓬勃。他们俩,看起来那么般配。
听得出来,微米在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黑暗中,萤火虫依然忙碌,月亮已经升到头顶,更亮了,却也更小了。我无法想象微米妈妈的模样,但能想象到他爸李明志年轻时有多帅。
我问过那个女人他们结婚的事,那个女人说他们是跳舞时认识的。她看他孤单,挺可怜的,就给他带自己做的小菜、包子、饺子。后来,是我爸非要跟她结婚,说想跟她有个家,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家的感觉。他们领了证,住在那个女人那里,后来生了小亮。
我极力想象微米她爸和那个表情漠然的女人,还有那个沉默的小亮,想象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样子,微米她爸会笑吗?会抱孩子吗?会去买菜吗?
你爸这个人……想到她爸已经去世,我打住了。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长得那么帅气,又有才华,可怎么一辈子就一事无成,到死了还两手空空呢?我真替他憋屈。微米说。
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在向前延伸,河道里的萤火虫也一直在向前延伸,月光下,隐约可以看见河对岸远远近近有几户人家,数盏灯火。
你不知道,唐丽,每见到那个女人和小亮一次,我就会原谅我爸一点。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尤其是面对小亮,看到他的眼神,看到他和我爸长得很像的那个嘴巴,我就狠不下心。
呃……可以理解。
我突然想到了刘会天,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也有那种奇怪的感觉。头一天还失望透顶,对自己的爱情和生活心灰意冷,对眼前的男人没有丝毫留恋,甚至巴不得他立刻消失,可第二天看到他突然病倒躺在医院,还是会紧张,会心疼,会不顾一切地照顾他。
我爸从来没有跟我提过我妈,一个字都没有。唐丽,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爸也不是不爱我,他只是恨我妈?
有这种可能。
微米说,我答应把老房子给小亮以后,那个女人的态度也缓和了一些,对我爸的后事忙前忙后,还让小亮给我爸戴孝捧照片,说以后让我多照看他。
你答应了?
答应了。
你爸的骨灰呢?
送回老家,埋在老院子的枣树下了,真到了拆迁那天再说吧。
嗯,这样……也挺好的。
我没有告诉微米刘会天住院的事,也没有解释那一段时间在忙什么,她也没问。很多事原本就像这河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遇到石头的时候会响一声,遇到沟坎就跳一下,遇到土丘就转个身,水总是要往下流,要找个归处。
越走越远,河道里的萤火虫也越来越多,有的顺水而下,有的逆流而上,闪闪烁烁,明明灭灭。这是属于夜晚的热闹和宁静。
责任编辑 杨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