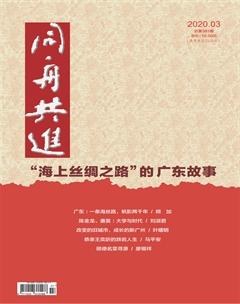岭海“船”奇:明代广东的财富钥匙
张嵚


16世纪初叶,那些乘着大航海时代的东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沿海的欧洲人,首先在自己日记里描绘的就是他们看到的“广东船”。明朝正德年间,当葡萄牙船队初次造访东南亚时,就在当地见到了大批来自广东沿海的中国商船。葡萄牙殖民者、《东方诸国志》的作者皮莱斯以绘声绘色的笔墨,描述了数千艘帆船在广州港聚集的盛大景象。嘉靖年间,一度客居广州的葡萄牙人克鲁兹也记录了广州河道上的各种船舶,有“无风时以巨桨驱动”的大船,还有鸟嘴型可以装载很多货物的单层甲板帆船。单是每天在河边看“蓬帆蔽日”的景象,就“足令人享受一番”。这些他们满怀新鲜感记录下来且曾在欧洲大陆引发火热风潮的文字,不止还原了当时中国的航运生活,更让古代广东制造的一件标志性产品——“广船”,悄然浮出历史水面。
中国古代造船业有“四大船型”之说,即苏船、浙船、福船、广船。而放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风云变幻史上,广船不但是老资格的见证,更是一代代国人劈波斩浪,征服万里海域的先锋。
海禁下的造船业
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广东的角色十分特殊: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徐闻古港,此后的两千年里,王朝更迭,但广东的海上贸易地位却扶摇直上。盛唐开元年间,地理学家贾耽就把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贸易网络誉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航线分为“东路”和“西路”,“东路”可达今伊拉克地区,“西路”可直达红海沿岸的东非地区,连接起亚非的海路航线。
在大唐“安史之乱”后,这条海上贸易航线蓬勃发展,成为中晚唐重要的财富通道。广州的经济也突飞猛进,从此“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植根于如此“黄金地带”的造船业进入了繁荣期。也同样是唐代起,广州与泉州成为中国两大海船建造基地,以“首尖体长”和“吃水深”著称的广船脱颖而出,与福建的福船一道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标志。
无论是在唐宋年间的中国典籍还是阿拉伯旅行家的笔记里,该时代的中国船都是亚非海洋上神奇的存在:船体大,续航能力强,能把中国的宝货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四方。由于船体太大,当中国船抵达波斯湾时,甚至无法直接进港,只能换成小船。而广船更是中国船中的佼佼者,比如出土于印尼的南汉王朝沉船就是那个时代广船的代表,其先进的船体设计与船上巨额的财富,无不惊艳世界考古界。
也正因为名声在外,所以,当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船队终于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东方航线时,他们对于传说中的“中国船”抱有满满的好奇心。明朝正德三年(1508)六月,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发出训令,命令即将远航东方的葡萄牙舰队必须要用各种办法,弄清楚中国船只的吨位与性能,然后才有了上文皮莱斯笔下对广船的各种生动描述。
当然,葡萄牙国王的训令绝非出于纯粹的好奇,葡萄牙船队远征东方的背后,是勃勃的殖民野心。皮莱斯在对广船进行了一番描述后,发出了狂妄的判断:“(葡萄牙)船队中的一艘船便可以轻易击溃二十艘中国帆船。”在他看来,广州港口那上千艘帆船,也不过是一堆“肥肉”。
曾经享誉世界的广船真是如此脆弱吗?其实,彼时正是广东造船业的低谷期。明朝从开国起就关闭了国门,严厉的海禁政策给了造船业重重一击。虽然大明朝曾有“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也曾拥有技术水准登峰造极的“宝船”,但对于曾经旺盛的民间造船业,朝廷掐得很紧,民间的船舶被严格限定尺寸。特别是永乐二年(1404)起,民间船舶一律改成适应内河航运的“平头船”,以“尖底”为特点,而适合远洋破浪的广船几乎绝迹。
曾缔造“郑和下西洋”辉煌的官营造船业也随着“下西洋”的终止而日益裹足不前。官营船厂的技术工艺在15世纪下半叶几乎是一代比一代倒退。明朝弘治年間,当大洋彼岸的达伽马哥伦布们一拨拨启航去探索未知领域时,最强的官营船厂龙江船厂受命制造大型海船,结果花费白银一万五千两,却造出了“不堪驾远”的残次品,贻笑大方。
明正德十六年(1521),对葡萄牙殖民者忍无可忍的朝廷决心调集广东地区的主力船队去清剿盘踞屯门的葡萄牙舰队,但此时广东水师的账目上有的只是一份惨淡的家当:大型战船不过20条,剩下的多是临时征调的民船;就连参战士兵也大多是从沿海渔村征调的民兵;即便是“大型战船”,比起葡萄牙舰队的船舶也是不堪一击。当时葡萄牙舰队乘坐的船舶被中国人称为“蜈蚣船”,即欧洲人常用的桨帆船,这种船只长度40米左右,能装载大小火器30多门,无论火力还是航速都远远优于明军战船。
侥幸的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由于葡萄牙舰队里的华人工匠杨三等人幡然悔悟,冒死来到明军军营,带来了葡萄牙的火器制造技术。临时换装新式火器的明军才凭借着兵力优势,将葡萄牙舰队艰难地逐出屯门。
其后,在“嘉靖倭乱”里,同样获得西方新式造船技术的倭寇们也迅速升级了自家的船舶,甚至对沿海“正规军”水师形成了绝对的海上优势。“倭寇王”汪直在广东高州(今茂名市)建立造船基地,将传统的广船技术与西方造船技术相结合,造出了新式的“巨舰”,其主力战舰甚至“方一百二十步,客两千人……可驰马往来”。凭着一支强大的舰队,汪直一度纵横中国东南沿海,甚至在日本萨摩洲松津浦建立领地。
迎来重生
就在这样一个倭乱深重、走私活动猖獗的年代,萎靡已久的广船产业却在悄然复苏,愈发发达的海上活动成了广东民间造船业的催化剂,沿海的民间船厂,无论是工艺水平还是规模,都在直线升级。曾在明王朝森严限制下沦为“小船”的广船,终于迎来重生。
当时的广船往往被称为“乌艚船”,分为“尖尾船”“横江船”等多种型号。“广船原系民船,由于明代东南沿海抗倭的需要,将其中东莞的‘乌艚、新会的‘横江两种大船增加战斗设施,改成为良好的战船,统称‘广船。”广船的帆形如张开的折扇,与其它船型相比最具特点。为了减缓摇摆,广船采用了在中线面处深过龙骨的插板,此插板也有抗横漂的作用。为了操舵的轻捷,广船的舵叶上有许多菱形的开孔,也称开孔舵。广船在尾部有较长的虚梢(假尾)。
广船多用热带硬木,如铁力木(柚木)制造,坚固耐用,寿命有达60年之久的。不过,《武备志》对广船的缺点也有客观评价:“广船若坏须用铁力木修理,难于其继。且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海则动摇,此广船之利弊也。”
即使与“高大如城”的福船相比,广船的体魄与坚固性都占绝对优势,广船坚硬的船体,不但能在海面上撞碎对手,更适合配备重型火器。《明史·兵制》对广船的评价是:“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对于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船只,广船更是天然的克星,很多时候,广船遇上倭船,甚至连开火都省了——直接撞过去就能把敌船碾碎。
于是,明王朝痛定思痛,开始重建沿海水师,民间船厂出品的广船也越发得到重视。大量广东民间船厂制造的广船被编入明军水师的战斗序列里。比如抗倭名将戚继光麾下就有大量广船助战;单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就有180艘广船受命北上,参加浙江沿海的剿倭战争。
由于水师的重建,嘉靖晚期的明王朝改变了以往的海防思路,在广东沿海组建了五大水寨,配备大小战船数百艘,形成了一道强大的“海上长城”,坚固且火力强大的广船成为水师主力。强大起来的明朝水师终于令肆虐数十年的倭乱销声匿迹。
更让人震撼的是,在16世纪晚期的万历朝鲜战争中,明代将领陈璘率领上万广东水师决战日本舰队。在露梁海战中,生猛的广船成了急先锋,将500艘规模的日本舰队切割得支离破碎,450艘日本军舰葬身露梁海。这一仗,打出了东北亚海洋近400年的和平。
与广船纵横海疆相对应的,是海禁政策的松动。在此之前,虽然广东的对外贸易已经十分火热,但商船出海依然被严厉限制。终于,隆庆元年(1567),史称“隆庆开关”的国策推行,福建月港放松了对船舶出海的限制,广州随之跟进。虽然依然要经历苛刻的盘查,但当地的商人终于可以驾着中国船正大光明地出海了。在海洋上大显身手的广船也有了新的使命:赚全世界的钱。
“帆绰二洋,倏忽数千里”
对于倭乱结束后的广东来说,“走出去”有多重要?可以先看看当时的广东蕴藏着多少“宝货”。
虽说中国古代的东南海上贸易航线常被统称为“丝绸之路”,但放在此时的广东,能在国际市场上做“硬通货”的,并非只有丝绸一种。明朝民间就有“苏州样广州匠”的俗话,意为广州手工业的技艺冠绝天下。很多在中国看似寻常的产业,当时都有着高额的国际贸易利润,比如蔗糖业。明朝中后期,由于“黄泥水淋糖法”的推广,以及甘蔗等作物在广东的普及,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重要的制糖中心,各种品牌的“广糖”畅销大江南北。而在同时代的西方,由于制糖技术落后,白糖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在英国,王室贵族只有在生病时,才能享受一口白糖。
由于制糖业的繁荣,连带制糖所需的铁锅也成了一项重要产业。以佛山铁锅为代表的“广锅”,长期以过硬的质量驰誉天下,甚至在与北方鞑靼部落的“互市”里,被明朝首辅张居正列为“专用货物”。放在海上贸易航线上,铁锅是名贵的产品,一口佛山铁锅卖到日本,价格就翻成一两白银。
这样的宝货如果可以直接走出国门,必然能带来高额利润。于是,广船就成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明朝中期起,官营造船业日益衰退,就连明朝水师的战船乃至册封属国所用的“封舟”,也都“转包”给了民间船厂建造。“隆庆开关”后,财源滚滚的海上贸易给造船业带来了无限商机。许多有眼光的广东商人往往采取“合股”的方式凑钱打造民用商船。这些商船往往是“千斛以上”的巨型船舶,造价不菲。以万历年间学者张燮的估算,同样订购自民营船厂,一艘明军水师主力战船的造价往往只是民用商船的1/3,還不包括商船的维护费用。
下血本的建造换来的是丰厚的收益。正如明末清初的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所说,当时满载着铁器、白糖等货物的广船来往于日本琉球、吕宋、南洋等地,“帆绰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
“大赢”是多少?万历年间,单是在西班牙人控制下的菲律宾,每年上百艘中国船只能从西班牙人手中赚走价值100万比索的财富。以至于到了1598年时,马尼拉大主教向西班牙政府叫苦:“这些钱都流入了中国人的口袋。”以当代西方学者弗兰克《白银资本》里的估算,从明朝中后期至明亡,全世界至少1/4至1/3的白银流入了中国。
明朝“隆万中兴”的辉煌乃至白银货币在明朝中后期的重要角色,几乎都来自这场贸易热潮。而乘风破浪的广船,亦是这个火热时代里公认的财富钥匙和强国标志。虽然17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再度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但广船以及与广船有关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却依然是历史上一抹别样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