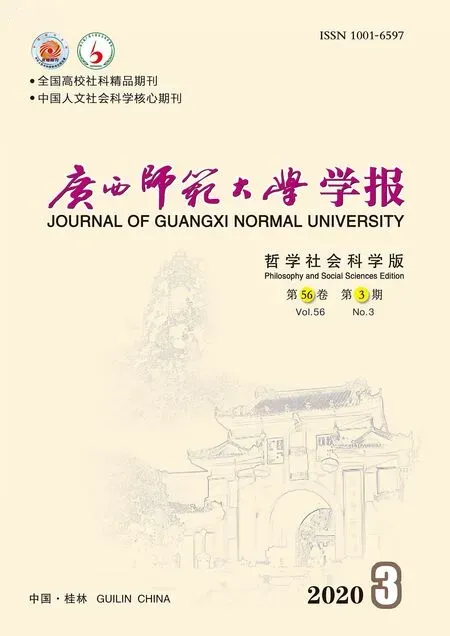中国农民务工流动幅度、地域选择与“农民问题”破解
朱新山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今日中国农民外出务工是普遍现象,“农民”相当比重在职业上已经非农化而且成为流动中的人口。不过,关于农民务工流动与地域选择的具体情形与特点,需要结合实证调查才能揭示清楚。本文拟通过全国66个村庄的具体调查和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外出务工流动幅度、地域选择与破解“农民问题”困境的关联性。
一、农民务工流动幅度分析
众所周知,农民的本职原是务农,鉴于中国地少人多的特殊国情,“农民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通过“非农化”的途径。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农村稀少,中国农民的非农化主要表现为外出务工,因而就存在“农民务工流动幅度”问题。
当然,农民(务工)流动及其幅度,主要是个“现代”问题。因为传统乡土社会基本上是静态社会,农民社会身份的变动甚为轻微。尽管历史上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但其更多是鼓舞人心的传说。因此,正如费孝通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7由于世代定居,人口就在一定地块上堆积起来,越积越多,进而造成人均耕地不断减少、谋生困难的局面,因而古代中国就形成“耕织结合”(以补土地产出不足)的传统。反过来,耕织结合会进一步强化农业的自给自足与定居性质。因此,中国农业与农村很早就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正如黄宗智所言:中国农村长期“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造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局面。[2]73-74针对中国农村,黄宗智创造性地区分了“扩大产出的‘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与要害正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农业总产出有所扩大,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全然无改进”。[2]73毫无疑问,中国“农民问题”破解的真正启动,始自改革开放,始自农民的务工流动(农民不再窝在土地上浪费时间,其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本文提出的“农民务工流动幅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务工流动幅度”反映农民的非农化程度,体现“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这首先直观地反映在“农民打工人口占比”上。
笔者牵头的课题组围绕“农民外出打工及流动人口占比”问题,展开了深度调查。不过,要获得一个村庄外出打工人口情况的准确与详细数据(包括打工人口数量、流向与职业等),需要对照村庄户口簿找知情人(尤其是村庄会计与书记等)逐一详细询问登记,这是一项有挑战且艰巨的工作。课题组2016年和2017年调查了全国66个村庄,有7个村(为降低调查难度部分下沉到自然村)的调查获得打工情况的精准数据,10个村获得了干部为主的估算数据,分别列表如下(见表1与表2)。

表1 六省7村村民外出打工情况调查(精准数据)
说明:乘黄村、天阁村、夏辛村与旺台村为课题组2016年初调查,骡驮村、项西村与新丰村为2017年初调查。

表2 七省10村村民外出打工情况调查(打工人口占比由村干部与村民估算)
说明:石门村、石子村、石村与南黄村为课题组2016年初调查,龙飞村、张孔村、袁村、西河村、北星村与高柳村为2017年初调查。
从表1、表2看,课题组2016年与2017年两轮务工流动调查覆盖的地域较为宽广,具体包括中国东部3省(冀鲁浙)5村、中部4省(晋豫皖赣)7村、西部2省(川贵)5村,共计17村。从17个村的调查数据看,中国农民外出打工的比重相当高,调查的全部村庄均有超过1/5的人口在外务工。其中,超过1/3的人口在外打工的村庄有11个,占调查村庄总数(17个)的64.7%。外出务工人口占比最高的为安徽阜阳的北星村、山东莱阳的高柳村与江西金溪的夏辛村,均达到村庄人口的60%(或接近60%),可以说,三村村民处于非农就业为主与高流动状态。外出打工人口占比最低的为贵州三穗县天阁村,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少数民族村寨,也达全村人口的23.4%,接近1/4。这说明,地处高原、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也高度卷入外出务工与流动大潮。
课题组将云贵高原的民族地区作为入村调查的重点之一,因为这里地处大山深处,交通困难、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通过深度访谈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进行全国农村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参照。三穗县位于贵州东部边缘,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人口以侗族、苗族为主体,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5%。天阁村位于三穗县城东南两公里,四面环山。现在的村是2015年由两个行政村合并而成(下分11个村民小组),包括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聚居的7个自然村寨,村庄人口(2016年初调查)1758人,耕地面积1420亩。村庄人多地少(人均耕地0.8亩),农业生产仍靠传统方式耕作,很少使用机械,生存压力较大。青壮年多数外出打工,成为改善生存状态的重要选择。调查显示,他们多数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主要从事纺织、服装、制鞋等工作,部分在建筑工地干活或开车。外出务工收入是村内务农收入的2.5倍以上。再如台江县(号称“天下苗族第一县”,全县人口17万,苗族占95%),位于黔东南州中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课题组调查的秀山村地处台江县城区,2017年初人口为3580人(其中苗族3500人),耕地1500亩(原有1800亩,300亩征为城市规划用地)。由于县城太小,经济带动能力不强,因而相当多的村民选择外出打工。2017年1月课题组成员入村访谈时,村支书欧德荣(41岁)反映,村中青壮年有七八成外出打工。男的大部分当建筑工人或进皮鞋厂、电子仪器零件加工厂,妇女则选择进手工艺品加工厂或茶叶加工厂等。不过,近年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秀山村大力发展传统苗族刺绣和精品水果种植项目(项目由政府拨款资助),在外打工的部分人又回来了,既能赚到钱(刺绣做好后,拿到村里专门的地方统一卖出去),又能照顾家庭。可见,本地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机会少,是村民走出去的重要原因。再看更为偏僻的黔西盘县石门村,2016年有人口1579人,耕地840亩,村民构成主要包括汉族、彝族,外出务工人口也达三分之一。该村地处乌蒙山区南段,地势崎岖,平均海拔1650米,居民分散而居,形成多个相互隔离的小寨子。村庄宜于耕种的土地分散,难以集约化生产。村民反映,最主要的困难在于经济方面,没有固定的收入,搞农业地少(人均耕地0.5亩)、成本高,也没有出路。村干部曾想引进新品种核桃种植项目,预计面积20亩(最终还没搞成),如此规模,想带动村民发家致富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改善生存处境,只有走出去。
调查发现,“种地没出路”(关键原因在于一家一户地块太小),是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基本动因。这可从农民种地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看出来,下面以河南新乡张孔村(行政村,2016年调查)为例作分析。张孔村全村有2536人,耕地2490亩,人均0.98亩。一个五口之家,也就约有5亩地。通过对村支书及多位村民的访谈,我们了解到:该地主要种植小麦与玉米,一年各收获一季,1亩地毛收入2000元(种小麦与玉米收入各约为1000元)。而成本包括:每季每亩投入的“粮种、化肥农药、灌溉收割等费用”为200元(小麦、玉米各一季,共计400元);秋后耕地一次(每年玉米播种在小麦收获之前,因此中间不需再耕地一次),每亩100元。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包括:种粮补贴77元/亩,粮种补贴15元/亩。算下来,一亩地加上国家补贴在内的毛收入为2092元,而成本为500元。扣除成本(农民的劳动投入未计入成本),一亩地净收入为1592元。张孔村一个五口之家种地5亩,一年的农业净收入为7960元,人均1592元。可见,如果没其他收入,村民必处于贫困状态。如此一算就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坚定地离开土地去打工的原因了(村支书黄彦丽估算2016年张孔村人均纯收入为5000元,可见务农收入不足三分之一)。
从国家宏观层面看,农民务工大军驰骋全国,中国农民非农化普遍发展,已形成较为壮观的局面。2019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农民工(拥有农村户籍年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者)总量为28836万人[3]。不过,当代中国农民非农就业也有脆弱与不稳定的特点。安徽阜阳北星村(行政村,2017年人口3322人,耕地2954亩)金姓会计对村民务工特点的概括就有代表性:“村里约有五分之三的人在外打工,主要在城市工地上做苦力或收废品。有些人无固定场所,哪里有生意门路就去哪里。”总体来看,外出农民大多从事工厂操作工、建筑工、饭店(宾馆)服务员、保姆等较低端、出体力的工作;收入也偏低,年收入多在三五万元;他们进了城但落不了户,家乡仍有诸多牵挂。河南驻马店新丰村(自然村,2017年人口258人)村民吴盼(女,32岁)的打工情况就比较典型,下面是课题组成员对她的访谈片段:
问:你们打工一般去哪些地方,做些什么工作呢?收入怎样?
答:一般去广州、上海等地的电子厂,做一些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比如组装零件、擦拭产品等基础工作。工资不高,只有2000元左右,全靠周末节假日加班工资翻倍,每月才能拿4000元左右。我就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好好上学,随随便便上个大学也能做份差不多的工作啊。
(访谈时间、地点:2017年1月10日,新丰村村民家中)
应该说,吴盼的打工情形是个缩影,具有一定普遍性。调查发现,村民外出务工较“成功”、收入较高的,多为“自我做老板”型的。譬如,江西金溪夏辛村(自然村,2016年调查),虽然在外打工的人很多,但“干得最好的”是“在外做面包的那几家”。课题组成员入村访谈时,该村会计及几位村民反映:“从夏辛走到大城市混得好的那一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做面包的,他们少的在外面待了五六年,多的甚至有十多年,有好几户都是全家在外面做面包,收入可观。如村民车康南在贵阳做面包(兼做蛋糕)已七年,开了两家店(与妻子各打理一家)。店里请了几个员工帮忙,每家店每年都有十到二十万元的利润。”然而,这种“自我做老板”型的毕竟是凤毛麟角,并不代表农民外出务工的一般情形。
毫无疑问,农民务工流动幅度大幅提升与非农化普遍发展,展现出中国“农民问题”解决的光明前景。不过,农民非农就业的脆弱与不稳定,也决定了这一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曲折性。
二、农民务工地域选择分析
中国农民务工地域选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农民问题”解决的思路。调查发现,目前村民外出务工的地域空间已经相当广阔。河南永城石子楼村(自然村,人口70多户,近300人)村民打工地域分布就比较典型,下面是2016年1月18日对该村老太太刘秀景(68岁)的访谈片段:
问:村里出去打工的大概有多少人啊,都去哪些地方?
答:全国各地去哪的都有,因为南方的厂子多,所以去浙江那一片打工的更多,其他还有去上海、山东、新疆的,算下来得有五六十口子人吧。
问:那你知道人家在这些地方具体都是做什么吗?
答:人家在外边,有在机械厂的,有在鞋厂、电子厂的。还有做门窗生意的,反正人家都有自己的门路。
问:外出的人跟不出去的人相比,经济收入是不是要高?
答:反正指望着在家种地是赚不了几个钱的,人家只要出去就能赚个三四万。打工虽然赚不了大钱,但还是要比在家好得多。在外面做个生意也不错。人家回来,都把楼盖上了,有的把车也买上了。
(访谈时间、地点:2016年1月18日,石子楼村村民家中)
刘老太太所说村民打工“全国各地去哪的都有”,可谓“遍地开花”,体现了今日中国农民奋勇打拼的局面。调查发现,本地域产业基础越薄弱、生存压力越大,村民外出打工的冲动越大,打工地域范围就更广,活动半径也更大。江西、河南、安徽、贵州的受访村庄,均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趋向。
关于打工地点的选择,村民一般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先本地县城、城镇,再区域性经济中心,更或全国性经济中心(北上广深)。
为发现规律,课题组对江西东部金溪县夏辛村(自然村)村民打工情形展开了“麻雀解剖式”调查。夏辛村地处丘陵地带,人口有268人,耕地326亩(人均1.2亩),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甘蔗等。该村北距县城10公里,有平坦水泥公路相通,交通方便。由于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大,外出寻找工作机会就成为村民普遍的选择。2016年,该村有156人在外打工(见表3),占总人口的58.2%。村民打工的地区,东到上海、温州,南到深圳、东莞,西到贵阳、重庆,北到北京,四至均在700公里之外,甚至达到2000公里。

表3 江西金溪夏辛村(人口268人)外出打工人员(156人)地点分布
资料来源:课题组成员2016年调查。
由表3可见,夏辛村在一线城市(北上深)打工的有8人,占外出打工人员的5.1%;在二三线城市(东莞、重庆、贵阳、厦门、南京、义乌、温州)打工的有63人,占外出打工人员的40.4%;在四五线城市打工的有11人(江西的城市除南昌以外,都属于四五线及以下),占外出打工人员的7.1%;在本县县城(金溪县城)打工的最多,有74人,占外出打工人员的47.4%。
可见,本县县城(或就近城镇)往往是村民外出务工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也预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中国“农民问题”解决的努力方向(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并为农民进城落户积极创造条件)。中国东部山东、浙江一带,工业发达,企业多,村民一般选择在本省就近就业。譬如,山东莱阳高柳村(行政村,2017年2月调查),地处胶东丘陵,人口1700人,村民有60%务工经商,但很少有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而大多选择就近在莱西城区工作(收入至少一年3万元)。山东东营小宋村(行政村,2017年人口1050人),地处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村民收入模式为务农加打工。年龄大者在家务农,农闲时进城做绿化,或打扫卫生;年轻人则就近在东营城区打工,主要集中在超市、商场、工厂。再如山东潍坊昌乐县贵和村(行政村,人口1580人,2018年调查)也是如此,村民大多选择就近打工。下面是对该村支部书记兼主任刘锡(63岁)的访谈片段:
问:村里现在还在种地的人有多少?
答:现在没有专门种地的了。一般就是种下麦子之后,就不用管了,都出去打工挣钱了。
问:都是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呢?
答:基本上都是去县城,一两个在潍坊的。像是些小青年、小妇女的,就在城里打工,干什么服务员之类的。上了年纪的,甚至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就去环卫、绿化带上干。反正没有说是等着光种地的。
问:那有没有出去到大城市打工的?比如北京、上海之类的?
答:没有,都是就近的,最远的就到潍坊里头。没有出去那么远的,那种整年在外面的没有。
问:咱们村里有没有村办企业?村民有没有自己办企业的?有没有外来投资的那种呢?
答:没有,这个村属于比较落后的那种,这些都没有。
(访谈时间、地点:2018年2月22日,村委会办公室)
再看浙江农民的务工情形。台州旺台村(行政村,2016年调查),靠近临海火车站,背山靠水,风景宜人,人口有1462人,耕地874亩。该村务工人员有658人,占村庄人口的45.0%。2016年2月12日接受访谈时,妇联主任方荷菊(兼支委委员)说:“村民一般在村子附近打工,基本没有出远门打工的,可能我们浙江这边轻工业比较发达,不缺工作机会,工资待遇也很不错。”而中国中西部地区如安徽、江西、四川等,由于本地产业基础薄弱,农民出远门打工的就多,务工地域就更广。
当然,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体现了高收入水平城市对农民的(从土地上)拉出效应。与此同时,由于农业耕作与收割加工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农民用在农业经营上的时间不断压缩(加之地块太小),科技对农民的(从土地上)挤出效应亦日益明显。譬如,鲁中康村(行政村,2017年人口845人)一带,一年小麦与玉米各收获一季。农民耕地时一般是花点钱请人用大型拖拉机代耕,收割时则请人用联合收割机操作并脱粒,最后把收下来的粮食直接装到麻袋里就可以了,因此,康村农民一年用在农作上的时间最多不过一两个月,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外出务工。可以想象,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取得进步,农民务农的时间还可以压缩,而外出打工的时间会更长,活动区域会更宽广。
毫无疑问,农业耕作与收割加工技术不断进步,还为土地的规模经营与集约使用创造了条件。江西金溪夏辛村“种田大户”车卫国(42岁,在家务农),夫妻两人“轻松”经营土地69亩(种水稻),年纯收入五六万元。再如,河北唐山西河村(超大自然村,人口1万余人,2017年调查)翟某一家(3口人,孩子上高中),“耕种了100多亩土地,主要种植棉花和玉米。农作物收成好价格高的话,一年可以赚到二十几万元,差点也能赚十几万”。调查发现,如果一户农民能够经营耕地六七十亩或水面15亩,那么,其务农收入就可达到相当于外出打工的水平。如果种地能够达到一两百亩或更多(目前的耕作技术已不是问题),那么收入就比一般打工好许多。
然而,目前中国农民中冒出的“种田大户”仍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农民外出务工与留村扩大土地规模经营之间尚未形成良性循环。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民的“非农化”尽管普遍发展,流动地域亦宽广,但仍比较脆弱,尤其是在有效融入城市方面存在一定障碍。
三、“农民问题”破解的中国思路与特色
结合上述中国农民务工流动幅度与地域分布规律的研究,我们应该从“农民从农业(农地、农村)转出”“如何转出(转向何处)”及“农民剩余人口基数仍甚大”三方面,来考虑中国“农民问题”解决及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路径。
(一)鉴于地少人多及农民人口极为庞大的特殊国情,中国要坚定地走持续减少农村人口比重与稳步城市化的路子
毫无疑问,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本质与核心是“农民问题”,即农民占中国总人口比例过大的问题,也就是“农转非”问题。如果不能把大多数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转移到城市,中国的人均收入就会继续大幅度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就仍然是“农民国家”,仍属于穷国之列。[4]397其实,费孝通早在193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就讲了农村“无工不富”的道理。他在该书最后的结论部分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5]201其后,他在1940年代出版的《禄村农田》一书中也指出:“中国已开始工业化了,这大概是无法避免的路子。”[5]226可见,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路径。
当然,农民“农转非”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就地工业化,二是转入城市,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鉴于非农就业机会农村稀少以及乡镇企业(就地工业化之形式)早已完成使命并转制(加之这种遍地开花的乡村就地工业化“规模不经济”且“消极外部性”太多),目前中国农民的非农化就主要表现为外出务工与城市就业。因此,要稳步提高农民务工流动的幅度与比重,因为务工流动的幅度与比重越高,农民被城镇有效吸纳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建立以县城与小城镇为重点的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吸纳机制
根据农民外出务工发展趋势及区域分布规律,要尽快建立以县城与小城镇为重点的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吸纳机制(并根据条件逐步推进到二三线城市);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到户的进程,为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顺畅流转以及把农民引向土地以外的广阔空间创造条件。潘维指出,中国人均一亩地的小农经济,种地养殖可以丰衣足食,甚至还可能略有节余,却不可能创造足以同工商业相匹配的“利润”,不可能让中国的农民“致富”。一亩地只有0.16英亩,和美国普通人家的院子差不多大。没人指望美国人靠耕种自家后院来获得人均3万美元的收入,而寄望中国农民靠一亩地致富、追赶发达国家更是不可想象。美国的耕地面积大于中国,但农民的数量不到20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远低于1%。如果中国只剩下2000万农业劳动力,农业在中国当然是“产业”,不愁赚钱。然而,剩余的4.8亿农业劳动力靠什么生活呢?归根结底,家庭农业不是问题,人均一亩地的家庭农业才是个问题。[4]399因此,必须积极创造条件,统筹城乡发展,稳步推进农民的“农转非”。已有研究发现,“流动性移民”(进城农民工)“一方面对所在城市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准备将自己作为一个很多人想要他们成为的‘临时居住者’”[6]132。尤其是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从小就在父母打工的城市生活,熟悉和认同城市的文化与价值,而对乡村(父母之乡)反而完全陌生且缺乏农业谋生的基本技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农村已较为突出地存在青年农民“农业冷漠化”与“种地老人化”现象,“乡村凋敝”的迹象开始显现。毫无疑问,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治本措施,是在农民出村务工与留村扩大土地经营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进而最大可能地把农民引向土地以外的广阔空间。唯有如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才能稳步减少,中国农业才能由传统农业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高投入高产出、专业化的家庭农场农业),中国农村才有可能实质性摆脱贫困并进入现代化。
(三)乡村振兴亦是中国“农民问题”破解及中国特色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鉴于农村人口基数极为庞大的特殊国情,中国乡村不能凋敝,中国要走稳步城市化与乡村振兴二轮驱动的现代化路子。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节点),再用30年,中国将目前农村常住人口的大部分有效转为市民,任务极为艰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为8.31亿人(包含2.41亿进城农民工),乡村常住人口为5.64亿人[7]。假设目前中国人口总数(13.95亿)长期维持不变,到2050年,如能在将现有2.41亿(进城)农民工全部融入城市的基础上,再有效市民化3亿农村常住人口,就已经居功至伟了。算下来,每年要有效市民化1803万农村人口,然而,2018年中国乡村常住人口实际减少仅1260万人。不过,就算能这样(最乐观的估计),届时中国农村常住人口仍剩2.64亿,毫无疑问,中国仍为世界排名居前的“农民大国”。可见,留守农村的庞大人口及薄弱的农业仍是中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所说,“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效率的经济部门”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心议题之一。他指出:“的确,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对于农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8]4-5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模仿西方,中国农业(发展“大农业”)的“强大发动机”需要点燃,乡村振兴应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与“农民问题”破解的题中之义。
当然,要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科学认识、深入把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的支点则在因地制宜发展新型特色乡村产业。因此,要立足各地不同的乡村资源禀赋与独特优势,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像农产品原材料丰富的乡村,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产业发展,不断延展农业产业链,把农业附加值留在农村;农业生态资源丰富的乡村,可利用生态优势,合理开发利用农村空置住房,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乡村养老养生等产业;交通条件好的乡村,可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特别是要鼓励和支持发展“一村一业、一村一品”,推动不同乡村立足不同优势资源、形成不同的产业和专业特色[9]。当然,“乡村振兴”不能把产业“硬塞”给农民,要注重示范、服务与引导。要引导和支持农民在特色产业发展中找到收入增长的途径,针对不同的农民群体要有不同的带动方式:对于独立经营能力较弱的小农户,可引导其加入合作社或与龙头企业相结合,使其投身到特色产业链上的某一环节,实现抱团发展、联合发展;对于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特别是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可加强扶持引导服务,帮助其有效开发本地特色资源[9]。因此,通过进城务工并有效融入城市,降低农村人口比重;通过乡村振兴、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逐步做富做强乡村。两者紧密结合,彼此推进,中国“农民问题”可望走出有效破解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