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展示的图像:人类世中观看的欲望
伊姆加德·埃米尔海因茨(Irmgard Emmelheinz) 译者陈荣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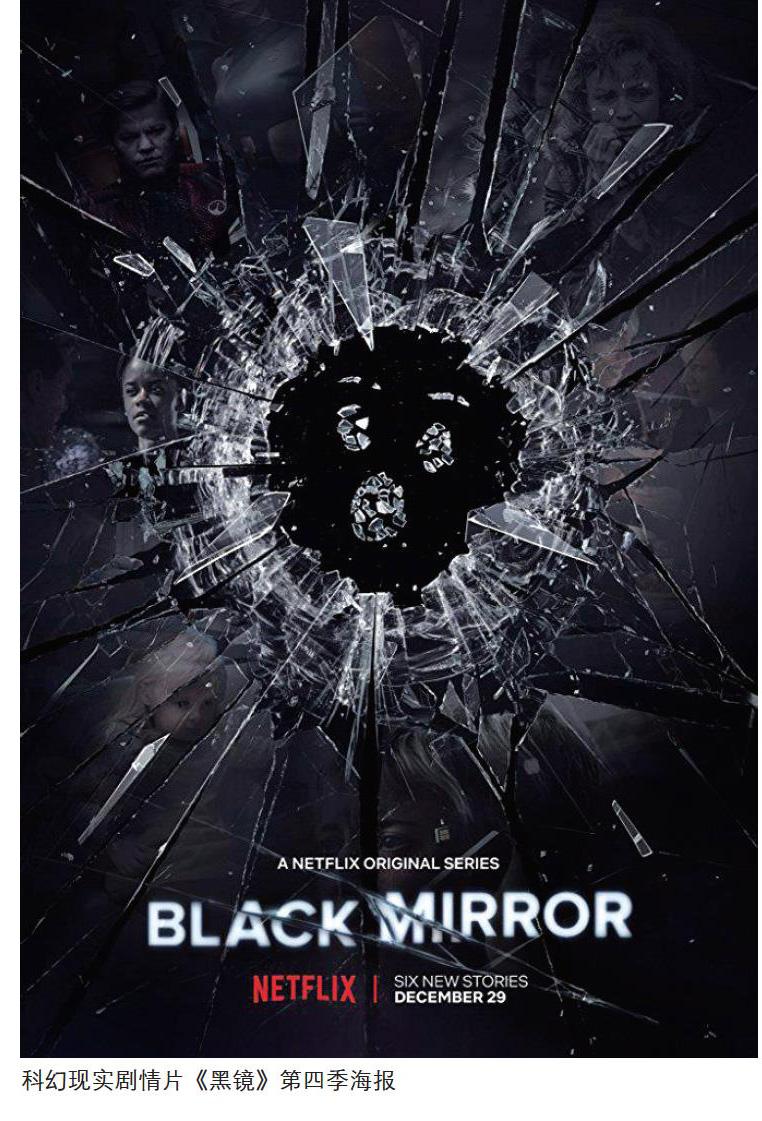
人类世这个时代,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变得如此强烈。我们见证了海洋和气候的变化、若干物种的消失,同时也将人类自身置于毁灭的边缘。人类世宣告了未来的瓦解:“迈向原始主义的缓慢分裂,永久的危机和行星生态的崩溃。”人类世没有被想象成未来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抽象图景,相反它已经沦为人类和世界终结的末日幻想。过去十年间,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2011)等电影将世界的尽头描述为启示录的、末日的叙事,可能以某种道德救赎告终,也可能不会。与此同时,大众媒体把气候变化描述为一场“可修复”的灾难,就像其它灾难一样,似乎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相当。总之,人类对地球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长期的地貌影响已经变得难以理解。
我将在本文指出,人类世不是一种世界的新图像。相反,它首先意味着视觉条件的根本改变。其次,它把世界变成图像。这些势态既是现象上的,也是认识上的结果。图像参与世界的形成,同时它们也成为构成新知识的思想形式。这种形式的知识建立在视觉交流的基础上,因此依赖于感知,伴随光学思维的发展。正如我们所见,图像已经获得了“现存”(the extant)的地位,也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数字媒体)。人类世视觉系统的这种变化意味着自动化,意味着同义反复的视觉对象,以及导向其它符号的符号。这导致了图像的扩散,同时意味着视觉的消失。
立体主义最终导致了反人文主义的断裂,在超现实主义手法的支持下,将视觉对象转化为“表现”“事件”“症状”和“幻觉”,而实验电影则带来了机械的、后人类的眼睛,在感知的运动层面传达图像。这些变化的结果是革命性的。图像不再传达“信仰”的主题或沉思的、美丽的对象,而被视为“现存的”对象。这包括一个从再现到呈现的段落;换言之,它不是在平行的时间性中表现出永久的存在,而是为了部分地呈现缺少的东西,这个图像已经变成纯粹的存在,或纯粹的当下:此时此刻。图像由时间粒子组成,从感觉中挣脱出来,变成了认知。图像更多地涉及概念和阐释,而非直觉和展示。
立体主义通过与文艺复兴观点断裂,分解了拟人主义。基于线性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将一个视角归一化为一个集中的、单眼的、静态的实体存在于一个数学上的、同质的空间中。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创造了一种外部世界的错觉视角,使绘画平面类似于一扇窗户。用这一传统视点构建的图像借由图像平面提供的视角将身份和主体赋予了先验性。与之相反,立体主义把空间、时间和主体颠倒过来,重新定义空间体验,破坏了画面平面。如果古典的再现传达了一个连续的空间,立体主义则通过颠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使同一性与差异性相对,并且必然质疑古典形而上学,创造了不连续的空间。立体主义图像与凝视、主体和空间脱离关系,但不使它们彼此疏远,从而更新了世界的图像。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反人文主义的主体立场。此外,有了立体主义,时间的持续和透视的多重性都被嵌入到图像平面中。
受安迪·沃霍尔影像作品的影响,60至70年代的北美实验电影(或结构电影)让时间的持续成为美学经验的关键构成,展开了对电影装置的探索,试图使其类似于人类意识。实验电影创造了电影的对等物或意识的隐喻,使假视觉让位于唯我论的视觉体验。迈克尔·斯诺的实验电影《中部地区》(1971)就代表了这种未来主义的技术景观。影片中,斯诺通过强化和削弱常规视觉的各个方面,来探索电影装置的普遍特性。《中部地区》展示了由专为此影片设计的机器“德拉”从荒野中收集到的图像。这台机器能够向各个方向移动,360度旋转,放大和缩小,到达以前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除了最初的参数,“德拉”拍摄的镜头和人类的任何决定或视觉架构都没有关系。拍摄时间不同,气候条件也不同。结果是造成了对荒野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拓扑学探索,这是一个“巨大的景观”。
立体主义体现了主体的反人文主义断裂和诸多心理层面建构的可能性。《中部地区》体现了人类主体从中心位置移开。它们都是机械化带来的现代性碎片的缩影和异化。然而,这就是图像和基于沉思的艺术的命运。
如上所述,人类世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新图像,而是世界图像的转变。人类对地球生物物理系统的改变,立体主义和实验电影所宣称的人类视觉皮质的接受域的快速变化,以及前所未有的视觉对象的爆发,这些实际上使变化的结果变得不透明。例如,对野生动物详尽的可视化和记录有效地掩盖了它正在灭绝的事实。除了作为对抗现实的盾牌,图像也成为了它的认证模式。苏珊·桑塔格在谈到20世纪70年代旅游业的民主化时,描述了游客对摄影的依赖。
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但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把经验局限于寻找合适的被摄对象,或转化为一个图像,一件纪念品……拍摄照片的活动是舒缓的,并缓解了可能因旅行而加剧的迷失感。
近四十年后,摆姿势、拍照、分享和观看图像成为游客经驗不可或缺的行为(“点赞”、“推送”、“转发”)。这一点可以从查理·布鲁克创作的黑色幽默科幻剧集《黑镜》中看出来。这部电视剧探讨了图像作为我们经验和认知器官的组成部分的意义。“黑镜”只不过是液晶屏幕,我们通过它来塑造现实。
其中一集《你的全部历史》(2011)描绘了一个人人在耳后植入芯片的世界。芯片能把人眼变成记录现实的摄像机,变成可以再现现实的投影仪,将生活经验、记忆和图像与认知经验融合在一起。在另一集《马上回来》(2013)中,主角通过一个程序复活了死去的伴侣,这个程序将他死后化身的大量信息上传到了互联网上。这些不死的、没有身体的信息,这些图像和信号——一张生命的死寂地图——被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化身具体化。在这一集中,对数据的主观制造暗示着它的自动性——预示着宿命论的自动化和认知活动之间的关系核心。根据弗朗哥·贝拉尔迪的说法,谷歌帝国的核心是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以便将认知行为转化为自动序列。这种翻译的结果是用一系列的自动连接代替了认知,有效地使用户的主观性自动化。
图像和数据正在取代经验的位置,或为经验提供形式。除此之外,图像和数据也正将事物转换为符号、意象与话语的结合,创造了视觉的同义反复形式。随着摄影和数字影像被广泛应用,所有的符号都导向其它符号。这是由于人们渴望观看和了解,记录和存档。这与当代政治经济的实际形态有关:符号资本主义(或认知资本主义)取决于由在信息领域传播符号和数据的体量和速度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一种全新的准公共空间模式,包含了相互关联、伴生的的传播平台及其设备,如触屏,并且通过宣传技术实现了与符号和传播相关的权力形式。换句话说,权力可以引起传播,但所看到的、所谈论的、所展示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在密集的全球通信网络中传播大量内容这件事。在《黑镜》第一集《国歌》(2011)中,一个恐怖组织绑架了英国王室继承人。他们要求首相在当天下午4点的电视直播中与一头猪发生性关系。视频在网上疯传,整个英国向首相施压,要求他满足绑架者的要求,而他最终屈服于公众的压力,和猪发生了性关系。我们意识到,绑架是一个艺术家的姿态。他批判地指出媒体在塑造公共舆论方面塑造的角色。
在传播型资本主义中,图像和符号通过“点赞”、“分享”和“转发”等传播结构来获得价值或权力。符号价值取代了交换价值,意味着物质的东西不再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嵌入观看者之中和周围的认知符号来起作用。除了消费“体验”或“情绪”,图像消费者还会购买非物质商品(如生活方式和品牌),并贴上“平等”、“快乐”、“健康”和“满足”的标签。在小说《白噪音》(1985)中,主角杰克·格拉迪尼和他妻子购买的品牌符号和东西标签能够减轻他们日常生活的神秘和焦虑。
认知符号的加速和扩散是传播型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使头脑屈从于不断增长的知觉刺激,不仅产生恐慌和焦虑,而且破坏了所有可能的自主主观性。在传播型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图像转化为符号,这体现了当前知识和机器的连接,亦即资本主义生产价值的技术组织。随着计算机数据可视化的实现,图像已经成为科学、管理和军事的知识工具,从而成为资本和权力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视觉意味着在日常经验领域中加速感知——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验的琐碎视觉领域,有一种无根据的、加速的、重复的视觉,源自于持续的被动观察。对于贝拉尔迪来说,这是传播型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治理形式,因为这种视觉通过毫无意义地信息携带、自动思考和意志产生出技术语言的自动化。
在信息领域中传播的图像也会产生影响,使观看者接触到超出日常感知的感觉。图像的感染力特性来自于传播型资本主义对感觉和审美体验的冷酷认知。它在缺乏意义的情况下转化为信息、感觉和热情,正是这种转化使它们被作为工作形式加以利用,并被作为新的体验和令人兴奋的生活方式挑选和销售。问题之一是,影响不能与更大的身份和意义网络相联系。根据许多当代思想家,如黑特·史德耶尔和克莱尔·科尔布鲁克的观点,这种无根的状态是人类世的特征,因为我们缺乏任何基础,去发现政治、社会生活或与环境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的基础。正如科尔布鲁克所言,人类世使我们面临人类灭绝:我们是无数物种灭绝的原因,因为我们也消灭了那些使我们成为人类、支持我们的物种。因此,我们都陷入了一种紧急的相互关联的境况。
无处不在的合成数字图像与人类视觉分离,直接和权力、资本关联到一起。在这样的时代,图像和审美体验被转换为认知,因而转换为空洞的感觉和重复的关于现实的真理。人类世是人类的“世代”,宣告着人类自身的灭绝。换言之,人类世的命题是人类自身命运的终结。因此,人类世的叙事还是以人类为中心,同时标志着反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死亡,因为无法弥补批判的反人类主义者或后人类主义者的形象。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技术和科学的进步,都能找到一种调和人类生活和生态的方式。简言之,人类世的形象消失了。因此,首先有必要通过区分图像(image)和想象(imagery)或图片(picture)来克服我們无法想象替代方案或更好的东西的能力。虽然由视神经传递,但是图片并不能产生图像。为了制造图像,以视觉为基础进行表演(如艺术活动),将视觉视为一项重要的活动。在让-吕克·戈达尔的作品中,真实、想象和艺术相互作用。只有电影能够传递图像,而不是想象,传达的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主体的假设,因此是实体。对图像来说,变化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图像是存在的强化,因此它能够对抗所有的视觉体验。
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委托,戈达尔和安娜-玛丽·米埃维尔制作的论文电影《老地方》解决了人灭绝后生命的人类世困扰。
我们都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宇宙和灵魂的深处。没有回家的路,没有家。人类物种在恒星中膨胀和分散。我们既不能处理过去,也不能处理现在,而未来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家的概念。我们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自由,而是迷失了方向。
戈达尔和米埃维尔勾勒出世界终结的轮廓。当他们强调缺乏精神家园时,他们突出了失去起源和目的地的感觉,这意味着世界的积极原则已经停止发挥作用。影片最后一句台词出现时,观众看到一只死去的小熊被妈妈盯着看,接着是阿尔佩托·贾科梅蒂的雕塑《行走的人》(1961)。生命的存在是非理性的,不是想象出来的形式,它停止了与更高的真理共存。
在《老地方》中,戈达尔和米埃维尔探索了人性的形象在整个西方艺术史中的位置,突出了两千来年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神圣图像构成的这段历史,强调“痛苦”“美丽”“自然”“神圣”“资本主义”都是该图像固有构造。我们还看到了暴力、折磨和死亡的图像,这些图像与雕刻精美的人物和面孔并列在一起,创造于人类的各个时代,微笑、尖叫或哭泣。
“今天的图像不是我们观看到的,而是文字描述的。”这是宣传的定义,艺术转变为市场和营销,安迪·沃霍尔就是其代表。然而,除了无处不在的传播型资本主义,对戈达尔和米埃维尔来说,在图像的艺术中有一种抵抗的东西还留了下来。按照米埃维尔的说法,我们看到一块空白的画布,由四条机械的腿支撑着,不停地运动。这个场景唤起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图像,一个在后基督教世俗意义上的纯洁图像,一个神圣的、救赎的图像,一种图像和文本之间的矛盾关系,一个与知识无关的图像,一个与信仰有着内在联系的图像。
不仅如此,戈达尔和米埃维尔创造了一系列事物和想法,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图像,探索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蒙太奇的方法,一种思想的图像,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思想的操练,把它塑造成艺术,像星星一样的艺术作品。该图像也与它的起源有关,揭示出它是恒久弥新的——这是一种与历史密不可分的原始景观。
(由于原文篇幅较长,内容有所删减)
作者 墨西哥独立学者,研究领域涵盖艺术、文化、电影和地缘政治
译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播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