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雅各布森:我害怕众口一词和人群中汹涌的情绪
李乃清

“不是只有病毒出现时,人与人之间才需要保持距离;这个世界已变得危机四伏,无论到哪里,总聚集着一群乌合之众。”欧洲疫情肆虐期间,布克奖得主、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与我讨论到对未来的恐惧时,坦承自己对人群密集的恐惧——“我害怕人群中那种浪潮般汹涌的情绪。”
2014年,雅各布森出版了长篇小说《J》,这部令人深邃不安的灾难预言性作品很快进入当年布克奖的决选名单。英格兰诗人、艾略特诗歌奖得主约翰·伯恩赛德曾在《卫报》撰文,称其可与《1984》和《美丽新世界》相媲美。——“《J》可被视作当下的英国反乌托邦小说,从流行文化泛滥到消费狂热,从回避严肃事物到系统性侵犯个人隐私,它巧妙地折射出我们时代生活方式的种种诡异。”
《J》的故事设定在未来社会的滨海小镇鲁本港,这个社会试图掩盖一场大屠杀式的历史灾难,官方对灾难从未有过正式认定,而是遮遮掩掩,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大家仅以含混不清的“出了事——如果真的出过事”来指称它。
雅各布森笔下的这个社会看似正常,但种种现象又显得“有点不对劲”。法律从未明令禁止某些书籍和音乐,但它们自动消失了。流行文化取代了严肃的审美趣味,人们只阅读成功学、烹饪书和罗曼史,情歌小调代替了自由即兴的爵士乐。“没有禁止——从来都没有明确禁止过什么——只是不再放了而已。它们被渐渐废除,有如‘废除这个词本身。”
《J》中的男女主角凯文·柯恩和爱琳·所罗门斯,他们的姓名都是一个凯尔特名字与犹太姓氏相混杂的奇怪组合。经历大屠杀式的灾难后,官方抹去书本记载,迫使人们改名换姓,以此消除对个人、宗族和历史的清晰记忆。雅各布森以荒诞笔法描绘了“出事”后的大规模改名行动:老老小小在公园里一起跳舞,陌生的人们彼此拥抱,等待随机发放乃至摇号产生的新姓名。“你将会进入深度狂欢的睡眠之中,梦境里你跳舞寻欢,等数到十的时候你醒过来了,那时候你还能记得自己是谁,但不会记得你以前叫什么名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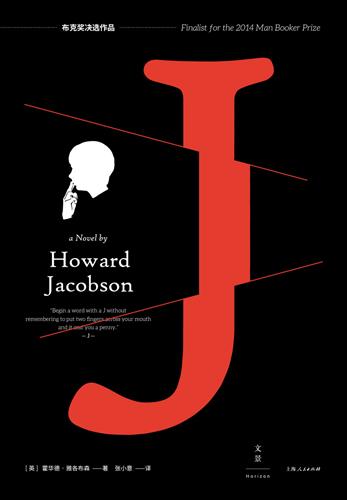
新姓名试图创建一个不分你我的乌托邦,“所有人都属于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人们相信再也不会出现仇恨,因为所有人已无差别。但现实并未按照设定好的轨道奔向美丽新世界,人们陷入不停地“为了历史”而道歉却不知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悖论中。若隐若现的噩梦袭来,人们在虚无感中沉浮,为戾气所笼罩,每个人都变得暴躁易怒,为了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
“当代文学已有太多表达未来恐惧的作品:被摧毁的景观、被火焰焚烧的社会等等,”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但雅各布森呈现了一种新的忧虑,他将毁灭转向我们的内心,在那里成为废墟的是我们的语言、想象力和爱。”
“我从没见过乐观的知识分子”——雅各布森认为,小說家有责任讲述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我总是觉得自己像是《旧约》或古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恨不得跑到大街上去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危险……有人总劝我别那么悲观,但一个作家的工作就是将它指出来。”
灾难会和以前一模一样地发生
雅各布森1942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毕业于剑桥大学唐宁学院,曾在悉尼大学、剑桥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职,迄今已出版小说16部、非虚构作品5部。
雅各布森以喜剧创作见长,作品致力于探索当代犹太人在英国的境遇及两性关系,他的喜剧小说既喧闹又辛辣,笔法精微,带有强烈的智性游戏特征。2010年,雅各布森凭借小说《芬克勒问题》摘得布克奖,评委会主席称赞他的作品“充满了睿智与幽默、忧伤与感性。它使人大笑,但却是在黑暗中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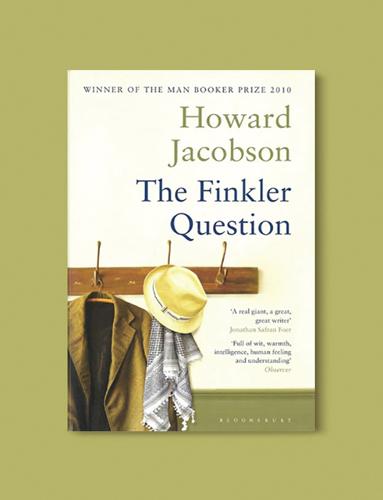
但小说《J》的主题和风格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华盛顿邮报》评论道,“《J》是雅各布森迄今为止最严肃、最令人不安的作品……比起机器统治,雅各布森对人类未来的忧虑更加深邃,他提出一个黑暗、绝望却被血腥历史不断验证的疑问:仇恨是人类文化的必需品吗?”
《J》中的男主角凯文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怪人,每次出门前都要强迫症式地反复检查门锁和邮箱,确保外人误以为他在家,不会伺机闯入。小时候父亲曾和凯文玩过一个游戏,只要讲出以J开头的词语,就要用两根手指压住嘴唇。
作为犹太裔作家,犹太人的境遇是雅各布森反复书写的母题。“J”是书中从未明确提及的“犹太人(Jews)”首字母,具有强烈指向,但也包括“爵士乐(Jazz)”等禁忌之词。在半隔绝的小屋里,凯文阅读严肃书籍,听父亲留下的爵士乐唱片,他的生活让邻居感到迷惑:“他们没以为他愚蠢,反倒觉得他可能聪明过头了。不过人类历史上总有些时候,聪明也就意味着愚蠢。”
凯文想知道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对周遭一切神经质地敏感,总以为有人要窥视他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迁居此地的同类爱琳。在复杂而精细的监视网络中,爱琳借用梅尔维尔《白鲸》的情节说出了她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一直以来亚哈都在追踪我们。”
随着小说情节逐渐深入,阴谋论警官和势利的艺术教授暗中盯上了这对恋人,整个社会就像是一场实验,作为杀戮的幸存者,艾琳最终选择与过去和解,但无法忍受命运的凯文却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社会的每个单元都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无意追究谁的责任,不管是对是错,过去的已然过去,什么也不用说了——这点我们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没有人可以指控,所以也没有人去弥补,即使弥补是合适的,而且有办法去弥补。但要是不能从过去总结教训,过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小说中,雅各布森虚构了一个重要角色:公众情绪观测机构的调研员埃斯米,她对官方行动的有效性发出上述质疑,但只得到主管的一句简短回答——“过去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忘记。”
“巧合”的是,埃斯米第二天上班路上被摩托车撞至昏迷,但在后来的康复过程中,她似乎“开窍了”,认清了社会关系的本质是敌意的对抗平衡。一旦社会发生危机,一个族群总要找个目标来承担责任。如果“出事”打破了这一平衡,那么只有重新寻找、培养灾难幸存者的后裔,创造未来的“仇恨目标”,社会才能复归平衡。
“哪个国家不是它自己历史的藏骨屋呢?一些人的春天,就是另外一些人的严冬。”穿透娱乐至死的社会中五光十色的泡沫,直视生活的黑暗底色,雅各布森借小说人物之口发出令人震惊的哀叹——“(灾难)会怎么发生呢?和以前一模一样地发生……”
人:人民周刊 雅:雅各布森
夾杂旧疾的重启真的是新生活吗?
人:《J》被视作精彩的灾难预言作品,约翰·伯恩赛德将它与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相提并论,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雅:他真是过奖了!那两本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小说,但我认为它们比我的作品更侧重预测未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写的《J》其实更针对当下。
人:小说中反复出现一句话:“出事——如果真的出过事。”书中人物也发出哀叹:“(灾难)会怎么发生呢?和以前一模一样地发生……”写下这些警告时你是怎样的心态,为何会写这些?
雅:这只是源于我所相信的——某些残忍、毫无理性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将来还会再现,而且常以无法接受的方式重现。我们为了防止下一次对人类的蓄意伤害已经忍受了太多,寄希望于此事再也不会发生的态度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可怕的事实是,已有灾难可能一次次持续再现。“(灾难)会怎么发生呢?和以前一模一样地发生……”,经常发生的还有忽视和恐惧,不只是对他人的恐惧,更是对未知和各种模棱两可说辞的恐惧。人们想要相信,并且确认自己是某种存在,而达成这种确认的手段却是消灭他者。《J》道出了某种紧迫性:不只是爱我们眼中的他者,更要接受一个重要观念:我们眼中的他者也是“我们”。
人:小说开篇,你引出一则狼与狼蛛的对话,具体介绍下这则隐喻?
雅:在那些古老精妙的叙述传统中,人们常常通过描写动物行为来揭示人类本性的真相,这能让我们除去政治或社交因素的干预,直面人类的欲望和动机。我创作了开篇狼与狼蛛的对话,它的寓意很清楚:如果你将一切吃得一点不剩,最后填饱肚子的只剩下你的家人甚至你自己。这也是《J》整部小说所讲述的:永远不要赶尽杀绝,否则你终将引向自我消灭的结局。

5月5日,工作人员在意大利罗马附近的韦莱特里公墓进行消毒
人:如今新冠病毒肆虐,对眼下这场扫荡全球的大灾难,你有何观察和思考?
雅:如此规模的大灾难后,未来势必发生变化,但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更好还是更坏,因为我们期望更好的变化,试图在无意义中寻得意义,那样才能解释我们经受苦难的目的。《J》中的男主人公凯文,坚信已有的罪恶中不会生出任何好事,他不愿让施恶者获得这样的满足感,他认为这些人理当被剥夺赦罪机会。但我们在小说结尾,听到的却是女主人公爱琳吊诡的声音,她迎来新启的生活却仍充斥着昔日的混乱,这样夹杂旧疾的重启真的是新生活吗?
人:说说《J》中公众情绪观测机构工作人员埃斯米这个人物的设定?凯文、爱琳和埃斯米三人在书中的形象比较清晰,那些观察、监视他们的配角(警长、艺术教授等)在这场社会实验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雅:埃斯米是完全虚构出来的,她原本是个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女人,但惹祸上身,最终变成了一个失去人性、像机器般冷酷的人。那些配角的出现代表着灾难发生后出现的各种质疑甚至仇恨的声音。
人:书中凯文所生活的滨海小镇鲁本港的环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有何隐喻?
雅:我曾经在康沃尔郡生活了多年,当地见闻呈现在小说里我对凯文生活之地的描述中——一片荒蛮原始之地,裹挟着一段暴力且具毁灭性的历史,常年被谣言、怀疑和盲目的恐惧撕扯着。我无意描述某个真实的地方,这都是脑中想象出来的,但事实上,所有地方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人:小说中你描绘了一座极具科幻感的城市尼科洛波利斯,那里布满了电子屏和透明汽车,你对眼下急速发展的高科技持怎样的态度?
雅:我害怕高科技,和过去那些人道主义者一样,我厌恶高科技导致的去人性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眼下大家都隔离在单人间里,互联网无人性、免接触的冷冰冰的文化却成了所有人的拯救。我最讨厌那些社交媒体,它们四处散播各种未经核实、缺乏质疑精神的论断和主张,这是艺术和想象力的大敌。互联网看似要解放我们,但种种迹象显示,我们将被它奴役。尽管它允诺将我们联于世界,但事实上,它驱使人们将自己禁锢在一小块苍白无力的屏幕前,沉溺于个人疯狂而不切实际的幻觉中,彼此联系的还都是些同类。
人:和诸多反乌托邦作品直接批判权力制度、技术焦虑或机器统治相比,《J》描绘的世界更为日常,你如何看待当下蓬勃的消费主义及流行文化?
雅:消費主义并未引起我的困扰。但人们日益缺乏独立思想,这一现象让我感到忧心,社交媒体正是由于人们缺乏独立想法才流行起来的。流行文化是对我们自由的最大威胁,我甚至可以说,它是对我们文明的最大威胁,流行文化本质上就是不加质疑的众口一词。
人:小说中,你借艺术教授之口道出“艺术,恰恰在于冒犯”的“真谛”,如许反讽,也说出了你本人对艺术的看法?
雅:我想,书里那句话算是对概念主义等运动所践行的艺术创作的中肯描述吧。某种程度上,那些不懂当代艺术语汇的人被激怒了,这正好说明艺术完成了这项工作,换言之,对抗中产阶级成了艺术的首要功用。也许我应该支持这种对流行文化的反抗,但这个钟摆似乎甩得又太偏了。艺术不必立时立刻就能看懂,但也不该竭力追求“高不可攀”。所有高质艺术和思想都处于个人与公众、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平衡区间,一旦平衡被打破,我们就把艺术给毁了,也毁了我们鉴赏艺术的初衷。

5月1日晚,法国巴黎第5区的多邦东大街,人们观看在墙壁上放的电影
“喜剧”是残酷的词汇
人:你的作品文字机敏俏皮,情节往往有点荒唐可笑,大家常称你是“喜剧小说家”,但你探讨的主题通常又是严肃沉重的,例如犹太人的历史、种族大屠杀、灾难等等,创作时如何保持“庄”与“谐”之间的张力?
雅:的确,如果我能游刃有余地掌控艺术,这种张力就是其魅力所在。我喜欢那些开头戏谑、结尾让人心碎的组合,反之亦然。我不认为有何主题是喜剧无法处理的,但我个人不喜欢、也不追求创作那种所谓光明的喜剧,我认为喜剧应该是深刻的,它的思想和言行建基于将读者引向惊恐万状的那个爆破点。
人:就如你曾说的,“‘喜剧是残酷的词汇”?
雅:没错!最好的喜剧将我们带到灾难的悬崖峭壁,并且逼着我们去看。它其实不太讨好读者,悲剧迎合我们的人性需求,与之相比,喜剧更残酷。在悲剧中,至少我们瞥见了人性的高尚尊贵,但在喜剧中,我们只看见丑陋的兽性。
人:创作小说之外,你曾撰写专栏、主持电台节目,你如何看待媒体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在眼下这场全球灾难面前,媒体应该发挥怎样的功效?
雅:当下世界,不负责任的大众流行媒体肆虐横行,有的倡导阴谋论,有的趋炎附势,人们从没这么急迫地需要一个诚信优质的独立媒体,但它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怀疑,眼下的时代,没有什么派别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看谁少犯错而已。媒体需要发出清晰理性的声音。
人:诗人米沃什曾说:“大众传播媒介奇妙扩展,我们的星球每年都在变小,见证着一个难以定义的过程,其特点就是拒绝回忆。诗人感到焦虑,因他感受到,不远的未来,历史将化约为电视上播放的,而真理,因太复杂,就算不被完全销毁,也会被埋葬在档案室。”遗忘也是你在这部小说中重点处理的主题。
雅:我完全赞同米沃什关于时代拒绝回忆的描述,这也是《J》所探讨的。如今的年轻人似乎都已习惯了遗忘,这种失忆症表现在他们对曾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我们以为互联网会提供给我们探索历史更丰富便捷的渠道,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如今的人们只关注眼下。
人:关于遗忘,《J》中那位哲学家表示:无需深究,我们只要说抱歉。“‘说抱歉将我们所有人从相互指责的过往中解放出来,去往一个无可指摘的未来时代。”我记得你有部作品就叫《此刻谁抱歉?》,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只是“说抱歉”吗?
雅:我不确定自己曾否见过真正有价值的道歉。大多数时候,致歉者向那些深受伤害甚至毁灭的受害者说抱歉为时已晚,而且谁被授权代表这些受害者接受道歉呢?灾难之后我们所期望的是对它的认知——既包括各种文字、信息,也包括深层的理解。《J》非常关注机密及讳莫如深的状态,当前的各种危机都深受纷繁复杂的秘密搅扰。秘密滋生怀疑,怀疑滋生关于阴谋论的各种猜想,这是个难以打破的恶性闭环。
人:小说中有个角色指出:“仇恨存在于人之外。我把它比作病毒。人们会抓住它………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去激发它。”有人认为,你在写作中指出种族仇恨仍在欧洲游荡,表达了对欧洲的一种隐忧。
雅:是的,这是《J》最集中的一个观点。对很多人而言,曾激起种族大屠杀的仇恨余毒依然存在,许多人在争辩“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但却希望“发生过”或者“它会发生”。种族大屠杀过去才多少年,要是致命而有毒的反犹主义再次出现,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
人:面对那些近乎绝望的事态,你通常会从哪里找寻“希望”?
雅:我从各处找寻“云朵的银边”——那一线希望。我多愁善感,高度关注个人快乐,甚至到了某种荒谬的程度。即便观看悲剧气氛浓烈的歌剧,到了结尾我还是执拗地希望恋人能重聚。但那是我的心,我的头脑想的却不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以说,生活经常都是恐怖又令人失望的,但在某些小角落,你必须继续相信,事实并非如此。
人:对于未来,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这是个大问题。我惧怕流行文化、缺乏独立主见、舆论一边倒、乌合之众、暴民,以及这些人追随的各种大众传媒上的表达。不是只有病毒出现时,人与人之间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这个世界已变得危机四伏,无论到哪里,总聚集着一群乌合之众。有些人享受流行音乐或体育赛事的大众狂欢庆典,但我不喜欢。我害怕人群中这种浪潮般汹涌的情绪。在我看来,人们保持一定距离才是安全的,当然,也不是那种远到各自关在卧室、整日沉溺于社交媒体虚设的幻梦中的距离……两者之间需要一个平衡。
(感谢杨沁、杨朗协助联络专访,实习记者陈梵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