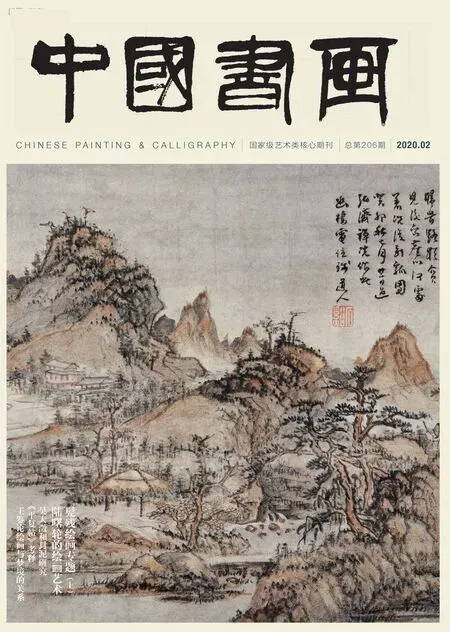从倡导形式语言到批评形式语言
——论吴冠中的美术批评
◇ 陈都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美术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创作方面,产生了如袁运生的《泼水节 生命的赞歌》、张仃的《哪吒闹海》等以首都机场壁画为代表的,形式感强、情绪饱满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打破了唯题材论的窠臼,而且还开创了文艺创作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在美术理论方面,吴冠中不仅率先呼吁“形式美”“抽象美”的重要性,也是第一位从理论层面批评写实主义的美术家。但正如吴冠中自己所抱怨的那样,“我直言不讳,但我的话容易被断章取义”〔1〕。尤其是一些研究吴冠中的学者,也并不清楚曾经疾呼重视“形式美”“抽象美”又批评写实主义的吴冠中,为什么会攻击“笔墨”这种中国画特有的形式语言。笔者细读吴冠中著述,发现他从赞扬形式语言,再到批判形式语言的逻辑转变,思维清晰、客观,有理有据,并非一般认知下的激进与情绪化。因此,本文意图梳理吴冠中对形式语言的论述,以此进一步地理解这位对20世纪后期中国美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美术家。
一、批判写实主义
在新中国美术中,人民大众是审美主体,组织主题创作的相关单位,如博物馆、美术馆,各地文化馆、纪念馆等组织机构,是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实际赞助人。虽然新中国美术讲求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但艺术家的作品必须先满足赞助人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基本属于图解历史事件或当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动态,是“无我”的。所谓“无我”,即创作主体无法主动驾驭对象,没有能力对创作客体进行主观化的处理,仅客观地描摹创作客体。虽然1949年以后的很多著名主题创作,都是作者对创作客体进行高水平的主观化处理,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并不属于“有我” 通过形式语言的美感,将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表达出来,并通过画面中的形式美再将这一内容传达给审美主体。

吴冠中 水上人家 68cm×91cm 纸本设色 约1981年
这种无法表达“有我”的美术创作,无疑对中国美术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吴冠中就是一位不屑于赞助人的要求,不愿遵从于既定样式、程式的艺术家。正如他所说:“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丑化工农兵 。 我看到有些被认为‘美化了工农兵 的作品,却感到很丑。连美与丑都弄不清,甚至颠倒了。”〔2〕吴冠中为了在作品中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思、感情,一方面,他不再画人物画,改画风景画,另一方面,他单独地将审美主体剥离出来,通过人民群众的审美期待来研判自己的作品是否经得住考验。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住在农民家,每当我作了画拿回屋里,首先是房东大娘大嫂们看,如果她们看了觉得莫名其妙,她们绝不会批判,只诚实又谦逊地说:‘咱没文化,懂不了。 但我深深感到很不是滋味!有时她们说,高粱画得真像,真好。她们赞扬了,但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因我知道这画画得很糟,我不能只以‘像 来欺蒙这些老实人。”〔3〕所以,吴冠中涉及写实主义的文章,往往给人以一种感觉,就是他以否定写实主义美术的客观价值为前提,来追求“有我”的形式美、抽象美。
事实上,吴冠中并不认为写实主义美术只能模仿“无我”的创作客体,他的艺术理念并不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基本精神相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吴冠中与其他艺专学生并无不同,一方面沉浸在象牙塔里,练习绘画造型基本功,汲取造型艺术的各个要素。当战火烧到杭州,吴冠中同艺专的师生一起,与劳苦大众结为难民队伍,尝到了颠沛流离的苦难,发觉了“臭”且“丑”的劳动者身上蕴藉的美感,他开始画生活速写,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不仅启迪了他新的审美观〔4〕,而且时时啃噬着他原先所追求的脱离现实、纯学术的象牙之塔〔5〕。此后,再经由留法期间,在蒙马尔特广场上,吴冠中看到那些受过严格技法训练的画家在街头卖画像,致使他“开始对长期所追求的象牙之塔感到空虚和失望”〔6〕。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吴冠中初次读到了《讲话》,过往的启蒙与当下的失落极速对撞,遂产生了强烈共鸣。他开始思考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认为他原先所追求的象牙之塔,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吴冠中也因此回到了故土,回到了人民中间,在与现实息息相关的生活中找寻艺术创作的道路,并追求人民群众能看得懂的艺术,也就是“不断线的风筝” “我认为‘无形象 是断线风筝,那条与生活联系的生命攸关之线断了。作为探索与研究,蒙德里安是有贡献的,但艺术作品应不失与广大人民的感情交流,我更喜欢不断线的风筝!”〔7〕所谓“无形象”指与自然物象无任何联系的纯形式,而“断线的风筝”即与生活无关联的艺术创作,“不断线的风筝”即“应不失与广大人民的感情交流”〔8〕的形象。

吴冠中 侗族村寨 90cm×90.5cm. 纸本设色 1980年
注释:
〔1〕吴冠中:《直话直说 答〈文艺报〉记者问》,见吴冠中:《笔墨等于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18页。
〔2〕〔3〕吴冠中:《望尽天涯路 记我的艺术生涯》,前揭《笔墨等于零》,第59页。
〔4〕吴冠中:《走出象牙塔 关于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回忆和掌故》,前揭《笔墨等于零》,第42页。
〔5〕〔6〕同上,第47页。
〔7〕〔8〕吴冠中:《风筝不断线 创作笔记》,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44页。
〔9〕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71页。
〔10〕吴冠中:《内容决定形式?》,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88 189页。
〔11〕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76页。
当我们整体地阅读吴冠中的文献,也会发现,他高度赞扬一些写实主义的主题创作的形式美,比如他认为《收租院》是美的〔9〕,同时,他也曾通过强烈的情感,构思出具体的、现实的写实主义作品 “刚离开大足,途中遇到对越反击战胜利归来的英雄们,我们鼓掌,激动得落泪,我立即联想到牺牲了的永不再归来的战士,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画:在我们国境的大地上,一个偌大的牺牲了的青年战士安详地睡了,广西、云南边境是亚热带,边民们几乎是半裸体的,妇、幼、老、少爬满在战士身上哭泣,战士与边民们身躯大小比例之悬殊,正如卧佛与其弟子们的差距,从战士绿色戎装的身后吐出一条细细的鲜红血流是牺牲的标志!”〔10〕
可见不管是从艺术理念的变迁,还是从艺术作品的品评、艺术创作的感悟,在吴冠中的认知下,他肯定、认可写实主义美术创作的客观价值,承认写实主义美术可以表现“有我”,可以用写实主义的形式语言传达出创作主体的情思、感情。也正是基于“不断线的风筝”的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冠中一系列疾呼艺术需要重视“形式美”“抽象美”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地否定写实主义美术的客观价值。
另一方面,吴冠中将写实主义的美术教学树立为形式美、抽象美的对立面,正如他在《美术》1979年第五期上发表的《绘画的形式美》一文中所说:“数十年来,在谈及形式便被批为形式主义的恶劣环境中谁又愿当普罗密修士呵!教学内容无非是比着对象描画的‘画术 ,堂而皇之所谓‘写实主义 者也!好心的教师认为到高年级可谈点形式,这好比吃饱饭后才可尝杯咖啡或冰琪琳!但我不知道从抄袭对象的‘写实 到表达情绪的艺术美之间有没有吊桥!我认为形式美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描画对象的能力只是绘画手法之一,它始终是辅助捕捉对象美感的手段,居于从属地位。”〔11〕可见,在吴冠中看来,写实主义的美术教学无法教授学生表达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是一种“无我”的教学方式。
因此,所谓“不知道从抄袭对象的‘写实到表达情绪的艺术美之间有没有吊桥”,是批判在写实主义美术教学之下,只训练再现“无我”的客观对象的学生,而不是质疑写实主义绘画能否传达出“有我”。

吴冠中 花 62cm×48cm 纸本设色 1995年
注释:
〔12〕王震:《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02页。
〔13〕同上,第 84页。
〔14〕吴冠中:《关于抽象美》,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82页。
〔15〕同上,第 180页。
〔16〕同上,第 183页。
〔17〕吴冠中:《三方净土转轮来:灰、白、黑》,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36页。
〔18〕吴冠中:《望尽天涯路 记我的艺术生涯》,前揭《笔墨等于零》,第60页。
〔19〕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72页。
〔20〕吴冠中:《望尽天涯路 记我的艺术生涯》,前揭《笔墨等于零》,第61页。
〔21〕吴冠中:《笔墨等于零》,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92页。
〔22〕吴冠中:《柳暗花明》,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40 141页。
二、倡导形式语言
诚如上文所论,吴冠中关于写实主义的批评,是肯定写实主义美术的客观价值;同时,通过否定写实主义的美术教育,以此构建以形式语言为主体的新美术。而这种美术批评所体现出来的逻辑关系,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并不是孤例。
徐悲鸿就是肯定传统的画传画谱的客观价值,否定以画传画谱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效用。从美术教学的角度,徐悲鸿极为厌恶传统的中国画教学 画传画谱,“因为一般人心理,大都喜欢取巧,只要有现成画谱,不必自己挖空心机来构思,花时间去找画材。所以想到画山水花鸟,人物屋舍,画谱上有的是,一举手之劳,都可解决,人人如此,中国画真要走上末路”〔12〕。所以,徐悲鸿不仅认为“‘芥子园 之类画谱的出世,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而且还通过激烈否定《芥子园画传》,进一步构建起写实主义的新美术,以救时弊:“真正要学国画的人,赶快去学习古人六法的深义,然后找现实题材努力写作,否则舍本求末,结果毫无所得。”而这也是后人多认为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艺术,就是建立在反传统之上的原因。事实上,徐悲鸿是很赞赏中国木刻版画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对传统的画传画谱大加赞赏,如“十竹斋之木刊彩印,可称人类文化史上稀有之杰作”,又如“厥后芥子园画谱版画,亦见精妙,无忝作者,但其道止于此,皆无名英雄为之,士夫视为等闲,无关宏旨”〔13〕。所以徐悲鸿并没有质疑画传画谱的客观价值,而是在攻击照抄照搬画传的美术教学,并确信写实主义可以诊治“虚、伪、浮”的画坛歪风。
历史的进程总是相像的,针对时弊、积弊所做的任何策略的调整,总是会逐渐产生各种新的问题。于是,曾经代表一个时代的先进力量,往往就成为下一个时代亟待解决的弊端。写实主义美术就是如此,曾经作为先进的改革力量的写实主义,逐渐产生了诸多问题,正如吴冠中所批评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忽视学生在创作中主体情思、情感的表达。于是,“大破”之后,必然是“大立”,吴冠中就提出以形式语言为主体的新美术:一方面,形式语言表现“有我”;另一方面,形式语言将“有我”传达给审美主体。
吴冠中认为,美术起源于客观对象的模仿,除了描绘像不像,更重要的问题是美不美,而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14〕。因为创作客体本身存在着“美”与“不美”诸多因素,画得像,就是把创作客体所有的“美”与“不美”的因素都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样的画面不一定是美的。吴冠中认为,应该从具体的物象中,提取抽象美进行研究,正如他所说:“要在客观物象中分析构成其美的因素,将这些形、色、虚实、节奏等等因素抽出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这就是抽象美的探索。”〔15〕“因为掌握了美的形式抽象规律,对各类造型艺术,无论是写实的或浪漫手法的,无论采用工笔或写意,都会起重大作用。”〔16〕需要明确的是,吴冠中所强调的“形式美”“抽象美”,并不是蒙德里安的纯粹的抽象主义艺术,而是“探求与父老乡亲们相通”〔17〕的艺术语言,由此可以再次论证“不断线的风筝”的艺术理念,首先,画面务必使普通大众看得懂,画面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这也是吴冠中不否认写实主义美术客观价值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正如吴冠中所说:“我并不以农民的审美标准作为惟一的标准,何况几亿农民也至少有千万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吧。我并没有忘记巴黎的同学和教授,我每作完画,立刻想到两个观众,一个是乡亲,另一个是巴黎的同行老友,我竭力要使他们都满意。有人说这不可能,只能一面倒,说白居易就是雅俗共赏的追求者,因之白诗未能达到艺术的高峰。但我还是不肯一面倒,努力在实践中探寻自己的路,不过似乎有所侧重,对作品要求群众点头,专家鼓掌。”〔18〕就是说,他在探索如何表达创作主体情思、情感的形式语言的时候,不仅会进入抽象的形式美的探索,研究形式美的独立性,而且更注重普通大众的审美期待与画面形式语言之间的关系。因此,其本质依然没有脱离《讲话》的基本精神。

吴冠中 竹涧图 48.3cm×45cm 纸本设色 2000年

吴冠中 四合院(一) 70cm×70cm 纸本设色 1999年
综上所述,吴冠中是在否定写实主义美术教育的同时,提出的“形式美”“抽象美”,其基本诉求就是“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19〕
通过形式语言将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表现出来,再通过形式语言将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传达给审美主体(群众与专家)。
三、批判形式语言
吴冠中批判写实主义、倡导形式语言,是以能否表达出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能否再将其传达给审美主体为评判标准。为了拯救时弊,遂疾呼“有我”的形式美、抽象美。但个中核心,是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也就是“有我”,而包括形式美、抽象美在内的形式语言不过是一种“表达出来”与“传达出去”的技术手段,是从属地位。而一旦居于从属地位的形式语言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有我”,则在吴冠中的艺术理念里,就是没有价值的。
这种批评逻辑在吴冠中的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比如《笔墨等于零》与其另一名篇《内容决定形式?》就有着相同的逻辑关系。前者批评孤立地品评笔墨等形式语言,会奴役作者的思想情绪的表达;后者是批评过分地关注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衣着服饰等内容,会限制作者的情绪和感受的抒发。也就是说,如若不能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则形式语言再丰富,主题思想再突出,也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吴冠中对于形式语言的批判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其具体论述主要集中在《笔墨等于零》,并在他的散文、随笔中偶有所见。一般的认知把吴冠中关于笔墨的论述放在中国画的语境之下进行探讨,事实上,吴冠中始终是把笔墨放置在形式语言的语境下进行论述,比如他曾说:“文人画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绘画隶属于文学,重视了绘画的意境,是其功,但又往往以文学的意境替代了绘画自身的意境,是其过。另一特点是所谓笔墨的追求,其实是进入了抽象的形式美的探索,窥见了形式美的独立性。”〔20〕在吴冠中看来,“笔墨”就是一种形式语言,属于独立的形式美、抽象美,而评判笔墨是好是坏,则与评判其他种类的形式语言是一个标准,正如他在《笔墨等于零》中所论述的,线、面或笔、墨,乃至其他形式语言,只有当“有我”表达出来及传达出去的过程中,才能判断出价值 “果真贴切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感受,成为杰作,其画面所使用的任何手段,或曰线、面,或曰笔、墨,或曰XX,便都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与价值。价值源于手法运用中之整体效益。”〔21〕所以,《笔墨等于零》不仅仅是关于笔墨的批评,更是在批判所有无法体现创作主体情思、情感的形式语言。
在吴冠中看来,形式语言能强烈地、有效地将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表现出来,以及再将这种“有我”传达给审美主体,则这种形式语言就是一种理想的形式美,也是吴冠中所追求的“不断线的风筝”。但如果作为独立的形式美、抽象美的形式语言,只将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表现出来,但没有将这种“有我”传达给审美主体,则这种形式美就属于“断线的风筝”。据他所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其母题是表现“汉柏”“苏醒”“故宅”“田”“忆故乡”等具体物象,但在努力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形式美的因素常常大幅度提升,使得块、面、点、线等等之间的形式语言成为作品的灵魂、根本,于是具象的母题被解构或被隐藏,作品也就进入抽象领域〔22〕。这种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抽象美往往无法为群众所理解,因此,吴冠中把这种作品归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美之感受无疑是雅俗间交流的通途,但美而不‘像 的情况当然也很普遍,怨作者还是怨群众呢,如果作者确乎不属于欺世盗名与装腔作势之流,则责任在双方,是普及与提高的老问题。”〔23〕换言之,美而不“像”的作品,如果不能让群众看懂,则并不能简单地批评作者或批评群众,只能说作者没有照顾到大众审美。群众还亟须提高审美水平。
注释:
〔23〕吴冠中:《谁点头,谁鼓掌》,前揭《笔墨等于零》,第190页。
〔24〕〔25〕吴冠中:《直话直说 答〈文艺报〉记者问》,前揭《笔墨等于零》,第212页。
〔26〕张天翼:《看了西湖艺专四展以后》,《申报》1934年3月16日,第19版。
〔27〕张天翼:《后期印象派绘画在中国》,《张天翼文集》(10),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91页。
〔28〕前揭《徐悲鸿文集》,第13 14页。
〔29〕同上,第 16页。
〔30〕同上,第 23页。
〔31〕同上,第 15页。
〔32〕同上,第 112页。
上述两种形式语言,不管是“不断线的风筝”,还是“断线的风筝”都是吴冠中所能接受的,但如果画家属于“欺世盗名与装腔作势之流”,那么居于从属地位的形式语言势必无法有效地表达“有我”,责任也必然在作者。但吴冠中为了醒目,起了“笔墨等于零”的标题〔24〕,从而导致这篇文章从有理有据变成了争议对象 刻意地选择历史虚无主义,以攻击陈腐、教条的笔墨程式。事实上,就《笔墨等于零》的全文内容来看,“笔墨等于零”改为“笔墨等形式语言等于零”更为适宜。正如吴冠中所坚持的那样:“笔墨等于零,我怎么想都没错。”然而他又慨叹道“不能只看个标题就大做文章”〔25〕。
之所以吴冠中的言论引起极大争议,则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性 在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突然涌入,传统文化迅速复兴的大背景下,吴冠中的这种激进一定不会被接受。但如果从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待“笔墨等于零”,则吴冠中对形式语言的批评,则属于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共识,甚至可以说,“笔墨等于零”的论调非常温和。比如曾上过一年上海美专的儿童文学家张天翼,就对这种欺世盗名、装腔作势的形式语言极尽讽刺之能事,骂中国的“后印象派”们“只要颜料刷得起劲就行,轮廓可管不着”〔26〕。同时,张天翼还敏锐地指出中国画家追求的“后印象派”与江湖市井作风的笔墨语言之间的关联,只是用词更加激烈:“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艺术。中国人既然想脱开圣贤之徒的八字脚文化的束缚,而唱一种从洋鬼子那儿学来的摩登的小白脸文化,唱个人主义,当然很容易地接受了这种艺术。”〔27〕
徐悲鸿也是激进地批评形式语言的典型人物,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把徐悲鸿诘责“后印象派”形式语言与批评文人画笔墨语言的论述分开。事实上,如果仔细研究“二徐之争”,尤其是徐悲鸿的《惑》,徐悲鸿在大骂“后印象派”的同时,也在骂文人画。这说明,在中国画坛,不管是“后印象派”还是文人画,都存在着同一个问题 装腔作势、欺世盗名的形式语言。比如:徐悲鸿批判“后印象派”的形式语言,是因为模仿者不仅不知道流派的缘起、发展、特点等基本的美术史知识,甚至连照猫画虎地描摹都做不到,而他们笔下的形式语言是否能体现真正的“有我”,更是不闻不问,只是用“后印象派”一词掩盖自身的粗陋〔28〕。同时,在徐悲鸿看来,借着新派艺术的形式语言标榜创新,与借着文人画的笔墨标榜气韵,其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所以,虽然徐悲鸿也肯定过“四王”的才干 “近代惟石谷能以画入自然,有时见及造化真际”〔29〕,但在《惑》中,徐悲鸿否定“后印象派”的形式语言之后,立刻将文人画的形式语言也否定了 “不愿再见毫无真气无愿力一种Art Conventionel之四王充塞,及外行而主画坛擅之吴昌老,式微式微,衰落已极。”〔30〕所以,徐悲鸿对“后印象派”、文人画的批评,都是在中国画坛市井江湖化的大背景下,其批评形式语言的逻辑是共通的。
用张天翼、徐悲鸿的例子,一方面是说明“笔墨等于零”所批评的形式语言的问题由来已久,另一方面说明,在面对中国画坛的江湖市井作风时,言语激烈,上纲上线,近乎一种传统。再以徐悲鸿为例,徐氏在论述西方艺术发展历史的时候,是肯定“后印象派”的形式语言 “欧洲绘画界,自十九世纪以来,画派渐变 如马奈、塞尚、马蒂斯诸人,各因其表现手法不同,列入各派,犹中国古诗中之潇洒比李太白、雄厚比杜工部者也。”〔31〕但他为了批判追逐时髦的人随声附和,就会激进地否定“后印象派”的形式语言,不仅将马蒂斯等人的艺术称为“鄙庸弱”,还要上纲上线地提升到“国家危亡之征”的高度上〔32〕。所以,与之相比,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虽然全文有理有据,但“笔墨等于零”显然是通过全盘否定笔墨的方式,以批判“无我”的形式语言。
结语
通览吴冠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作的美术批评,从批评写实主义到倡导形式语言,再到批评形式语言,吴冠中言辞往往激烈,易于被人误解、扭曲,但他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始终是以中国美术为重,始终以画作能否表达出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为评判标准 形式语言能强烈地、有效地将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表现出来,以及再将这种“有我”传达给审美主体,则这种形式语言就是一种理想的形式美,也是吴冠中所追求的“不断线的风筝”。但如果作为独立的形式美、抽象美的形式语言,只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但没有传达给审美主体,则这种形式美就属于“断线的风筝”。这种作品并不能简单地批评作者或批评群众,只能说作者没有照顾到大众审美,群众还亟须提高审美水平。而不管是“不断线的风筝”,还是“断线的风筝”,都是吴冠中所能接受的。唯有形式语言不能表现出“有我”的作品,才会受到吴冠中的鞭挞。所以,当写实主义专注于模仿创作客体的外在物象,不探索“有我”的表现,他则批判写实主义,并倡导形式语言的美感;当中国画坛再次陷于市井江湖的泥淖中,笔墨等形式语言不再为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思、情感服务的时候,吴冠中对形式语言的批判更引起轩然大波。
而从张天翼、徐悲鸿,再到吴冠中等等,对于没有真情实感仅浮于表面地把玩形式语言的现象,都是非常反感的。虽然反对脱离时代、脱离社会的陈腐程式,但往往建立在彻底地、全盘地否定某一派别、门类的艺术规律之上。关于这一特点,后世理应以更宽宏的视角去理解、同情前人的处境,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们的激进。

吴冠中 遗忘之花 69cm×69cm 纸本墨笔 2005年

吴冠中 老墙 70cm×70cm 纸本设色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