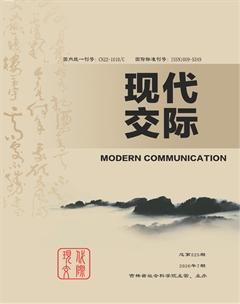重读《狗儿爷涅槃》
王幸逸
摘要:话剧《狗儿爷涅槃》对当代农民的人生命运和传统心态做了深层开掘,表现了农民既革命又保守、既淳朴又自私、既热爱劳动又摆脱不了“创家立业”意识的复杂特点,而这种复杂性又根源于农民的土地情结。对《狗儿爷涅槃》进行细读,分析其中展现的中国农民土地情结,并将文本置于当代文学的农村书写和农民想象的大语境中,检讨戏剧文本与社会泛文本间的复杂对话。
关键词:狗儿爷涅槃 陈贺祥 土地情结 农民形象
中图分类号:I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7-0105-02
《狗儿爷涅槃》(1986)以狗儿爷陈贺祥的人生遭际为线索,运用富有新现实主义特色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具有典型性和悲剧性的农民形象,展现了1949年之后大陆农村的发展史和大陆农民的心灵史。剧中人物形象丰富而复杂,对按阶级区分来塑造人物的刻板方式进行了突破,尤其是剥削者祁永年与被剥削者狗儿爷间既有对立又有共鸣的关系,展现了对立的阶级在共同的经济结构、共同的历史阶段产生的复杂联系。《狗儿爷涅槃》在戏剧结构、叙事手法等形式方面也进行了重要探索,摆脱了封闭单一的戏剧结构,以多样的艺术结构表现主客观世界,散而不乱;戏剧的叙事手法化用民族戏曲结构方法,博采隐喻、象征、心理外化、时空错位和间离效果等中外戏剧手法,产生了迥异于易卜生—斯坦尼传统的叙事效果,可谓是新时期大陆话剧探索的集大成作。
一、门楼与土地
《狗儿爷涅槃》一开头,便是一个颇具悲剧性的暗夜。在这个夜里,狗儿爷擎着微弱易灭的火光,立在旧门楼前,“像一只困兽,张望着,捕捉着,也伺机着”。剧作家第一场便安排了狗儿爷与祁永年的交锋,以及陈大虎与祁小梦的共谋,通过父一代与子一代的并置,暗示了陈、祁两家的复杂关系与父子两代人隐伏的深切矛盾。祁永年既是狗儿爷仇恨的对象,又是狗儿爷梦想成为的对象,面对李万江所代表的新政权,狗儿爷一边感念其为穷人出头,一面又不能理解集体化的政策。狗儿爷虽然与李万江同路,但却与祁永年同心。
如果说狗儿爷与李万江的矛盾集中在土地上,那么陈大虎要推倒门楼的行为,则是对狗儿爷的无力守卫的权力发起挑战。祁小梦的探问(“门楼是你爹的命根子,你敢动?”)正揭示了门楼之于狗儿爷的复杂意义:新政府的赋权(“你老祁家吹灯拔蜡,完蛋啦!高门楼……姓陈啦!……你狗儿爷有这么大权力?有!谁给的?咱政府!”)。门楼作为祁家权力的象征,在政府的支持下被分给了狗儿爷,也就意味着狗儿爷从祁永年那里获得了社会资本,实现了“翻身”。然而,狗儿爷仅仅获得物质意义的门楼,门楼作为菲勒斯(Phallus)的象征性意义则交由新政府保存,因此当物主狗儿爷无力捍卫门楼,他自然想到求助于保管门楼象征权力的新政府。但狗儿爷对李万江这个村长控诉有人要“拆我的门楼,摘我的心”,李万江只能以无力回应:“我不敢管,不能管,也管不了。”苏连玉甚至暗示,乡长也无法阻止门楼被拆毁的结局。显然,作为菲勒斯的门楼,和被变卖的门楼一样再次发生了流转。门楼的两次流转,体现着截然不同的两套逻辑。前一次流转遵循着阶级斗争的逻辑,狗儿爷作为受苦人分得地主的“浮财”,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党和政府则获得乡村社会的领导权。而在后一次流转中,不管是接待日商的乡长、无力管理一众“能人”的村长,还是作为商品被出卖的门楼,都遵循着市场的逻辑。
“门楼”代表乡土社会的面子和权力,而土地则更贴合狗儿爷的生命,它是狗儿爷的魂之所系。对狗儿爷来说,土地是比亲人还要亲的存在,“这地可不像媳妇……地呢,又随和又绵软,谁都能种,谁都能收。……地不跑,它陪着我,我陪着它。”土地更与狗儿爷的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狗儿爷获得土地伴随着妻子的横死,其失去土地引发的疯癫,又促使与后妻无奈出奔,而耐人寻味的是,冯金花正是推动狗儿爷失地的助力之一。(她曾向李万江控诉:“你要‘一片红,是我帮忙替你揭了‘黑膏药。”)狗儿爷在暮年,似乎从对土地和门楼的执念中稍稍醒转(反讽的是,陈小虎问狗儿爷“又晕乎什么呢”),思念陈小虎的生母与后母,而陈小虎只是平静地回应:“亲妈死了,就为您那二十亩芝麻……”“后妈走了,就为您死心眼,想不开……”这暗含着对狗儿爷不顾亲人、一味执迷土地的指责。子一代的陈小虎已经不能理解父辈对土地的痴恋,只将其视为“舍命不舍财的土庄稼孙”。然而狗儿爷最后紧抱门楼的举动,以及对陈小虎这一眼前的亲人的无视,恰恰说明他的“醒转”,只是对即将失去门楼和土地的应激反应,他无力对抗眼前这个长大的陈小虎,于是借由对“虎儿的妈”的思念,试图获取作为父的力量。妻子、亲人又一次输给了狗儿爷对土地的执着。
二、作为文化镜像的农民涅槃
美国学者布里恩·汉德森曾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1]今日重读《狗儿爷涅槃》,不难发现其对农民形象的书写,与50—70年代迥然不同:这是一个打不倒、改不了的倔强老农民。如果说在50—70年代的农村叙事中,狗儿爷是一个注定被淘汰、被遗忘的“历史中间物”,那么到了80年代中期,原本立志教育农民的干部也落到了“历史中间物”的地位,“教育农民”成了对教育者的巨大嘲讽。只有集体化前夜卖地、集体化困难时期瞒产私分、改革年代见风下海的苏连玉,才最受陈、祁夫妇及其代表的80年代赏识(“要不您怎么老不吃亏呢”)。
另一方面,狗儿爷对新政权既认同又悖逆的矛盾态度,又颇耐人寻味:他既“不忘新社会的好儿,不忘大救星的恩”,又堅守一家一姓的财富观,他恨祁永年,恨的却是“姓祁的”而非地主阶级。他始终把血肉情置于阶级情之上,不理解何为阶级仇恨,当人们要拉祁小梦开斗争会时,狗儿爷的对策竟然是让祁小梦“告诉他们,你更名改姓了,叫陈祁氏”。似乎“地主”“贫农”的这套阶级话语,丝毫没有在狗儿爷心中留下烙印。
狗儿爷又是80年代文化政治的一个镜像:在维护新政权的前提下,从不断革命走向改革开放。正如汪晖所言:“‘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事迹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等被视为典型的‘80年代的论题,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来自 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2]80年代的改革延用了50—70年代的众多能指,却变换了其所指。如果将《狗儿爷涅槃》中的狗儿爷、祁永年、李万江与《创业史》中国的梁三老汉、姚士杰、郭振山进行对比,其中延续与断裂、同构与异质的复杂关系就能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而对《狗儿爷涅槃》的重读,或许能有益于我们把握改革年代对乌托邦想象的重写与转向:从“劳动乌托邦”①到“市场乌托邦”,从“中式乌托邦”②到“普世乌托邦”。
最后,不妨关注全剧的关键意象——涅槃。当时有论者把剧末的涅槃视为“曲终奏雅的俗套”,认为这种设计“大概仍是一种政治意识作祟,以为只要是劳动人民形象,戏的末尾总要拖一条光明的尾巴”,还认为即使大火指向新生,也只能是狗儿爷的子孙获得新生,而狗儿爷决无新生的可能[3]。这种说法饱含对“政治煽情”的警惕和今必胜昔的信心。涅槃的意象显然并非是俗套,也未必表示一种通向新生的仪式,它暴露出剧作家面向未来时的一种犹疑和暧昧态度,更揭露“80年代”的农民甚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之复杂。如果说陈大虎等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自己在“80年代”的命运(无论成败),那么过去唯一没有被阶级话语打上烙印的狗儿爷,如今也依旧不肯对新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作出妥协,他的火烧门楼,分明在无奈中表明着一种坚定拒绝的态度。
三、结语
如何写农民,始终是新文艺作家们挂念的问题。然而,不管是鲁迅式的乡土文学,还是茅盾式的乡土社会剖析,又或者是政治式写作,都未必能获得农民主体的认可。如果说50至70年代主导的农村叙事,以将农民建构为一个群众性主体或阶级主体为旨归,意识形态通过扮演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的角色来发声,从而遮蔽了农民的个体经验;那么,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个体经验的解放和浮出历史地表,似乎也并未改善农民的失声困境,农民的声音仍旧缺席,意识形态想象农民的现象并未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农民主体不但被规范,甚至有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被新一代写作者忽视的可能③。
当然,作家创作农村题材作品是否必须如实展现农民的形象,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4]或许对作家来说,重要的并非笔下农民形象是否如实反映了农民的真实面貌,而是其对农民的塑造能否为农民接受,并进而为沉默的农民发声、立言。
注释:
①蔡翔认为,劳动或劳动乌托邦叙述,是“革命后”时代的重要概念,“在这一叙事中,‘劳动承担的不仅是伦理的正义性,也是政治的正义性;不仅发展出对所有制关系的变更要求,也发展出对国家政权的新的形态想象。”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页。
②按照林毓生的说法,所谓“中式乌托邦”,指的是一种强烈现世宗教性与政治性彼此加强的封闭系统。参见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文收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67-469页。
③杨庆祥曾用几个关键词总结出“80后”文学的美学症候:城市、个我、反讽和历史虚无感。这似乎正暴露出“80后”写作对农村经验的隔膜与兴趣缺缺。参见杨庆祥、金理、黄平:《以文学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92页。
参考文献:
[1]布里恩·汉德森.《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J].戴锦华,译.当代电影,1987(4).
[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林克欢.一代农民的终结:评狗儿爷[J].文艺研究,1988(1).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