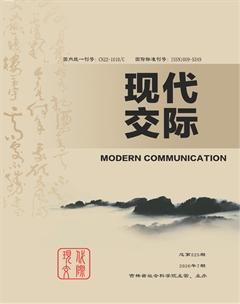美国的多重面相
李一凡 李光泽
摘要:作为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作品中展示了多重而复杂的美国面相。被建构的美国“他者”形象,成為其折射中国这一“自我”形象的关照对象。福柯的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为阐释严歌苓作品中的美国形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美国作为正面形象,表现出乌托邦的特性;同时,美国又被描写为一个自由无序的空间,折射出人的自私、种族歧视、社会的异化等负面形象。
关键词:美国 严歌苓 乌托邦 异托邦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7-0097-02
自20世纪90年代严歌苓的作品问世以来,中国的严歌苓研究逐渐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镇,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女性论、人性论、文化论、叙事论、形象论。在众多的研究中,有关严歌苓小说中的美国形象研究却不尽如人意,基本处于初始阶段,而且对原文本解读不够详尽,议论流于空泛,缺乏理论的指导和系统性。罗月兴的《严歌苓作品中的美国形象》、朱耀龙的《论严歌苓汉语写作中的美国形象》、向忆秋的《想象美国——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论文。而从福柯的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阐释严歌苓作品中的美国形象尚属空白,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开展新的尝试。
一、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
自古希腊至近代启蒙运动,乌托邦思想存在于众多历史形态之中,它的本意是“哪儿都没有的地方”或者“理想之乡”,是人们努力寻求却又“求之不得之处”。因为乌托邦是凌驾于真实历史之上的道德理想的产物,它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不确定性。一方面,道德乌托邦是人类希翼的完美所在,而另一方面,历史的真实则给人们留下不完美的遗憾。乌托邦思想的道德感伤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正是基于这种不一致的意识下形成的。作为批判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乌托邦的存在意义不在于它能否达到所谓的“理想之乡”,而只在于它指引人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维系一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和超越现实的意识。
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乌托邦的内涵及其概念也不同,它的波及范围甚广,文学、哲学、宗教、神学、社会,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概言之,乌托邦有三种传统理解:乌托邦即空想,它是不科学的,无法实现的;把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相关联,把社会主义分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把乌托邦理解为一种文学体裁,如“乌托邦小说”“幻想小说”[1]。
福柯以乌托邦为参照,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异托邦”,1984年他在另一则报告《另类空间》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详尽的阐释: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它或者是完美的构想,或者是现实的相反面,总之,乌托邦是非现实的空间;而异托邦是现实存在之地,但它们却时时通过自己的存在展现、质疑和颠倒现实,并因此成为对现实构成威胁的另类空间[2]。福柯认为,世界存在着多元文化,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眼中,彼此所处的不同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就是说,我们虽然身处同一个星球上,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彼此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文化生活。自然,这种异质文化无疑会成为作家在描写异国的国家形象时的背景。在严歌苓笔下,美国这一国家形象,作为正面形象,表现出乌托邦的特性;同时,美国又被描写为一个自由无序的空间,折射出人的自私、种族歧视、社会的异化等负面形象。
二、严歌苓笔下的美国
作为当代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严歌苓1989年留学美国之后,由于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其作品中描绘了丰富多样的美国形象,作为“他者”形象的美国,成为严歌苓折射中国这一“自我”形象的关照对象。按照福柯的异托邦构想,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是一种偏离性的异托邦,那里的人的行为偏离了正常要求[2]。在《扶桑》中,医院、拯救会、中国妓馆是严歌苓构建的真实存在而又略显虚幻的“异托邦”。在美国这一异域空间,正常的规则和身份认同被颠倒了,美国被描写为一个自由无序的空间,折射出人的自私、种族歧视、社会的异化等负面形象。于是《扶桑》中的医院,就成了禁忌的被隔离的场所:“一所孤立的房在死街尽头。窗子下半截被砖石和木条封死,顶上留一掌宽的空隙,它放射出的黑暗在亮起来的早晨显得那么醒目。这就是那座人们说起便打寒噤的医院了。克里斯拴好马,一面仔细打量房子。房子的建筑意图是隔离内与外:外面的人凭你怎样努力也无法探清它的内里,没人能爬上那么高的窗,即便爬上去目光也绝无可能伸进那缝隙。门是紧锁,锁与这房这门是失比例的大。”[3]108医院显然成了恶的空间,严歌苓对境况进行了极为放纵的描写,使个体的人被安置在一个无法逃离的空间里。身患痨病的主人公扶桑被秘密转移到这里等死,作者通过扶桑,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这宛如人间地狱的禁忌之地:“扶桑的眼力慢慢锐起来,渐渐穿透了黑暗。医院里有四张床,叠摞起来,只占两张床的地盘。眼力再锐些的时候,扶桑看见对面床下有只鞋。鞋歪在那儿,像孤舟搁浅。床上没人,扶桑觉得那鞋一定还有体温。”[3]102医院本来是救治病人的地方,然而这里却成了虐待和剥夺人生命的危险之地。后来在克里斯的揭发下,医院才得以被媒体曝光。床上的指痕与齿痕,黑的血迹和爬满蛀虫的墙。这些异质因素的不断引入,美国在此被描写成一个颠倒常规的异质空间,折射出人的自私、种族歧视、社会的异化等负面形象。一直被看作移民天堂的美国,其国土上也有难看的疮痍。严歌苓笔下的美国,与福柯的异托邦构想完全吻合。
然而,严歌苓并未止于此,她没有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对美国一味地批判,而是站在中西文化的中间地带,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较为客观而又复杂的美国形象。严歌苓在她的小说中对美国的叙述,建构了一个异托邦,完全背离了理性和真理,但同时她又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具有救赎意义的乌托邦式的美国形象。不过这里的美国只是她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是她超现实的理想主义下的乌托邦。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4]。严歌苓小说中经常出现美国白人男性拯救华人女性的场面,扮演着救世主的美国人在与华人交往中,常常把自己幻想成勇敢的“骑士”,对中国女性进行爱的救赎。作为美国新移民作家的严歌苓,她没有偏向于东西方的任何一种文化,而是对两种文化冷静思考,以一种冷静的理性态度,重新构建起美国这一他者形象,极不谄媚,亦不贬损,呈现出“文化间隔”后所独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小说《扶桑》中,严歌苓塑造的男主人公克里斯,柔弱敏感,对于扶桑有着俄狄浦斯情怀、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东方主义迷恋和骑士般居高临下的拯救幻想[5]。克里斯对于扶桑这个东方女子充满了好奇,并爱上了她。克里斯盼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像“骑士”一样,把可怜的扶桑从黑暗肮脏的生活圈子里解救出来。在他的梦想中,自己是一个高大威猛、手持长剑的敢爱敢恨的骑士,他要去拯救那位被囚禁在牢笼里的东方女子。当病重的扶桑将被活埋时,克里斯求拯救会的人救了扶桑,并送入基督教拯救会。后来,在自我牺牲精神的驱使下,克里斯又想通过和扶桑结婚来拯救她。可以说,《扶桑》中克里斯的这种西方骑士精神的救赎行为,正是严歌苓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这里的美国是她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承载着她对乌托邦式的美国的渴望和归属感。严歌苓颠覆了以往西方殖民文学中白人男性一贯恶的形象,表达了她对待异文化的态度: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东西方民族应该抛却成见,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相互尊重。抛却以往作家狭隘的民主主义情结下的“东方主义”,严歌苓以其冷峻而又充满睿智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美国形象。
三、结语
严歌苓关于美国形象的塑造,是美国这一“他者”的想象在中国这一“自我”形象中的映射。她游走于东西文化之间,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更为全面立体的美国形象:美国作为正面形象,表现出乌托邦的特性;同时,美国又被描写为一个自由无序的空间,折射出人的自私、种族歧视、社会的异化等负面形象。美国形象的双重面孔,体现了作者对他者文化的认同与拒绝的矛盾心理。
参考文献:
[1]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J].北京大学学报,2000(1):130.
[2]孙纯,任卫东.中国的多重面相: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空间”[J].外国文学,2017(5):132.
[3]严歌苓.扶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4]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2-123.
[5]刘珊.东方幻想下的西方骑士:《扶桑》中的克里斯性格解析[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6):93.
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