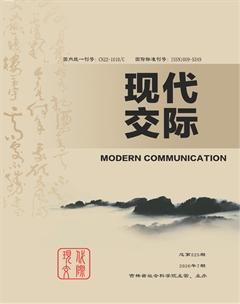从叙述策略看《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我”
周荣荣
摘要: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范本,它不仅呈现了女性的个人化经验,还为如何叙述这一经验提供了思路。其叙述策略包括运用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视角及动态变化的叙述视角,通过时空的停滞和跳跃方式表现对鬼、梦、神秘女人的特定意境的叙述策略。借由对林白叙述策略的分析,剥开“我”的外纱,探寻故事人物形象的虚构与真实的丰富性。
关键词: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 “我” 叙述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7-0091-02
《一个人的战争》因私语的形式、大胆的女性心理描写而引起争议,因此林白也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林白本人则认为“个体差异比性别差异更大,更值得变成文学。”[1]《战争》中,林白针对“我”这个个体的形象,运用了第一人称回忆性视角及多重叙述视角进行突显;把“我”放在一个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解释,“我”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多个“我”,形象变得复杂而富有存在感;“我”最富有个体差异的,则是依赖于对鬼、梦、神秘女人的超现实的想象的运用。
一、叙述视角的混杂的“我”
林白的《战争》中,叙述者和人物分不开,这主要是第一人稱“我”混淆了视线。林白在《战争》中出现提示多米只是虚构人物的例子:“多米,做一个被虚构的孩子是多么幸福,虚构的孩子就是神的孩子。”[2]100多米作为被叙述者,她只存在于故事中,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然而,一旦加入叙述者“我”之后,故事就出现了混杂的“我”。“在全世界,除了多米,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回想我的童年时光。”[2]4这里多米作为人物出现,“我”也作为多米出现。这个“我”便是叙述者,也会被认为是作者,这是因为“叙述者以自我称代、自我显现的方式,把自己同作家在形式上融为一体”[3]16,导致了认知上的混淆。但按照布斯的观点,“叙述者是作家在小说中的代言人,是小说所有话语行为的行为主体。”[4]即叙述者被认作是作者叙述时的替身,和作者是有所区别的。
叙述者“我”和人物“我”混杂不仅是因为二者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还因为林白采用的是回忆的叙述方式。回忆意味着是用不同时段的“我”的两种眼光看同一事件。第一种眼光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种则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二者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战争》中此时的“我”的眼光与彼时的“多米”的眼光穿插交错在一起。多米的眼光贯穿始终,而叙述者“我”总时不时地要插上几句。“我”的眼光成熟、冷静地对彼时的“我”(多米)审视,试图揭示本质。故事“我”是个单纯天真,会犯错的女孩,“我”则以理智的眼光看到“多米”的无知与不幸。这两种眼光开始是分开的,渐渐融为一体,便更难分清二者。
此外,林白还采用多角度叙述视角转变的策略,让读者对“我”产生混杂的观感。当以叙述者“我”回顾过去的视角讲述故事时,读者会怀疑性地看待这份记忆。而当采用第三人称视角时,叙述者不再介入:“多米和男孩坐在山顶的石头上,听着男孩说他自己的事情,多米想单调的读书生活竟然就这样充满了她四年的光阴,毫无光彩和刺激,这点奇遇是多米弥足珍贵”[3]18。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故事时,读者不会将叙述者代入进去,反而会更相信叙述者讲述的真实性。
二、时间、空间下存在的“我”
“真正的叙事文学,总是‘个人的存在学。”[5]即“个人”是叙事的主体。《战争》中,“我”无处不在,且身份多变,让人存疑,这是由回忆姿态下的时空跳跃性决定的。《战争》经常陷入到回忆的时空中去,但是这个回忆的真实与否很难把握。每当相信这个“我”讲的事情时,叙述者便会跳出来,“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个北诺,除非她本人看到我的小说,亲自向我证实这一点。”[2]10不管林白如何模糊概念,都只证明了其实回忆只是一个时空观察点。通过这个观察点,林白将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想象发生过的事情、发生过但却带有主观色彩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显露或者隐藏背后存在的“我”,拉近或拉远“我”与读者的距离,以此表明“我”的存在。
人物多米从总角到而立的成长时光整体上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遵循从童年到插队,再到大学毕业之后在图书馆工作后旅游,以及成为电影厂编剧后恋爱并恋爱失败后的逃离这条主线。但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着重对时间做停滞处理,即把人物某一年发生的事拿出来做具体的描述,二者结合起来构建了存在的“我”。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中间着重描写了包括五六岁时的自摸,十九岁的抄袭,二十九岁的恋爱等情节,这种成长时间和时间停滞结合起来的运用有助于促进读者感受作家的主观性体验。借由时间的距离“使叙述者能够对往日的痛苦和欢乐作出更为理性的评价”[6]。因此,叙述者“我”能够超然于人物“我”。
时间与空间一般是分不开的。巴赫金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7]林白在叙述人物时,采用线性时间和停滞时间来充实人物。在这过程中,空间则依着时间在变化。比如线性时间下,空间表现为地点的转移:童年在家乡B镇;大学在W城;工作恋爱在N城;最后逃离到北京。这里时间和空间都为林白自己设置,属于故事时空。时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故事,而且在设置时便带有作家的策略,展现存在的叙述者“我”。不仅如此,故事之外的文本时间,也表现出叙述者“我”的形象特点。如:“她说我无论如何要留下一个纪念,我不能什么都没有。她说着就哭了起来……倒像一出拙劣而不真实的戏剧。”[2]181在这段叙述中,叙述者并不是故事中的人物,由于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将人物和自我分得很清,叙述者没有进入人物的时空,因而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了双重时空。
此外,小说中互文叙述策略的运用也伸展着时空,彰显着“我”的存在。在小说的开始和结束,林白就引用了《同心爱者不能分手》里的原文来表现这一篇小说里“我”的自恋和某种隐秘的状态。而在讲述美丽的姚琼最后落到卖咸鱼的境遇时,“我”认为姚琼不应生活得如此粗糙,因而选择在一篇小说《日午》里虚构了另一个结局。也就是说,在《战争》中,“我”选择了互文的方式,讲述两个时空,不管是自恋,还是具有小资情调的观念都只是为了突出“我”的形象。
三、神秘加持下立体的“我”
除了叙述视角、时空的运用让“我”的存在更显著之外,林白还采用了一些神秘的事物塑造“我”的形象。《战争》中,“我”追求超越世俗生活的东西,讨厌被限制,想跳出平凡的生活而飞跃到超现实的境界。为实现这种境界,林白描写了“我”神奇地被相中的命运:“我不知道神秘的事物为什么总要找到我”。“我”对鬼的好奇和害怕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被引述,借此到达神秘的未知。林白将小说中“我”对鬼的兴趣进行了解释:“我”出生在广西北流县城里的B镇,离鬼门关只有八公里。借由靠近鬼门关的出身,“我”家乡的真实程度进一步被确认。同时,“我”对鬼的兴趣出自于一种对未知的好奇,符合“我”爱幻想、爱冒险,勇敢同时又胆小的形象。鬼属于神秘想象事物的一种,林白通过对“我”靠近鬼门关的身份,以及关于鬼的奇思异想的描写,实现了对现实事物的超越。
做梦也构建了“我”从生活到超越生活的神秘渠道,为理解“我”做了注解。《战争》的第一章里有两页专门描写梦境。“我”对生活中认识的人和事在梦中的编排,成为一种隐秘的征兆。梦在文学中指的是虚构的象征产物。弗洛伊德曾说:”梦是某种其他思维过程的替身。”[8]53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讲到梦也就是向读者敞开“我”某种思维的思考。《战争》中,读者看到了“我”梦见自己的亲人死,自己死,还有八岁之前反复做的彩虹的梦。梦带有二次叙述的特点,会将读者引向虚构的现实。一般认为,做梦是因为在现实中没有满足的欲望而在某种思维层面构建以求得到满足[8]69。“我”梦到外婆和母亲的死,不是“我”渴望他们死去,而是“我”害怕他們死去。因为一旦他们死去,“我”便会成为孤儿。“我”在这里其实是以缺乏安全感的形象出现的。
“我”的形象的神秘感还通过神秘女人总是和“我”相遇隐现地表现出来。“我”在对童年、大学、旅游、恋爱等的现实回忆中都夹杂着虚构的神秘女性的故事。她们指引“我”进入某个神秘空间。借此,“我”能够逃离现实,遁入超越平凡的生活的境界:“美丽而奇特的女人,总是在我生命的某些阶段不期而至,然后又倏然消失,使我看不清生活的真相。”[2]10这些神秘女性有许多的共同点:美丽、独居、孤寂、神秘莫测,且具有超常的能力。她们或是能接通冥界与现实;或是能指引记忆,甚至能超越生死。除此之外,这些神秘的女人往往会选择“我”。其实“我”的命运在神秘女人的映照下有了隐喻。神秘女人就是超越现实的“我”。这些形象既表现出“我”欣赏女人的心理,又折射出“我”作为女性的压抑与幻想、欲望与期盼、灵魂与寄托。
四、结语
“我”的混杂其实是由于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和动态的叙述视角造成的。理清叙述视角的问题,叙述者“我”和人物“我”便可以剥离开来。林白借由时空叙述策略把“我”巧妙地融入故事叙述时空和文本叙述时空,使“我”飘忽不定,能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穿梭。“我”的形象逐渐立体化还离不开神秘的事物:“我”出身于靠近鬼门关的地方,使“我”具有许多奇思妙想,“我”能够经由现实到达超现实的想象空间还借由“河流是地狱的入口”这一说法。“我”做的梦则由潜意识层面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我”的矛盾和害怕。而神秘女人的出现和指引则让“我”超脱于平凡生活的界限,拥有神秘感。林白正是借由这三个方面的叙述策略,表现了个体的“我”最大限度上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林白.生命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J].当代作家评论,2005(4):121.
[2]林白.一个人的战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祖国颂.叙事的诗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4]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4.
[5]谢有顺,李德南.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J].文艺争鸣,2014(4):25.
[6]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
[7]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小说理论[J].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4.
[8]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