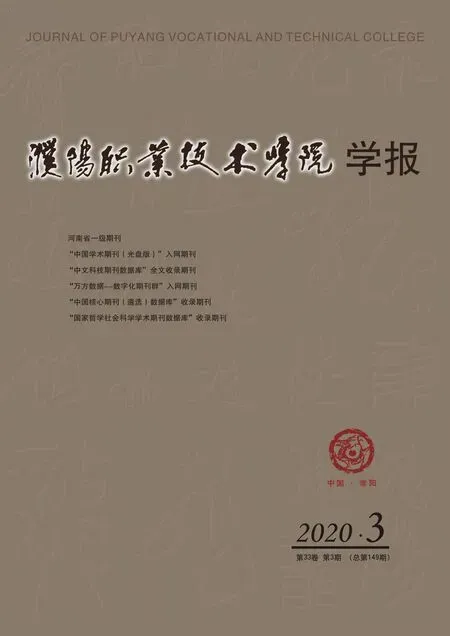隋代墓志之青龙纹饰
孙 晨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墓志是中国古代中高级墓葬中最重要的出土物之一,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墓主人的身份信息,而墓志纹饰也是墓葬艺术的重要代表,是反映社会制度、文化、宗教、丧葬观念、丧葬习俗的重要形式,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较强的装饰功能,且蕴含着当时的绘画特征和雕刻技法,其纹饰形象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人们的丧葬理念和死亡观念,能够在很多方面填补墓志文字难以表达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墓志内容的重要补充和这一时代社会思想的反映。隋代出土墓志接近八百方,其中有纹饰的占51方,而装饰纹饰中最为多样的则是神兽动物纹饰,以青龙纹为代表的四神纹饰在隋代墓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神之一的青龙纹饰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根据五行学说其本身代表着东方,与白虎、朱雀、玄武共同组成了代表天地四方四季的四神形象,198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时期的45号墓的男性墓主人左右发现了分别用蚌壳摆放着龙虎斗图案[1](1066),这可能是华夏龙纹与神龙崇拜的最早实物资料。早期文献也有较为准确的记载,《礼记》卷三《曲礼上》曰:“行,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招摇在上。 ”[2](1250)可见这种观念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到了汉代,四神四方思想和神仙观念兴盛,其多见于瓦当、铜镜和壁画之中,反映了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到了北朝隋代这种思想仍然长盛不衰,并随着墓志这种崭新的媒材而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
一、隋代墓志青龙纹饰的发现
隋代墓志中发现的四神纹饰较多,主要有刘琬华墓志、范高暨苏氏墓志、姬威墓志、李元暨邓氏墓志、张濬墓志、阴云墓志、宋虎墓志、宋忻暨妻韦胡磨墓志、张寿墓志、郁久闾可婆头墓志、韵智孙墓志、段威暨刘妙容墓志、独孤罗墓志、杨钦墓志、李景亮墓志、杨休墓志、史射勿墓志、梁明达墓志等18例,占有纹饰墓志数量的35.29%,可见其特殊地位。
隋代墓志中的青龙形象根据其形态可以分为三类[3](10)。
第一类,无翼蛇形青龙。这一类青龙皆身长似蛇,身体表面有鳞片,背部无翼,有两爪或者无爪。这一类形象的墓志有宋忻暨妻韦胡磨墓志、杨休墓志、史射勿墓志、李椿妻刘婉华墓志、梁明达墓志、独孤罗墓志等六例。其中开皇九年的《宋忻暨妻韦胡磨墓志》中青龙有两爪,身体布满龙鳞,体型如蛇,逶迤前行,白虎身体细长,通体有竖线状斑纹,作奔腾向前状;又大业三年的杨休墓志四神纹饰虽有磨损,但仍可看出青龙身形细长似蛇,身上绘刻着大块龙鳞;又大业六年的《史射勿墓志》从拓片可见蛇形青龙的身上布满龙鳞,作奔腾状;再大业六年李椿妻刘婉华墓志的青龙身形细长,背部有五只上扬的鳍,无翼,身上有短线状龙鳞,作飞奔之势;又大梁永隆二年(618年)的梁明达墓志,青龙头大身细,背部无翼,张口逶迤向前。
第二类,带翼走兽形青龙。此类青龙的身体比蛇形粗壮,四肢有力,身上无鳞片或者鳞片较少,背部皆有翼和鳍。这类墓志包括阴云志、宋虎志、郁久闾可婆头墓志、段威暨妻刘妙容墓志和李景亮墓志、韵智孙墓志等六例。其中开皇三年的阴云墓志中青龙颈部有类似翼状鳍,四肢和身体接触之处带有四翼;开皇五年的宋虎墓志青龙身体粗壮,尾部细而长,末尾卷曲,身体有鳍,背部有翼,作飞奔状,周围装饰有云纹;开皇十二年的郁久闾可婆头墓志中青龙形象清晰,其头部较小,身上有鳞片,背部有鳍,带翼;开皇十五年的段威暨刘妙容墓志中的青龙则线条简单,青龙身体四肢粗壮,背部有鳍,身体带翼,呈现飞奔之状,白虎无翼无斑纹;开皇十五年的韵智孙墓志为上青龙下白虎形象,其特殊之处在于青龙和白虎都是两两相对的一对,中央为一朵花,青龙体格强健,带翼带鳍,两龙向中央奔走,白虎亦向中央奔走;大业元年的李景亮墓志纹饰图像清晰,青龙身上有鳞片,尾巴细长,背部有鳍,带翼,腿部关节和肌肉明显,呈飞奔之状,周围装饰以云朵纹饰。
第三类,无翼走兽形青龙。这类青龙四肢健壮、昂首翘首,身上有鳞但背上没有翼,此类型仅有大业六年的范高暨妻苏氏墓志一例,其纹饰刻于盖题四周,仅仅占据中心位置,极为罕见。
二、隋代墓志青龙纹饰的源流
墓志中青龙的形象在北魏时期已经出现,在之后的隋唐时期发展并达到顶峰,在后代的墓志纹饰中也扮演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在石头上刻绘出四神形象的艺术在汉画像石中已经被发现,这种在相同的载体之上的相同纹饰在不同时代的变化能够构成四神纹饰发展的源流与脉络,其中有一定的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各自的个性,但是无论是在什么时代,墓志上的青龙纹饰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隋代墓志上的青龙纹饰同刻画在石材上的汉画像石上的青龙纹饰拥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其直接来源为北朝墓志。根据考古发现,现在已知的较早的带有四神青龙纹饰的北朝墓志为北魏神龟三年(520年)的元晖墓志[3](87),此墓志上的四神纹饰出现在墓志石的四侧,且分别有一对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为整个墓志增添了许多活力,因为空间限制,这里的青龙形象偏小,不如隋唐时期之大气,但是也不失秀美。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尔朱袭墓志和苟景墓志与元晖墓志一样出土于洛阳并带有四神青龙纹饰,尔朱袭墓志的四神纹饰刻于志盖四杀,且单个出现,与隋代墓志中四神图像的构图方式相似,青龙、白虎、朱雀之上皆有仙人乘处羽带飞扬,其形优雅纤秀、神采生灵,其雕饰精细轻巧、疏密有间,无论从布局或细节描述而言,都精美异常。在龙的前面有两位神仙做前导,龙的身后有一位神仙护侍[5](93-112)。苟景墓志将四祌纹饰雕刻于墓志盖四杀下方的四侧之上,它们也单独出现,表现形式基本与隋代墓志上四神纹饰相类,形象为人面神兽,性质尚有争议。其雕刻功底娴熟,青龙形象清雅超脱,画面充满和平之气。
根据以上最具代表性的北朝墓志可以看出,北朝墓志和隋代墓志青龙图像存在一定联系,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墓志多在洛阳地区,因为时代原因,这一时期的墓志与隋代墓志的青龙图像无论是在艺术刻画还是表现形式上还都有所差异,总概其特征如下:其一,北朝墓志中四神青龙纹饰多单独出现,较少成对出现,这与隋代的类似,在隋代墓志四神青龙图像中大部分为单独出现,只有宋虎和李景亮两方为成对出现;其二,北朝墓志上的四神青龙纹饰有的与仙人神兽相组合,而隋朝墓志上的四神青龙图像常与云、山或者花草相组合;其三,风格上,北朝墓志上的四神青龙纹饰往往雕刻得秀雅端庄,隋代墓志上的纹饰亦清秀细瘦,有某些相似之处。
隋代四神图像墓志之中,藏于西安碑博物馆的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段威墓志和隋大业十一年(公元591年)张寿墓志较为有代表性,在其志盖四杀上都出现有青龙纹饰。前者将温弱文雅的四神形象刻绘在神秘的森林之中,奔驰着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虽然四神形象雕刻得极为干练,但它们与周围的物象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流云、树木、山峦与四神巧妙地结合,整幅画面就仿佛是一幅富有生趣的情景故事。后者较多,在墓志盖上既有四神纹饰又有十二生肖纹饰,其新颖的构图方式使其别具一格。张寿墓志盖的盖题四周分别刻有十二生肖,其中三个动物为一组,一共四组,布局合理,整体美观。四神纹饰被刻画在志盖的四杀中央,周围环绕着盛开的花朵,富贵吉祥。四神形象比唐朝墓志上的四神形象要小得多,整体长度也没那么长。志盖上的四神纹饰与十二辰纹以及花卉纹饰都是精雕细琢而成,虽然饱经沧桑,但直到现在,上面那雕刻纤细秀丽的纹饰仍然清晰可见。从以上两方典型墓志看出,隋朝墓志上的四神图像纹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沿袭了北朝墓志中四神纹饰的艺术特点,又被唐代继承成为唐朝四神墓志发展的基石。
通过以上对于隋代墓志与之前的北朝和之后的唐代墓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隋代墓志青龙纹饰在墓志纹饰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汉代的青龙纹饰古朴大气,北朝墓志中的青龙纹饰古朴矜持、秀雅端庄,唐代四神青龙纹饰则豪放大气,而隋代墓志青龙纹饰则介于两者之间,继承了北朝墓志中图像的一些神仙元素,最终在形制和纹饰上走向成熟,同时又转向唐朝墓志青龙图像的大气,又隋代墓志青龙纹饰与初唐风格关系密切,在表现形式和造型塑造上处于过渡阶段。而处于过渡中的隋代四神图像纹饰在形式、位置和图像描绘技法、形象的刻画上已经基本定型,这直接被之后的唐代尤其是初唐的墓志所沿用。
三、隋代墓志与瓦当、铜镜上青龙图像的对比
瓦当是中国古代高等级建筑上的重要构建,作为筒瓦顶端的下垂部分,其不仅具有挡雨保护椽头不受侵蚀的实际用途,也具有较强的装饰作用。瓦当纹饰种类众多,其中图像瓦当之中的四神瓦当则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汉代制作华美、精良且独具美感,并具有深刻的寓意。汉代四神瓦当中的青龙瓦当和隋代带有四神青龙图像的墓志一样,多出土于作为都城的长安地区,因为他们是同一地区前后不同时代的相同纹饰,所以其中必然有继承的部分,隋代墓志中的四神图像在整体上与汉代四神瓦当形象接近,且无论是汉代瓦当上的四神图像还是隋代墓志上的四神图像都具有去除邪恶、祈求祥瑞的美好愿望。两者具有类似的主题和寓意,同时也有一定的差异。首先,两者材料不同。瓦当是以陶土制成,在陶土之上绘制青龙形象、模印之后再进行烧造;而隋代墓志四神青龙图像则是刻绘在坚硬的石材之上,更有利于长久的保存。其次,两者在表现手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汉代青龙瓦当以浮雕的形式展现而隋代墓志以线刻的手段展现;后者主要是平面上的艺术,而前者则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再次,两者使用范围的不同。瓦当主要适用于建筑之上,为生前的居所,青龙纹饰则是生前世界的装饰;而墓志四神中的青龙纹饰则是黄泉世界的装饰。最后,两者在图像上也有较大差异。因为受到不同材料和画面规模的限制两者的图像大相径庭,汉代青龙瓦当刻绘在圆形的画面之内,它利用圆弧的运动感和韵律美,再加上青龙围绕着中央突起的大乳钉进行构图,给人一种圆润、光滑、回环的视觉效果,青龙图像较为卷曲,昂首作腾空飞舞之姿,形象姿态矫健,刻画得富有动感和活力,充满灵气,精雕细琢给人以返璞归真的艺术感受;而隋代墓志中的四神图像主要分布在墓志盖四杀、四侧和盖题周围,都是在长条形的空间内创作而成,因此其形象呈现出修长而绵延的效果。在狭长的区域内精雕细琢,将每个细节处理得精妙无比,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尽管两者艺术特色各不相同,但皆制造精良,优美的造型和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加工更是给整个图像增添了艺术气息,焕发出持久的经久不息的魅力。
铜镜是中国古代用来照面的铜制品,正面打磨得光亮而平整可以用来照人,背面则装饰有各种纹饰,它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和时代价值的青铜制品之一,拥有极强的活力,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铜镜为生人使用,虽然与专门为死者制造的墓志有较大的差异,但都具有相同的青龙纹饰,在汉代铜镜中经常出现一种包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图案,在西汉末期到东汉前期最为流行,包括四神规矩镜、四乳四神镜和多乳四神禽兽纹镜。和墓志中的四神图案相同,两者都具备镇邪除秽、祈求祥瑞的功能,正是在相同的目标追求之下与四神青龙纹饰产生一定的联系和影响。
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从材质上来,铜镜主要是刻绘在青铜器上的纹饰艺术,而墓志上的四神纹饰则主要刻绘在石材之上,载体应用的范围不同;从艺术表现和空间布局上来看,铜镜上的四神被框定在一个圆形的范围内,而墓志上的四神则被框定在一个长条形的范围内,前者往往是四神出现在同一面铜镜上,而后者则多是在同一方墓志的四杀或四侧,前者适宜用来仔细欣赏,而后者较宜远观,故前者尤为精致;在制造方法上,铜镜上的四神通常采用线雕进行创作,即用线条在平面上塑造出有轻微立体感的形象,而墓志则是线刻工艺,这是两种材质的特性决定的。
在纹饰形态上两者的差异也较明显。汉代出土了大量的四神规矩镜,上面的纹饰虽然简单但是精炼而富有概括性,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各自占据一个方位。东汉时期的四神镜风格则由古拙转向精巧,四神往往和瑞兽等配合,充分体现了神仙思想。到了隋唐时期,四神十二生肖镜摆脱了过去的线刻传统,代替以浮雕的工艺,四神形象更加精致华美,运用较粗的线条和空间关系表现出四神形象的动感、活力与四方关系,这种铜镜在唐代之后逐渐衰落。相比之下隋代墓志中的四神纹饰在表现细节上更加准确,但缺乏铜镜上纹饰的立体感。可见,无论是墓志上的青龙还是铜镜上的青龙图像都是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
以上通过对隋代墓志中四神图像纹饰与铜镜、瓦当中的四神图像的对比,展现出了隋代墓志青龙纹饰与其他载体上的青龙形象的共性和区别,可以看到隋代墓志纹饰处于纹饰发展较为成熟的环节,与汉代的古拙深沉的画像石、铜镜、瓦当和壁画相比其拥有更多的艺术加工,但是作为墓志这种狭小空间内的艺术装饰其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
结合以上关于墓志四神图像纹饰与汉画像石、瓦当和铜镜的对比,笔者以为他们的形态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载体的不同,这种载体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其质地影响工艺和空间布局上,瓦当、画像石和铜镜三者材质各不相同,故工艺各异,画像石虽然和墓志同为石材,但是因为定位的主体不同而有所差异,另外,墓志上的四神图像因为空间的阻隔被固定在一个长条状的单元之内,因而其四神形象形态也大致为长条奔走状,而汉画像石、瓦当和铜镜上的则有所不同,汉画像石虽然也为固定的框形空间,但是它更像是一张画布,能够包容众多角色在这张画布上自由地舒展、跳跃,不拘于形态和空间限制,铜镜上的形象则介于画像石和墓志之间,圆形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形态,但是也能够令其充分舒展;另一方面是时代精神的影响,每个时代的艺术风格都具有其特殊性,表现在当时的艺术上也各不相同,汉代的古朴大气和唐代的精致委婉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写照,而介于两者之间的隋代墓志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