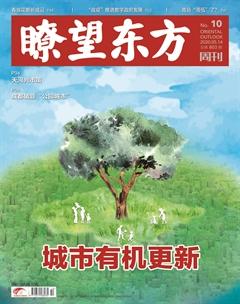纯真年代呈锦绣
易丹

2016年5月22日,书吧正在举行诗画品赏会
在西湖景区,临西子湖、枕宝石山、依保俶塔,有一个标志性的杭州文化景点——纯真年代书吧。书吧所处的环境有着独一无二的景致,正如莫言兴之所至之时的题词:“楼上观锦绣,湖中弄子潮。”
2010年,纯真年代书吧被纳入杭州文化创意旅行路线,2013年被列入“杭州十大美丽样本”,2019年被列入杭州全民阅读活动站……在杭州人心目中,纯真年代不是普通书店,而是谈笑有鸿儒的最美西湖文化客厅。
纯真书吧创始人朱锦绣,也成为书吧的一道景观。她气质温润古典,常常穿着长裙在这样书香浓郁的空间里做着文化活动,或和前来参加活动的读者侃侃而谈。对于过往游客来说,朱锦绣和纯真年代书吧都是美的存在。
“如果时光倒流,我也不会将书吧往市中心开,书吧就应该是比较清净的地方。太理想化也许是一种反商业行为,但是过去恰恰是这样一种反商业行为让我们活了下来。我相信现在也一样,疫情会过去,我们会好起来的。”朱锦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好想开书吧”
有轻音乐、有书、有风景和食物,人们在喝茶或咖啡时聊聊天或者翻翻书——朱锦绣很早就想做这样一个集阅读、卖书、餐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书吧,然而,在2000年去工商局注册时,书吧曾经面临无从归类、无法注册的囧境。
“那时候,书店就是书店,餐厅就是餐厅,咖啡吧就是咖啡吧,还没有一个集图书馆、书店、茶吧或咖啡吧的特点于一身的空间。”朱锦绣解释道,“我应该是第一个提出‘书吧概念的人。我就渴望有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在喝茶、喝咖啡、聊天的时候翻翻书,也可以讨论问题、交朋友,成为一种文化沙龙。”
想到开书吧,还得从朱锦绣的个人经历说起。1999年,还在杭州商学院当英语教师的她因肠肿瘤住进了医院。在绝症面前,朱锦绣想到,医学意义上的死亡会擦去人在世上所留下的痕迹,那么要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才能证明自己曾在这个世上活过?杭州有这么多的茶吧、酒吧、咖啡吧、网吧,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书吧?她想开一个书吧,万一自己不在了,自己的先生也有个地方找得到她。从此,开书吧的念头在朱锦绣的心中日渐强烈,挥之不去。
朱锦绣记得一次室内音乐会,书吧里又是座无虚席,其中包括一位靠在墙边的红衣先生。他是食品配送公司的送菜工人,负责每天将菜从山下挑上来。音乐会开始后,他就一直站在那个位置上安安静静地聆听着……
在朱锦绣的畅想中,书吧应该是把书文化与吧文化合为一体的时尚文化休闲场所。
“在那里应该有一长排书架顶天立地,书不在多,有导语、有书讯、有推荐,让知识精英和白领人士用最宝贵的时间读到对他们最有用的书。”朱锦绣在一篇文章中憧憬,“那里也应该有个旧书寄售窗口,莘莘学子在那里也许会意外地得到一本找寻已久的廉价但有价值的书本;他们也可以把自己闲置一旁的旧书寄售在那个窗口,等着它们的伯乐,积攒起来的钱又可以去买一本油墨香味未尽的新书;那里肯定要有个休闲吧,渴了,饿了,喝杯茶,吃点东西,又可以继续书山的跋涉、书海的扬帆;我还希望有个角落,给像我一样喜欢外语的人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
正是这一篇2000年7月25日发表于《钱江晚报》的《好想开书吧》,打动了当时热爱文学的杭州市工商局局长。2000年9月28日,在杭城偏隅一角的文三西路上,一面写着“纯真年代书吧”的旗幡在沿街的一个屋顶挑了出来。
朱锦绣给书吧制定的理念是“源于书店、高于书店”,以“书文化”为主要载体,通过各种各样人文活动的举办,为爱读书、爱文化的人群提供文化沙龙环境。
神奇地是,书吧梦想成真以后,当时被确诊为癌病中晚期的朱锦绣,体内的癌细胞渐渐消失了。
“物质社会,人们仍向往纯真年代”
朱锦绣的先生盛子潮,生前是浙江文学院院长。他才华横溢,处世率性豪爽。爱妻在生命触及边缘时,想开个可以安顿心灵的空间,他便举债帮朱锦绣完成心愿。由于盛子潮文坛朋友甚众,广结善缘,书吧刚开张,便满堂高座,吸引着爱读书的人。
在读图不读书的时代,朱锦绣希望请到一些作家和爱书的人,对书里书外展开更深入的交流。书吧策划了“每周读一本好书”活动,那时,杭州的各大报纸都会预告书吧的读书活动,书吧每周六下午3-5点总像过节一样热闹,不仅吸引了爱书的读者,也吸引了过去读者只能在书本上看到名字的作家朋友们,他们中间有余华、张抗抗、陈忠实、阿来、王旭烽、唐浩明、麦家、刘醒龙、莫言、北岛、舒婷……
朱锦绣记得,陈忠实回去后寄来了签名版的《白鹿原》;余华来书吧时人未坐定,他的粉丝们已围上去请他签名;“触电”的麦家更红火,他用心写的一篇文章《一片锦绣》让他的粉丝们知晓杭州有这么一家书吧;《天下粮仓》的编剧高锋和《卧薪尝胆》的编剧李森祥在书吧交流碰撞,催生了优秀新作的诞生……书吧举办过无数次文学沙龙、诗歌沙龙、英语沙龙,墙壁上贴满了各种活动的留影。
2001年,讀书沙龙已举办了十多次,有一次请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茶人三部曲》的作者王旭烽。那时读书沙龙定的茶水费是10元,会后一位记者感叹:“这样一场高品质的读书沙龙只收10元茶水费!我们湖南老家的老年人上公园喝杯茶也要10元!”
朱锦绣至今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炎热,书吧所处的杭州文三西路又翻修数日。那天王旭烽如约提前到达书吧,可是开讲时间都到了,就是没来一个读者。朱锦绣极目文三西路,路上不见一个行人。那时她心急火燎,想着如果有人路过,她愿意付他们10元,请他们进来参加沙龙……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书吧不仅开了分店,场场活动都是济济一堂。对于朱锦绣来说,开书吧最有成就之处不仅仅是把一件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些年来在书吧里遇见的人和事,更让她感触良多。
她记忆中,有作家莫言的逗乐题辞、张抗抗给纯真年代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的美好祝福、书吧移址宝石山后韩美林赶在开张之前寄来的招牌墨宝……还有更多身边人和普通人的书吧故事,也让她倍感纯真年代的意义非同一般。
丈夫盛子潮去世后,儿子盛厦辞职帮母亲料理书吧,看着“书店里长大的孩子”成长为上台演讲时从容不迫的样子、在疫情期间独立策划直播活动的样子,朱锦绣备感欣慰。
这么多年来,宝石山的灯光始终温暖着过往路人。他们当中不仅有大作家,更有默默无名的挑夫。朱锦绣记得一次室内音乐会,书吧里又是座无虚席,其中包括一位靠在墙边的红衣先生。他是食品配送公司的送菜工,负责每天将菜从山下挑上来。音乐会开始后,他就一直站在那个位置上安安静静地聆听着……
朱锦绣还记得,曾有一位台湾老先生带了22位学生,到纯真年代书吧请她分享做书吧的故事。而朱锦绣先请他们先参加一场“秋天的读诗会”,结果他们非常喜欢。老先生拿过话筒感慨道:“没想到在景区的山上会有一家书吧,在这家书吧正在举办诗会。”
“他以为整个杭州都会是像我们纯真年代书吧似的存在。”朱锦绣说。
将民营书店开进相对封闭的社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对于纯真年代书吧来说,这条新路也是一条回归路——书吧从一个朋友们的沙龙空间,成长为西湖边的文化客厅,再回到社区做熟人社群。
“离家更近,离生活更近”
2014年,朱锦绣参加第12届中国民营书业发展高峰论坛,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先生指出:书业经营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和卖生活方式转型。
对于朱锦绣来说,这是一道分水岭:历经14年,纯真年代书吧从去工商注册时的无从归类,变成实体书店转型的样板。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进城市书吧、社区书屋等新型阅读空间建设,2018年,纯真年代书吧杨柳郡社区分店正式开张。杨柳郡书店由盛厦独立开辟,这位“80后”掌门人表示,纯真年代的新分店可以说是一次转型,卖书不再是主要目的。新店开张以后,书吧专门为社区办了年卡方便借书。365元一张的借书年卡,一天只要1元钱,吸引了社区里不少业主带着孩子过来借书读书。
纯真年代书吧的工作人员郑秋明表示,她也去过一些外地特色书店,纯真年代最大的不同是文化消费理念。杭州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自古以来又是个风雅的江南城市,相对来讲书香城市的倡导建设力度也大,每年各类读书节、读书活动层出不穷,市民的文化消费理念也成熟一些,对书店书吧这类文化消费场所支持度相对要好。
将民营书店开进相对封闭的社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对于纯真年代书吧来说,这条新路也是一条回归路——书吧从一个朋友们的沙龙空间,成长为西湖边的文化客厅,再回到社区做熟人社群。盛厦给新书吧的理念是“离家更近,离生活更近”。
盛厦认为,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软需求,社交则是硬需求,喜欢书店、住在同一个小区其实是两个非常好的筛选同类的标签,从这方面来讲,封闭的环境并不一定是劣势。朱锦绣认为,做任何事业都有风险,如果一味守成,那一生多无趣。虽然现在很多书店都设计得高大上,但纯真年代书吧有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我们就做自己的‘小而美。我们心平气和地去经营,做成社区的一个文化休闲场所,让大家在社区里有归属感。”朱锦绣说,“书吧应该是社区家人品质生活的理想配置。我希望用近二十年积淀的文化资源和工作经验,更好地打造社区书吧的文化休闲功能,影响和带动社区的读书风气和文化氛围,为街坊邻里营造一个亲切、温暖、富于品质感的文化客厅,让书和人发生美妙的联系,让人和社区产生美好的情愫。”
“坚持到疫情结束的时候”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疫情下的实体书店纷纷面临灭顶之灾。
刚刚复工的时候,纯真书吧里每天只有店员在店里整理书籍,打扫卫生,宝石山上的顾客也非常少,而杨柳郡分店因为周围环境较为封闭,客流量更少。朱锦绣的心情非常低落。

4月7日,朱锦绣在纯真年代书吧二楼手持第20届文学迎新手册(杨晓庆/摄)
不过,朱锦绣已不是第一次面临人生难关。早在2003年,纯真年代书吧就已经和非典进行过一场生死搏斗了。朱锦绣乐观地表示,当年非典对纯真年代的冲击力度更大,因为当时想开书吧的时候,家里积蓄都用在治疗她的癌病上了,所以开书吧的钱除了向朋友借,余下只能通过把唯一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解决。
“非典期间,我们书吧门可罗雀,没有营收,给银行的本与息还不出来,一家人流离失所。”朱锦绣说,“这次疫情对我来说威胁还相对小一些,因为我有一份退休金。书吧一直做下去的话,这样的文化场所越来越被需要。”
凭着近二十年积淀的文化品牌和文化资源,即使在疫情期间,纯真年代书吧的线上沙龙活动仍旧风生水起。例如将近4小时的三八女神节诗会,众诗人在线上朗诵自己和诗友的作品,引起众人的共鸣。
盛厦觉得,疫情下的坚持虽然艰难,但和书店一起成长这么多年,他感受最深的是外界对于书店和书店人所给予的尊重——同样规模的餐馆、酒店或者其他实体店,可能难以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
在朱锦绣看来,从一家独大的新华书店,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营书店,到国营书店在新的市场需求下的改造,再到大商场纷纷引进品牌书店,纯真年代書吧见证了杭州城市的变化,尤其是书店的变化。她希望,书吧能长长久久地存在于人们的品质生活中。
如今,书吧编辑出版《朋友丛书》、每年一辑的文学迎新手册和原创诗歌朗诵手册近30余册,字数超过360万字,累计发放数万册。这些书籍进一步传播了书吧的文化理想,成为全国范围内少有的文化现象。
“借马云当时在央视《赢在中国》节目上的一句话:坚持不一定胜利,放弃必定失败。让我们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坚持到疫情结束的时候,书店会迎来生机。”朱锦绣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温暖所在,众人拾柴火焰高,赠他们一根火柴,书店将以光亮温暖整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