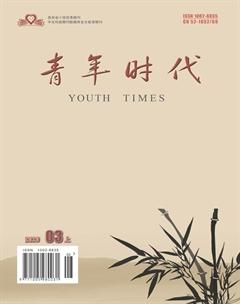幽居中的幸存感
摘 要:对于生前最后一本且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对照记》,张爱玲称其是“三搬当一烧”后的“幸存”展品,虽有保存之名,实际上却蕴藏着张爱玲在幽居中的幸存感,本文将以此为入口,联系《对照记》的图文对照、图像对照和文本对照,以求能进一步呈现处于生命后期的张爱玲如何在与社会、时代相隔离的自我封闭中寻求、确立自我生命的存在感。
关键词:张爱玲;《对照记》;幽居;幸存感
一、引言
《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最早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本文采用的研究版本为1996年辽宁省大连出版社出版的《对照记》),是张爱玲生前最后一本且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通过横跨20世纪20至60年代的54张照片及其附文展现张爱玲的前大半人生:从“悠长得象永生的童年”[1]到“崎岖的成长期”[1],最后随“时间加速”[1]来到了“遥遥在望”[1]的“急景凋年”[1]。对于54张老照片的收入成册,张爱玲称是对“幸存”[1]的“保存”[1]。在《辞海》中,“幸存”意为“侥幸生存、侥幸保存”。这份“侥幸”与其说是“三搬当一烧”[1]的幸运,还不如说是幽居中的张爱玲有意存之。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1]因此,在《对照记》里,生于家族衰落,长于家庭破裂、战乱年代,谋生于冷战格局的张爱玲将祖辈的、父母的、亲人的、朋友的和自己的照片以蒙太奇的方式拼贴成集,在幽居中体会个人在生活颠沛流离和时代快速流转中的幸存感,体现了张爱玲在经历多次个体出走后尝试从最后的自我封闭中寻求、确立生存价值的深层意义。
二、断裂背景里的幸存感
在《对照记》中,父辈的“一味辟谣”[1]甚至是“绝口不提”[1]首先为张爱玲姐弟俩架起了一张与祖辈相隔的薄纱:“我们祭祖没有神主牌”[1],“祖母是照片,祖父是较大的油画像。我们从小看惯了,只晓得是爷爷奶奶,从来没想到爷爷也有名字。”[1]而遗少父亲和出走母亲的婚姻破裂、继母的虐待、母亲的失望和弟弟的麻木则逐步摧毁了张爱玲最直接根本的亲缘依靠,即使是亲近、照应自己的姑姑也为不背上离间母女感情的恶名而声明“她是答应我母亲照应我的”[1]。至此,祖辈的朦胧和父辈的黯淡,使张爱玲在一次次被抛弃和被托付中带上了“孤儿”的印记,身后的生命背景日益缩小(《对照记》中没有与祖辈、父母的合照,没有父亲的个人照,没有父母的单独合照,和弟弟的合照只限孩童时期,和姑姑的合照只有三张),直至留下一张张张爱玲在奔波中的五官派司照。
所以,从阅读《孽海花》那时起,张爱玲开始了“自己‘寻根”[1]:她将祖父张佩纶、祖母李菊耦、外祖母和伯父的照片放入《对照记》并加以介绍(尤其是对祖父母的传奇姻缘和婚后生活),同时穿插对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堂侄张人骏(及其孙儿女)、继母父亲孙宝琦、祖母亲戚曾家等的记述,从一地零碎中找回和祖辈的隔代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1]祖父的几经沉浮与张爱玲的辗转写作,“祖父诗文都好”[1]与张爱玲出色的散文、小说,都是张爱玲跨越父辈这层断裂带找回存在根源的写照——祖辈的传奇际遇和文学才华在张爱玲身上幸存下来了,正如照片上张佩纶和张爱玲神似的“轻藐”[1]目光。
張爱玲与母亲的个人照对照,也饶有张爱玲自我幸存的精神意味。逃离父亲家后,张爱玲投奔了自小的精神偶像与物质偶像——母亲黄逸梵,可迎接她的却是母亲的淑女教育:“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3]但这时的女儿已不是年少的母亲,经济窘困和战乱频发让张爱玲懂得的是“活下去”而不是“怎么活”,所以“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3]的她缺乏母亲的浪漫,也“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1],在《对照记》里形成了母女二人各自独特的个人照景观:母亲多为半身照、全身照,注重整个画面布局,常以时尚淑女之姿出现在风景里;张爱玲多为五官特写,注重个人精神表达,目光无视镜头所在。可见在“出走”这条路上,张爱玲“比母亲走得更远”,是自己选择“自成孤岛”[4]存活下来。
三、物质匮乏的幸存感
儿时对母亲打扮的向往,年少时艰难地向父亲求取学费、难堪地向母亲领取生活费的经历,再到战乱的残酷和卖文为生的打击,形成了张爱玲对物质生活的向往与珍爱,她认为“钱就是钱,与精神和感情无关”[4]。《对照记》不仅充分展现了张爱玲从小到大的穿着打扮:从“淡蓝色薄绸”到“继母的旧衣服”,再到“广东土布”“花绸衣料”“祖母被面”“单色呢旗袍”“浴衣”[1],正如张爱玲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富贵到困窘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即使是在困窘的物质条件下,“考究一件旗袍、一条披肩、一副耳环的心情”丝毫不受打扰,“这是一个封闭的个人世界,绝对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价值被摆在社会价值之上”[5],让自己在自我建构的封闭空间中得以幸存,继续追求物质、享受物质,“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对照记》中,张爱玲提到曾让祖母身边最得力、最熟悉祖母行事安排的老女佣讲点祖母的事情给她听,老女佣“想了半天方道:‘老太太那张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足感“祖母孀居后坐吃山空的恐惊”之深,也体现在她对儿女的管教上,祖母严管父亲的经文背诵,会给父亲“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以免“他穿着入时,会跟着亲戚的子弟学坏”,又给姑姑“穿男装,称‘毛少爷”,虽这“阴阳颠倒”刺激了女儿乃至孙女张爱玲的性别觉醒,却依然阻止不了儿子在烟雾缭绕中继续啃老,“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鉄槛儿圈子巡行”[1]。可见,面对物质日见消磨的家境,祖辈的惊慌努力和继承人父亲的本性如故都或多或少地加重了张爱玲在父辈矛盾(父母离婚,伯父和父亲、姑姑对簿公堂,父亲与姑姑失和等)中能够获得学习、活着、出走机会的幸存感。
同学兼好友炎樱在《对照记》里的出现都是张爱玲和读者的意料之事,活泼的炎樱照亮了张爱玲的孤僻,但张爱玲对其照片的收入,从文段介绍来看,又不为介绍她在自己人生的重要位置,而是更多地强调:她“人缘好,能服众”;入读圣约翰大学后,“她读到毕业,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她有个小照相机,以下的七张照片都是她在我家里替我拍的”;“我从来不戴帽子,也没有首饰。这里的草帽是炎樱的妹妹的,项链是炎樱的。同一只坠子在图四十一中也借给我戴。”[1]让自己和炎樱构成对照,突显自己从年少起与外界隔阂的精神状态和为物质所迫的辍学卖文,并指明是炎樱帮助当时物质匮乏的自己记录、留存了有色青春,渗透着张爱玲在幽居中体会到自我生命延续的幸存感。
四、独居外人的幸存感
从《对照记》的开篇到结束,张爱玲前后呼应着对自己的“不认识”,“十分陌生,毫无印象”,这种贯穿自己前大段人生的陌生感都表明张爱玲无论是与曾经繁华奢靡的家,还是与当下经济发达的世界都保持着距离,即使已经做到一次次出走(从昏暗的父亲家出走到明亮的母亲家、从学做淑女的母亲家出走到深造跳板的香港、从战乱的香港出走到富庶的美国),却始终是一个孤独的“外人”[1],几经周折,只剩下自我这座幸存的孤島,作为她最后的家,过完最后越来越快的二三十年,在这些年里,或许始终不变的除了记忆里的姑姑,便是个人幸存的沧桑——在正处幽居的1984年,张爱玲发现了30年前在香港拍下的独照,“不禁自题:‘怅惘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1]
这种“外人”的自知,其实在《对照记》的儿时部分(图一至图九)已有初现:张爱玲没有一张与父母的合照,父母唯一的合照中也没有儿女的身影,存入的照片及附文呈现的“是受姑姑、妞儿等人照顾的孤独形象”[2],自己仿佛是被收养的存在感,一直伴随至成年、老去。而从赴港前得到负责检查行李的青年“和颜悦色”[1]相待开始,“外人”身份带上了彻底离乡的色彩,再加上之后赴美的艰难立足,更加刺激张爱玲走向自我封闭的幽居生活。《对照记》的图五十二是一张1962年张爱玲回港所拍的派司照,是由一位曾在美任滑稽歌舞剧歌星、老了在三藩市开小照相馆的英国老太太[1]操刀,这张照片的收入和对摄影师的介绍实际深藏着张爱玲同病相怜的自嘲意味,也是她在这种“同病相怜”中对自我作为圈外人能够在圈内独自幸存至今的一种体察感知。
无论是《对照记》所选照片的时间跨度,还是写作《对照记》所收散文的时间历程,都完全涵盖了张爱玲与胡兰成、赖雅的两段婚姻,但两位伴侣在《对照记》里却没有一点踪迹可寻,就像是承接孩童时期的被亲人托付,张爱玲的成年面对的是被伴侣离弃(与胡兰成离婚、赖雅病逝),所以她宁可“抹去丈夫的痕迹、离群索居、孑然一身”[6],仅用一连串蒙太奇式的个人特写呈现时光如梭流逝,呈现“被”字在年华上的幸存:“一个自信自恋的年轻女子转眼间变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5]最后止步在1968年摄于波士顿的个人面部特写,对照终结,仿佛预示着第二年作者张爱玲的独自离去,张家又一个传奇的悄然结束,留下的终究是这些陪伴幽居、“煊赫旧家声”[1]的幸存老照片了!
五、结语
《对照记》在张爱玲逝世前一年与世人读者见面,不经意的时间差使《对照记》带上了逝世者回光返照的意味:重新经历这一生,拾起这生最深刻的记忆。可在这些记忆里,除了友人炎樱,张爱玲没有着重介绍父母兄弟,而是长篇介绍未曾谋面的祖辈和多次提及照顾自己的旁人,没有介绍生命中两位婚姻伴侣,而是介绍香港监护人夫妇、影星李香兰、登记户口的穿草黄制服的大汉、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入境检查的瘦小的日裔青年、摄影师英国老太太等大多为萍水相逢之人,这样也许为的是让自己和世人观看到一只无所依靠、又高又瘦、生活拮据又有点“clothes-crazy”的丑小鹭鸶——也就是文末张爱玲所说的“自画像”[1],带着一副如同“能剧面具”[1]一样兼具悲哀与微笑两种截然相反情绪的五官从出走到幽居,再在幽居中通过重放生命的对照确立此生最后仅有的、站立在个人孤岛上的幸存感——独自出走、自我封闭的生命价值,这种确立如同张爱玲笔下的霓喜,虽“生平坎坷,颠沛流离,总还是保存着那本照相簿,里面有历任丈夫的照片和子女的结婚照,在她不无炫耀地向来客展示那些照片时,似乎找到了存在的证据和价值——个人所涉及的社会谱系中,她总归是占据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点。”[2]
所以,虽然张爱玲在文末说幽居中的她希望“能与读者保持联系”[1],但一旦对照达成,幸存感确立,自我孤岛便找到了存在的根源与意义(至少和同样拥有文学才华的祖父、同样“早了二三十年”[1]的母亲相比,张爱玲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坐标轴上不可忽略的一点),这时余生快进的幽居生活就不再是张爱玲出走的停滞、围困而是不可或缺的、必然幸存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对照记[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
[2]张爱玲.流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3]张爱玲.私语 张爱玲散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4]姚玳玫.没有足够的爱去克服两个世界的鸿沟——从张爱玲的母女书写看“五四”之后个人主义女性的伦理困境[J].学术研究,2017(8):151-158.
[5]姚玳玫.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个案解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6]陈鲲鹏.独异的张爱玲——从《对照记》读起[J].名作欣赏,2015(6):75-76.
[7]高秀川.张爱玲《对照记》的撰述:家族寻根、个人形塑及其他[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18.
作者简介:韩悦瑶,女,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