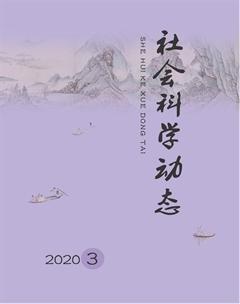还原历史真相的文学路径
摘要:《铁血首义路》从被历史书写疏漏的空白点,即湖北人、武汉人的文化个性切入,描绘了波澜壮阔的辛亥武昌首义画卷,刻画了革命党人的英雄群像以及在情感世界中展露的铁血柔情。这些迥异于鲁迅先生辛亥叙事的明亮色泽,凸显出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作用,因而文学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不过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呈现。《铁血首义路》对话本叙事的借鉴,与方方同一题材小说《民的1911》中的现代叙事风格的相照,可以看出传统叙事方式仍然有生命力,而形式创新和语言表达,在历史小说领域内尚有极大空间。
关键词:尔容;《铁血首义路》;历史还原;文学路径
尔容(原名望见蓉)的历史小说创作,是从书写辛亥革命开始的,《铁血首义路》作为“中国首部还原武昌起义历史真相的长篇小说,中国文学谨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精彩献礼”(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该书的封面定位语),在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前夕隆重推出。与商业意识形态覆盖下“戏说”的历史叙事不同,“严肃”的历史小说作家尔容是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己任的。面对武昌起义这一宏伟的参照系,在建立互文性关系时,尔容智慧地选择了自己的叙事立场和叙事策略。
一、城市的火炉性格:还原小人物成就的大历史
武昌起义的仓促爆发与迅速胜利,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奇特的一页。秉承唯物史观的学者,笃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存在,遂历数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诸多方面因素,以佐证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必然性。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张鸣教授,则一语驳开:“武昌起义一举大获成功,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①进而强调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偶发性、随机性因素,将其作为现代意识的体现,也不能不说“还原”了“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
学界之争,在辛亥首义之地的武汉,曾推演出2011年的一场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大学生辩论赛,且“赛事顾问团队阵容强大,由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章开沅,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冯天瑜”诸大家领衔,一时围观者众。② 但文学介入这一伟大历史节点纪念活动的方式,只能是文学的、审美的,而小说“还原历史真相”,回答偶然必然之辩,则必须在以“文学是人学”美学原则的烛照下,独具慧眼,去发现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忽略的地方。
《铁血首义路》的着眼点,也即是被历史书写疏漏的空白点,即湖北人、武汉人的文化个性。
小说开篇即写道:“武汉这座城自古都是火炉性格。一个拳头扔出去,可以在地上砸出一个坑。一粒唾沫星子吐出去,可以引爆一座城,一个国家,甚至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这段文字看似寻常,却涵盖了很大的信息量,它不仅提供了调和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粘合剂,为全书奠定了基调,而且开篇伊始,就预叙了全书的大结局。正如学者杨义所言:“中国小说擅长于预叙,预叙往往暗示人物和事态在其后的岁月里带命运感,甚至带神秘性的发展和变异。”③
这种“火炉性格”,集中体现在小说着墨许多的曹新生和熊秉坤身上。这一虚一实两个人物出场时都只有15岁,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底层贫民,“不同类,却同道”,由愤青而革命结成了生死兄弟。曹新生自小桀骜不驯,知子莫若其父:“胆子大,做事喜欢头脑发热”。这种性格,在湖北各团体为捍卫国家主权、争取粤汉铁路自办的筹款活动中,以断指明志一节,表现得淋漓尽致。熊秉坤的祖父“早年曾是太平军,随军辗转于长江中下游”,“時常给熊秉坤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教他识字做人”,因此熊秉坤“从祖父那里早就攒足了勇气和仇恨”,受洋人欺辱时能以头相撞,又能“飞起一脚,踢倒了祖宗牌位”,因为他不相信“死人能保佑我们什么”。为了搭救刘银根,便想用爷爷留下的剑“去杀官府,杀洋鬼子”,而“我们要暴动”这句话,就是率先从小小年纪的熊秉坤口里喊出来的。不难看出,对这位在众皆惶惶群龙无首的历史紧要关头,能振臂一呼,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英雄,作者探究人物性格其冰山之下的部分,寻找其必然性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这种“火炉性格”,也成为首义英雄群像性格中的某种共性。王汉在小说中只是神龙一现,其行刺满清大员未遂而投井自杀,行前一语,掷地有声,让人想起易水荆轲。丙午党狱中朱子龙、张难先、梁钟汉、李亚东、刘静庵、曹新义诸人的大义凛然,首义前夜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的慷慨赴死,这些都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在“火炉性格”人身上的闪光——革命团体中湖北籍人士占了大部,这是史实的实录,而汉口人力车夫、苦力、商民因车夫吴一狗被英国人打死激起的反英大示威事件,就“像一堆干草积薪,大有一颗火星即可点爆的气势”,无异于是辛亥首义的预热,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此言不虚。
要展示出这种“火炉性格”,就必须描写独特的地域风情,如黑格尔所言“地方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们的性格有密切的联系”④,中国俗语表达得更简洁直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原清末老武汉这一方水土的历史面貌,包括自然面貌和社会面貌,是还原历史必不可少的内容,此即所谓典型环境描写,小说《铁血首义路》在这方面是十分成功的。
汉口大码头、五国租界、武昌昙华林胭脂巷,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地方。码头江湖的生态,租界工部局的运作,胭脂巷妓院的门道,张之洞力推“新政”的气象,雨后春笋般兴办的新式学堂,应时而起的众多会党,五音喧哗可闻,斑斓杂色可见,营造出氤氲全书流布篇页的氛围性存在,而胭脂巷妓院在某种程度起到了结构上的纽结作用,成为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活动的凝聚点和发散点。许多保留至今的旧地名,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
当小说渐次展开作者设定的人物画廊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那些从历史舞台的边缘,因种种机缘巧合而登上舞台中心的人物,都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号令天下革命党人的孙中山(彼时远在海外筹款)、“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章太炎先生联)的黄兴等人不但没有出现,而且武昌首义的成功完全在其预料之外。
西方新历史主义把大历史(History)和小历史(history)作了泾渭分明的切割,提倡对被大历史遗忘的小人物、普通人物、边缘人物的书写,这一倡导客观上与告别了宏大叙事的某些中国作家产生了共鸣,出于对国家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的反拨,注目书写隐没于符号化的“大我”中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小我”,蔚成一时风尚,于是历史变成了一种背景性存在,小人物裹挟在历史风暴中,只能像沙粒般与世沉浮便成为常态。反观辛亥首义中的小人物,我们不能不为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看到的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惊赞,这些小人物干成了大事情,他们在俯仰之间,走进了历史,参与了历史,书写了历史,这或许可以视作新历史主义中国化,建立中国文化诗学的一个生动例证。
二、风月与风云:还原革命者的情感世界
鲁迅先生写了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中短篇小说,多属于侧面书写,这给选择长篇小说体式的写作者预留了再叙述的广阔空间。简而言之,就是采用一种全景式的、正面强攻式的书写,而创造巨大社会历史含量和审美精神含量,史诗性地为这场伟大革命存留一份文学记忆,似乎成了尔容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因如此,若要“还原历史”,则不仅要还原革命者金戈铁马的斗争生活,还要还原其儿女情长的情感世界,用刘银根那句犹如贾府焦大的一声叫骂,就是“个斑马儿的,是革命重要,还是过日子重要?”对革命者而言,两者其实是很难分割的,而以往革命文学尤其是样板戏中,把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为地切割了。
尔容在小说的后记中说道:“既要考虑男性读者对军事历史小说的口味需要,又要关注女性读者的审美情趣。于是,我把这部小说的基调定位为四个字‘铁血柔情。革命加爱情,战争加生活。”其实这也是战争题材小说,尤其是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惯用的套路,再往深里说,这也是编年体式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的重要区别。西方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奠定了理性化的史学精神,这种传统下的历史叙事要求避免过多的修辞性干扰,平实、白描是其追求的语言风格。中国的历史叙事,被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文学性色彩显然浓烈了许多,但是无节制地肆意铺张描述性语言,毕竟也是史家之大忌,而为史家回避的许多内容,却恰恰可能是小说的血肉,也是小说家功力的所在。
一部旨在描绘“铁血”、再现首义的小说,起笔却在吟咏风月处。开篇犹如一组电影镜头:武昌城—蛇山—昙华林—胭脂巷—桃花坞—人物出场,由远及近,画面感极强。首章便围绕妓女胭脂红,使刘银根与曹玉林构成情敌关系,这一矛盾因曹玉林阴差阳错卷入宜昌教案而受刑讯之灾,误认为系刘银根从中作梗而加深;刘、曹两家儿女登场,冤家儿女由同学关系而结成情侣;胭脂红赴湖北巡警道王士豪酒局,席间听闻杀革命党事,已渐露风云之色。此后小说由风月而到风云,风云中不时穿插风月,两者交织纠缠。“排满、兴汉、灭洋”,风云之色渐浓,遂有花园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间以“湖北有哥老会、洪江会、三点会、江湖会、红灯会”等众多会党,相互表里,风云际会,终至石破天惊,掀开历史崭新一页,而刘曹两家也十年宿怨,一朝冰释,“冤家转身做亲家”。小说以阴柔美和阳刚美的交替转换,调节不同叙事单元的组接,以及叙事情景情调的变化,进而兑现了作者“铁血柔情”、“革命加爱情,战争加生活”的叙事策略。
在这条爱情线索中,曹玉林与胭脂红这一对人物占了不少笔墨。曹玉林本是一身洋服,“眼戴克罗克(crookes),嘴衔茄力克(garrick),手持司的克”的买办富商,若按阶级论分析,应该属于革命对象,他也的确对儿子参加革命百般阻扰,但形势发展不由人,他对革命由排斥到同情、由同情到理解,最后发展到“如果需要带路,或者当当翻译,他就主动凑上去:‘我跟你们走吧!”读者可以从这一人物心理转化细节中窥见出革命高潮汹涌而来,人心思变的历史面貌。
将胭脂红划入革命者行列似乎有些勉强,这位大家闺秀命运多舛而沦落风尘,久锁深院,自然不知何为革命,但“她有种直觉,凡与官府对着干的,必是好人。好人在现在的世道受欺压。不论这人是谁,她都抱以同情”。这是一种出自自身阶级地位而产生的对革命懵懂的、本能的向往,犹如阿Q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不免也有些‘神往了”(魯迅《阿Q正传》)。不同于阿Q只是准备“投降”革命而去结交“革命党”假洋鬼子,胭脂红却以一己之身,实实在在地“介入”了革命活动:当获悉刘银根被捕即将开刀问斩时,她不惜自毁“守身如玉”之志而搭救他,只为了这个黑脸汉子“口口声声要赎自己出去”,便将其作“恩人”看待;曹新义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胭脂红视为“今生遇到的第二件性命攸关的大事”,立誓“负石救溺,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而再次忍受“权色交易的屈辱”,则是为了曹新义系她钟情的曹玉林之子。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妓女形象层出不穷,可以说,胭脂红以一个有情有义的,不是革命党的革命党形象,丰富了这一人物序列。
三、历史与文学:纠缠不清的“还原真相”
对尔容(望见蓉)这部10年前出版的小说,今日“旧书”重读,其价值何在呢?历史小说是小说家族的一大门类,关于它的现状与未来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而重读旧作引发新见原本就是批评常态。
所谓历史小说,按约定俗成的认识,是以真实历史人物、真实历史事件,加以作家的想象性虚构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一个显性的标志是,它通常都是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书名的,比如《李自成》、《张之洞》、《曾国藩》,二月河的“落霞系列”等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约翰王》、《 亨利六世 》(上中下)、《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等,也可作如是观。至于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在作品中所占比例,虽无一定之规,但大都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问题是作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正史,大量的笔墨是留给大人物的,这使得尔容在书写成就辛亥大事的小人物时,单指望历史对其一鳞半爪的记载,很难支撑起一部体量30万字的长篇,于是虚构人物走向前台,承担起起承转合贯穿首尾、捎带真实历史人物的作用,便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叙事策略的灵活调整。好在人物的得失成败,并不以其虚实作评判标准,《亨利四世》中作为伟大典型人物载入文学史的,不是帝王,而是那个叫福斯塔夫的破落骑士。《铁血首义路》的创作也告诉我们,并不存在格式化的历史叙事方法。
《铁血首义路》时间跨度15年,以沉实厚重见长。作者写刘静庵在狱中组织中华铁血军,办报宣传革命,而“狱卒任他们将报纸传递出去”,狱中5年病逝,狱卒和受難囚犯“都抚尸痛哭”,“人人都叫他‘铁汉”,并集资托狱吏将其死讯告知圣公会。胡瑛身陷狱中,却与党人联系密切,还被狱卒看中,许配爱女,对比《药》中夏瑜遭际,可谓天壤之别。小人物的这些举动有受到革命者宣传鼓动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要从武汉人的城市性格中寻找,即码头文化滋养下的豪侠仗义。曹新生起草的振武学社宗旨就是“联络军界同胞振兴湖北武力,推进反满革命”,进而提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让广大黎民百姓都参加革命”的主张,这也明显与鲁迅先生笔下革命者的“孤独前行”相左。
倘若与鲁迅先生的辛亥革命叙事作为参照,将上述内容称为颠覆式的辛亥叙事,当不为过,那么究竟哪一种叙事更“准确”或者更接近“还原历史真相”呢?面对无限复杂的社会与人生,面对一场终结了两千年帝制的伟大革命,与其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去做一道单项选择题,倒不如认同其鲜明彰显的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作用,认同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注目历史的焦点更为可靠;与其判定某种书写为对历史真相的“还原”,还不如将其视为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可靠,这就是克罗齐强调的历史阐释的当代性。但这实际上也不是西方独有的新见,中国古人早就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如此而已。鲁迅立足精英立场,秉承五四启蒙主义,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而时移世易,21世纪的方方、尔容等人,肩头已无需背负这副重担了。
尔容还原历史真相的文学野心,在其书写伍子胥这一历史人物时,遇到了更大的挑战。比起百年前的辛亥首义,伍子胥的故事则上溯了2500年,巨大的时空落差,足以使沧海变作桑田,而史料的多寡,与年代的远近恰成反比。作者熊召政为核实《张之洞》的细节,多次到故宫实地踏看。而尔容笔下蛇山两侧的老武昌城,其基本格局与百年前并无大变,许多老屋犹存,连老街旧巷名字也未改。可以想见,当作家徜徉其间时,其移情作用,足以使人物尽可能近距离地贴近书写对象。明乎此,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小说取材明清者多,而且成功率高,越往前推数量越少,难度也越大了。一言以蔽之,再现式地对历史现场作原生态还原,尤其是上古时代的历史,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具备可行性的,甚至可以说,面对遥远的时空距离,面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对某一方面的“再现”,就意味着是以另一方面的遮蔽为代价的,换言之,考古式的、实证式的写作方式,不是作家分内之事,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作家没有必要越俎代庖。试想如果尔容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力都集中在实证上,无一字无出处,则无异于自缚手脚。比如我们批判歪曲历史、戏说历史的虚无主义,而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显然不在此列,两者都自认为是在书写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正剧,体现的都是国家主义政治观,但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目标指向的并不是一碗一碟的失真,而是作者秉持的历史观。
四、传统与现代:历史叙事的两条路径
对重大题材的策划引领,是国家意志在文艺领域的体现,这一中国特色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之中的,深受史传影响的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永远是常写常新的题材。尔容(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和方方的《民的1911》在同一时间推出,彰显了湖北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回应,同时对历史小说的写作也提供了新鲜话题。
不同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将诗(文学)看作高于历史的文类,“史书是中国文化文类等级最高的叙述文类。‘六经皆史,按这说法,史书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文本类型,即所谓‘经典化文本(cannonized texts),接近许多文化中宗教典籍的地位”。⑤ 就历史叙事的文本呈现而言,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三千年煌煌“正史”的三种基本书写方式。历史小说作为“小说”,亦即语言艺术的一种门类,向来被古人目为“假语村言”,按说其享有的自由度,远非被尊为“高文典册”的史书可比,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就小说创作的总体路径而言,中国传统小说向有“历史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曾讲到“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这影响就是“极多讲古事……多教训”⑥。所谓“讲古事”,用唐代刘知几的话说,是视小说为“史之余”,“可与正史参行”,以“补史之阙”;所谓“多教训”,则来自寄寓褒贬、申明王道的史官文化传统。除了书写内容方面的影响之外,宋人“说话”还深刻影响到历史小说的形式结构和语言表达。直至辛亥百年之后的这部《铁血首义路》,其流风依然清晰可辨。
分章分节的线性结构,全知视角的叙事方法,是这部小说的整体面貌;章节之间的衔接过渡,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收束,给读者留下悬念;一章之内的叙述转换,用“却说”如何如何;新人物的出场,必作一番静态的履历和背景介绍,诸如:“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1859年生。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1884年上书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沿用的是纪传体的标准格式;人物外貌描写,采取的是史传小说的惯用语,比如写刘银根眼中的曹新生:“红唇皓齿,眉如刀锋,目似朗月”,张难先出场,则是“只见他前额秃顶,目光炯炯。眉似鸥翅,嘴似月刀”云云。
方方《民的1911》的叙事手法与此大异其趣。小说设置了一个叫“民”的虚拟人物,这一名字的象征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其开篇第一句话,即道“我设想我无处不在”,“民”是作者为这部中篇划定的一帧取景器,叙事学中谓之“见事眼睛”的“无处不在”,更是叙述上的讨巧之言,有了天马行空而又无影无踪的“无处不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局限便得以缝合,旁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的抵牾便得以消解。有了这一“设想”,叙述者与隐指作者拉开了距离,叙述者即可在革命者、统治者、旁观者之间自由穿梭,在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作无缝对接了,小说遂实现了从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的整体转换,并显示出作家驾驭重大题材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深厚功力。
当我们把两位湖北女作家同一题材不同叙事方式的小说略作比较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尔容的《铁血首义路》首先是在网络上发布的,随即受到读者热捧,之后被三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说明传统叙事手法还是有生命力的,从古老的话本、拟话本中吸取营养的文本呈现,居然和最现代的网络传播方式高度契合,如果再加上喜马拉雅、荔枝等网站“有声小说”的助力,古代勾栏听书的方式似乎又复活了。当然事物还有另一面,传统历史叙事的巨大惯性,使历史小说在形式创新和语言表达方面明显滞后于非历史题材小说(戏说、穿越类不在此列),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关注点大都在是否“还原历史真相”方面,从高阳到姚雪垠、凌力、二月河、刘斯奋、唐浩明、熊召政,等等,再到尔容,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传统演义形式的深入人心,是否会把历史小说演变为一种类型小说,换言之,我们是否需要探索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呢?
注释:
①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② 徐金波、王慧红、周芬:《两岸学子激辩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13日。
③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版,第123页。
⑤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5页。
作者简介:吴平安,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特级教师,湖北武汉,430074。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