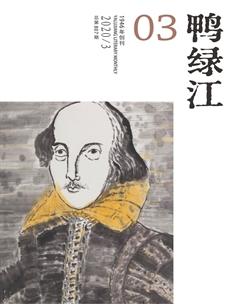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青海诗说”
摘要:诗歌能体现出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因此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文章中通过多角度的诗歌分析,阐述了诗歌所承载的情感以及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影响。
关键词:玉树地震;诗歌精神;苦难记忆;价值重塑
自从2010年4月10日青海玉树地震发生以来,媒体上涌现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表达诗人及民众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高原人民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伤和追索。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主编的诗集《废墟上的花朵》由一场场死亡灾难中肉体与灵魂的对话所构成,凝结百位诗人的民族情结和苦难记忆,对“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进行旗帜般的深情谱写。
一、大爱同心
大爱同心展示的是灾难面前,中华儿女爱比山重、情比海深的骨肉亲情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面对突如其来灭顶之灾,地震诗歌交织生命、死亡、苦难等繁复旋律,但书写大爱无疆是公认主旋律。“孩子,别哭/ 你轻轻地靠过来/ 把你受伤的头依在他的肩上/ 把你忧伤的泪洒在他的胸前 /把你惊魂的花季让他揽在温暖的怀中/ 把你流血的十指让他握在宽厚的手心 。”( 杨廷成《深情的依偎――写给胡锦涛总书记》)“汶川的烟尘刚刚散去/你匆忙的背影仍温暖着这片土地/大西南干裂的田野在声声呼唤/你关切的话语就是那渴盼的雨滴/早春四月,你又行走在三江源头/给西部高地的藏家儿女送来希冀。”(杨廷成《翘起的大拇指——写给温家宝总理》)诗人站在一定政治高度,讴歌党和政府“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治国理念。
对社会各界无私援助,诗人也高度关注。如刘佑《信仰在旗杆上猎猎飘扬》:“……中央领导、地方官员、三军将士/义无反顾地挺住了——/当地百姓、寺院僧人、民间俗众/生命可贵,争分夺秒/藏汉一家,众志成城/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救人要紧/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多救一人。”郭建强《结古诗章》:“我并非神灵,也没有万能法术/但身旁却有千千万万个兄弟/千千万万个如我一般十指鲜血淋漓/却仍然屈似弓弩狠劲扳住那扇正在缓缓合拢的铁门和扣环。”这些诗所贊美的时政,真实与美善的高度融合,以实录现实文献价值,刷新古典诗词再现时政的历史。
对地震中杰出人物由衷赞美是人们高度认同的主题。“我为慈善家陈光标再一次/为他魂牵梦绕的雪域献出的巨大爱心恸哭/我为日籍华人李翀博士心系灾区而流出的一行行泪水恸哭/我为香港义工黄福荣在第一时间舍身救人光荣献身的悲壮恸哭/我为‘雪域最美女孩熊宁的子弟们时时刻刻与第二故乡心心相印的情缘恸哭。”(张翔《玉树,我为你祈祷》)对平凡而高尚人格歌颂,使诗歌有了特别力量。
抒写大爱丰碑,还集中体现在舐犊之情上。如龙仁青《孩子,你睡着了吗》“孩子,你睡着了吗?/也许你梦见春天了吧?/微风徐徐吹拂,/路边的树枝上,/调皮的小鸟正在鸣叫。/或许,还有一只小藏獒,/带你去了,/你刚刚去过的学堂。/……孩子,你睡着了吗?/也许你梦见了草原吧,/小河轻轻流淌,/河边的草地上,/浅红的花蕾就要绽放。/或许,还有一头小牛犊,/带你去了,/你刚刚去过的牧场。”刘士忠《玉树:四月十四日》:“今天我写下朴素的诗句/为自己,也为这块高原上的土地/因为我是她人民中的一个/也是她羊群中的一个。”这些抒写平民百姓挚爱深情的诗歌,构成地震诗歌中最令人难忘和感动的乐章。
严羽《沧浪诗话》说“诗者,吟咏情性而已。” 地震诗歌实际上是最单纯的生命欲求的呐喊,是捍卫生命、珍爱生命的心声,用生命去感受生命价值。
二、坚韧不拔
坚韧不拔展示的是灾难面前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以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的顽强意志。
首先,体现在阳刚激情鼓舞斗志的战歌与慷慨激昂的歌颂型诗篇。如陈世庆《一个崭新的玉树,将会在青藏高原崛起》:“啊,玉树/灾后重建已经启动,/请你一定要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精卫填海的毅力,/有女娲补天的精神,/有同舟共济的优良传统,/有相濡以沫的骨肉亲情,/人心齐、泰山移,/地震算得了什么,/我们有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有13亿炎黄子孙的强大后盾,/一个崭新的玉树,/将会在青藏高原崛起!”“从废墟中刨出太阳/从瓦砾堆抢出花朵/从石隙间救出星月/……人间无法抗拒的大灾/却抗不住人间大爱涌流!/扎西德勒经受又一次熬炼/已变得更加深沉、丰厚。”(白渔《向高原》)
其次,抒写众志成城的民族自尊,让人在这场自然灾难面前力量倍增。如武玉嶂《玉树,惊世宿缘》:“这一天,/我回忆,多少奔腾着热爱你的血液/在诗篇与歌声里让人熟悉你的宁静与洋溢/多少商旅马队奔赴而来/为你遗址上从不萧瑟的卓玛的微笑和巴松的热情/你面对灾难也未改变/把对亲人的疼惜揣进胸膛/把最大的怜悯投入对同生的救助/新寨嘛呢石堆300年的祈愿绕了一圈又一圈/长路,车载驰驱/鲜红的旗子每一面都深情呼唤着玉树。”“你曾是穿越时光的古道驿站/是汉藏通衢中让人流连的茶肆/文成公主的足迹如今依稀可寻/汉藏一家,有说不完的迷人往事/……结古,我从远方来又别你而去/总难忘你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众志成城,你与三江源相聚相依/江流大地,传颂着你诗意的名字。”(谌强《结古镇》)这些真实记录了民族悲痛与坚强的乐章,见证了灾难、见证了生死、见证了灾难中人文关怀的丰厚,也见证了古典诗词艺术与当代诗人灾难诉说“悲与力”融合。
再次,地震诗歌中不少诗人还表现了深切悲悯情怀,这是继承传统又是超越传统的。悲悯不仅是佛家术语,儒家也津津乐道,韩愈《争臣论》即曰:“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真的诗人,无不具有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场地震诗潮产生的诱因是罕见自然灾难,但悲天悯人的元素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抢眼。如才登《玉树,倾斜的天堂》:“我的雄鹰飞翔、歌舞升平的天堂/我的长袖甩开、万人踏歌的乐土/我的经幡猎猎、嘛呢轻诵的圣地/我的三江源头风情万种的草原/你和春潮一起、重重地摔碎在巴颜喀拉脚下/顿时,倾斜的天堂间/木鱼和念珠自慈悲的佛掌滑落。”“你安魂的哀曲在地动山摇时升腾/你百川之源的泪滴/让一场晨昏相连的冻雪降临在古代岭国的琴弦上/……你在废墟间的蹀躞/让一行恣情迭出的足音鼓动在系心萦怀的低诵中。”(肖黛《挽歌》)
三、挑战极限
挑战极限展示的是在世界屋脊、高寒缺氧的特殊地区、特殊环境和山摇地动、天昏日暗的特殊条件下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挑战体力极限、精神极限和生存极限的英雄气概。
“2200多名同胞永远失去了生命,/一万多兄弟姐妹承受着伤痛,/还有那十万父老乡亲/面对着刺骨的寒风/……4000米高的海拔,/缺氧考验着每一个人,/气短胸闷,头痛欲裂,/但子弟兵仍然用手刨挖着瓦砾,/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拯救废墟下的每一个生命。”(陈世庆《一个崭新的玉树,将会在青藏高原崛起》)“玉树受伤了、高原受伤了/刹那间,锅庄没有了色彩/刹那间,山歌充满了悲伤/那些废墟为家/清水解渴的日子里/你依然用高原最坚强的脊梁/承载了民族从未有过的创伤/你依然用西部最矫健的躯体/扛下了人类从未有过的灾难。”(多智合《生命从废墟中延续》)1对这些珍贵诗作的收集整理很好地见证和保存了在大灾大难中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战斗力和强大的民族精神。
地震灾难给人类生命带来巨大苦难和疼痛,澎湃了诗人的情感海洋,他们将自己强烈的情感倾向倾泻于不同诗歌艺术形式中。如高建斌《风吹玉树》:“四月在玉树的路途上/在雨水中与你相遇,要滂沱/直到死亡的静寂/有了与悲伤相等的重量/直到我爱你/还能用剩下的日子和剩下的词语/就这样消失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不是刹那的残忍/从没有过这样多的剥夺/破碎的一天,春天为什么而来/如果四月不为了生长/如果花朵是活着的禁地。”“传说,在这个暴戾的清晨破碎/我看见,格桑和梅朵,一双姐妹/在裂缝中捡起碎片/天空的碎片、云朵的碎片/……梦境,在春天即将降临时破碎/炉火熄灭,一对夫妇/在通向往日的路口看见/道路的碎片、课本的碎片。”(马海轶《救援之马奔驰在祖国的路上》)灾难中的小生命更能触动人们痛感神经,这种强烈灾难意识逐渐积淀为忧患意识,成为一种悲剧性与群体性的表达,最终凝结为情感价值核心。所以作为感情丰富的诗人,或以直接抒情,或以反思审视,虽情感倾向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但他们的“忧患”却是相通的。正是这种“忧患”担当,使人具有了悲剧性,同时也成就了人的崇高。
任何生命都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本能,所以世界虽处处存在物种竞争,遵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但依然有生命延续和发展。每当生命遭到外力摧残,“生”受到“死”的威胁时,人类便自然而然地奋起对抗,面对死亡必然性的抗争,传达的是人对自然恐惧、对生命的热爱。如格桑多杰的《钢铁的臂膀》:“钢铁的臂膀抗震救灾/钢铁的军令在抗击天祸/以命救命、以躯救躯/付出牺牲自我的勇气/拯救还未闭眼的青春/奉献自己宝贵生命的准备/全力救助就要熄灭的人生/人民的子弟兵像长城一样出现在灾区玉树。”这种求生抗死精神是人类心理的共同建构,是共同人性最坚固的基石。“玉树,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在你的废墟深处/掩埋着一代代祖先的遗迹/如果让我,选择你的重生之地/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就在你曾经死去的地方/在那里获得新生的/必将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之乡。”(吉狄马加《玉树,如果让我选择》)对生命不朽的追求让位于对精神不朽的追求,求生抗死意识从生理生命到精神生命转变,是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一种积极超越,是对生命价值的现实而充分肯定。
四、感恩奋进
感恩奋进展示的是灾区各族人民忠厚、善良的质朴秉性,是对所受大爱、温暖、关心、支持、帮助最真挚、最真诚的感谢。更可贵的是,把这种知恩之心、感恩之情转化为精神动力,以重建新家园、新玉树的行动报答伸出援手的人们。
玉树的春天降临在老阿妈浑浊的眼眸中,也镌刻在卓玛坑坑洼洼的课桌上:“一个与死神面对面的藏族小女孩/听到了太阳敲响的叮当声/那是母亲和祖国一起在呼喊她啊/让藏族小女孩知道这是她又一个生日/她想吹自己的这个生日蛋糕上的小蜡烛/她说出自己的这个生日最想说的话/‘叔叔,我打扰你们了……”(叶延滨《献给玉树的女儿和儿子》)从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中,我们一方面看到“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历史形象。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苦难是表层的经验,创伤是一种心灵的内伤,而文学所要面对的应是一种被心灵所咀嚼和消化过的苦难,只有这样,作家对苦难书写才不会把苦难符号化、数字化,才能俯下身来体察一个人、一个人的具体创痛。”诗人们在创作中更多的承担的是祭司角色,他们祭奠的是受灾个体、群体,同时也是人类命运、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普遍危局,一切自然灾难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但人生的苦难是恒久的,不应将任何一场自然灾难孤立化,短暂的自然灾难只是常态而持久的人生苦难的一次急剧爆发,以“苦难”为最基本的底色人生,应时时刻刻保持“抗震救灾”忧患意识。从悲痛中升华,从苦难中追寻,真正地关注人生、思索人生,通过人们在自然灾难中所受的苦痛来审视生存状态,重新建构生命价值。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束语中写下了一段千古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人类要与自然界保持一种和平共处、自然和谐的关系,实现一个有序、祥和、自由的世界。在这方面,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因此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书写民族灾难和民族重生正是玉树地震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
参考文献:
[1]吉狄马加. 废墟上的花朵[ 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2]张帆. 大爱永存与灾难永志———论地震诗潮中传统诗词灾难书写的美刺精神[ 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6)
[3]李祖德. 苦难叙事、人民性与国族认同——对当前“地震诗歌”的一种价值描述[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4)
[4]岳逢春. 面向玉树肃立——兼论地震题材诗歌的创作理念[ J]. 都市生活,2010,(7)
[5]王玉红.中国自然灾难的审美之维 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0年5月
[6]杜岩.汶川地震叙事文学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
[7]王嘉悦.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2016年6月
作者简介:
祁生贵(1970—),男,藏族,青海海东人,青海警官職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