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小镇
王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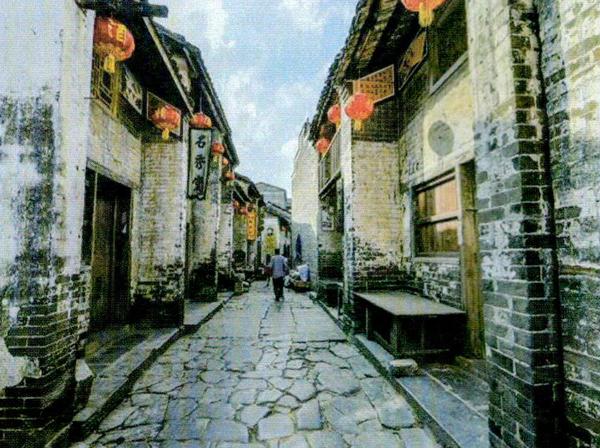
在小镇住久了,我便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每天放学后,吃毕饭,我就回了那个院子。我不是那种爱游逛爱串门的人,何况,我也不认识几个人。
回到院子。我坐在廊檐下,看着院子里的草一天天长高,似乎要翻过院墙,逃跑了一般。它们要是逃跑了,这里就真的只剩下我了。我坐在廊檐下,看着院子里的草一天天长高,像疯了一般,毫无节制地生长着,我常想,使劲长吧,长到把我淹没,我在荒草深处疯子一般游荡,像一只蚂蚱,唱着九月悲伤的歌。
没有人跟我说话。我需要一个人跟我说话。我把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翻遍了,除了我住的偏房,其余的门都锁着。西侧,是厨房,锁着。正屋,锁着。东面的土屋,人走房空,锁着。就连房后装麦草的柴房也锁着。我跟每一把锁说话,说关于钥匙的事。我跟院子的那棵榆叶梅说话,说春天的事。我跟一晃而过的野猫说话,说狸猫换太子的事。我甚至跟墙上挂着的一根绳子说话,说秋天麻子成熟了,打下来,炒着吃,麻丝剥下来,拧绳子,做新鞋,过大年。最后,我跟我自己说,为了混淆,我用右手跟左手说。
我又回到廊檐下,坐着,枯寂地坐着,把自己也坐成了一株草。看着虚弱的光线在日渐倾颓的土屋上被黑夜一根根抽去,看着满院的青草披上黑斗篷和夜色簇拥在一起,看着我的眼眶里装满黑色的液体。
进屋子吧,七月的夜晚依旧是冰凉的。进屋子,也是我一个人。房子里一台老旧的电视,炕头一组过时的板箱,除此,再没有别的物件了。电视连着屋外锈迹斑斑的铁锅,起初,还有信号,后来就坏了,无论我怎么捣鼓,都无济于事。我放弃了看电视的欲望。板箱一侧,放着我的书,我胡乱翻着,没有一个字是入眼的。
黑夜完全盖住小镇时,大地上所有的声响都销声匿迹了。我在昏黄的十五瓦灯下,影子那么长,那么黑,我真想拉起他,叫一声兄弟,咱们今晚喝两杯,就最便宜的一星金辉,卜二块钱,几盅子下肚,天昏地暗,天大的孤独都会成为半夜翻身而起的呕吐物。可当我伸出手,我只抓住了一把地上的灰。
此刻,世界远去,人类把我遗忘了。
有一天,当我回到院子时,大门掩着。我那表姐的邻居蹲在院里,认认真真,一株不落地把所有的草拔掉了。看着光秃秃的院子,好像有人剃尽了我的头发,头皮凉飕飕的。我坐在廊檐下,听着许巍的歌,一遍一遍,都听得熟烂于心了,但还是听着,除此之外,我还能听到别的声音吗?一切都是那么辽远,装在别人的屋里,就连山鸟的吼叫也是远处山林的,跟我无关。我的院子再也没有草了,有人在我心上拔去了羽毛,我掉落进连根带起的泥土里。蚯蚓咀嚼着七月的尾巴,蚂蚁搬走童年的家,唯独我不知该向何处。
没有野草,我一无所有。
没有野草,山鸟不再来,夜猫也消失了。有时候,摸着夜色,像摸着一段木制扶手,我便出去走走。我不是那个梦游的人,莫怕。我就是走走而已。有一个晚上,我来到离中学不远的地方,那里的路边正放映着露天电影。电影独自演着,黑白的老片子,落满了米粒大的斑点。没有人看,空空的荧幕下方,除了飞舞的蚊虫,就没有什么了。放电影的人坐在一侧的铁皮箱上,昏昏欲睡,月光落在他的右肩上,他穿着蓝色的衣裳。我在脚底下摸了一片砖,摆在路边,坐下。月光也落在我的右肩上,我穿着蓝色的衣裳。我一个人看完了一场电影,我不知道演了什么,反正结局依旧那么悲伤,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都消失了,只有那个跟剧情毫不相关的人还活着,像个傻瓜一样,朝我扮了一个鬼脸,吐着舌头,眯着眼睛。然后电影就结束了。我看着那个放电影的人收拾完所有的家当。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手,没有抽。抽烟的人是孤独的。
另一个晚上,我来到了小镇的另一块打麦场上。几个外地人在耍把戏,炽白的灯光把整个打麦场照得阴森森的。人们头顶着白光,像顶着一头雪,围成圈,在看那些外地人的把戏。他们把我挤在人圈外,他们高大的后背一堵墙一样用黑沉沉的影子压住我,我挤不进去,也看不到里面。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惊叫和赞叹。我只能窝在影子下,一個人待着。最后,把戏耍完了,外地人开始推销他们的药品。所有围观的人一哄而散,就好像他们不曾来看过一样,打麦场上空荡荡的,除了我,再没有观众。外地人为我表演了一个节目,一个小姑娘在脖子上放了一根筷子,一个男人用大铡刀劈了下去。我以为那个小姑娘会死掉,但没有,只是筷子断了。但我明显看到那个挨刀的小姑娘眼角挂满了泪水。她是一个像我一样悲伤的人吗?我鼓了鼓掌,为所有热爱流泪的人鼓掌。那个小姑娘送了我一瓶他们的药。有人关了灯,夜是那么黑,都快把人类淹没了。
后来,有人来小镇看我。四拨。第一拨是我的姐姐,那个从老旧画里走出来的人,那么稀薄,泛着淡黄的韵,只是寥寥几笔的体态,让七月的中午都在飘动。我们在没有野草的院子里坐了坐,说了说话。然后她就走了,她又回到了她的画里。然后是我的丽个同学,我们在戏场里喝了一顿酒,东倒西歪地回到院子。我们并排躺在炕上,说起我们犯病的师范光阴,说起毕业后可怜的生活,说起无处安置的未来,说着说着,我们都睡着了。再然后,是我的朋友。我带他到小镇的山上走了走,他摘了一把野草莓,红得像心脏的野草莓,在他的手上跳动着,他带着它们,坐上班车走了。最后来的,是一个姑娘,她来了,又走了。没有带来什么,没有带走什么。我说,你还能不能来看我?她咧着嘴笑了。夕阳站在树梢,纵身一跃,就消失在了山背后。
那个姑娘趁着夜色走了,我守着空旷的马路,像我送走别人后一样,守着空旷的马路。我把一条马路扛回屋,抖一抖,看有没有来看我而未回的人。没有。他们来了,又走了。没有人留下来陪我说更多的话。他们似乎不曾来过,只是我假设他们来过一般。
我还是我自己,我坐在廊檐下。孤独像一只茧,将我裹起来,挂在房角的房檐上。风吹来,我摇啊摇,风吹来,我摆啊摆。直到有一天,风把我吹干了,我唱的歌谣四散了,我就不再孤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