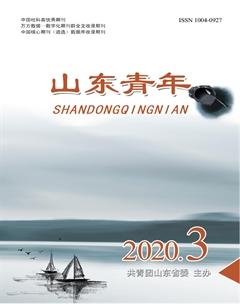违约金酌减规则研究
曹爱菊 于辉
摘 要:违约金酌减规则主要围绕“是否酌减”以及“酌减多少”展开,由于司法裁判中对违约金过高案件大概率的酌减,破坏了违约金酌减的基本理念。在对违约金是否酌减的认定层面上和酌减多少的环节中,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裁判规则模糊。为解决上述问题,司法机关需要明确“以不酌减为原则、以酌减为例外”的理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具体把握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和预期利益等综合衡量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作出裁决。
关键词:违约金性质;司法酌减;损失;综合衡量因素
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确立了违约金酌减规则,当事人对于约定的违约金可以诉请人民法院进行酌减。《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又进一步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对违约金的调整要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综合因素作出裁决,过分高于的标准以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超过实际损失的30%为限。尽管法律法规已经看似具体明确,然而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在审理违约金酌减案件时,仍会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将围绕违约金酌减原则、违约金性质、损失关系以及综合衡量因素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通过设立统一的裁判尺度,化解违约金酌减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矛盾。
一、违约金司法酌减的理论基础
(一)违约金的性质
法官在处理约定违约金司法酌减案件时,首先应当准确把握违约金的性质,然后在此基础上理解约定违约金酌减的正当性。赔偿性违约金,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先估算在交易后出现违约行为时造成的损害赔偿总额。惩罚性违约金,是指为了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若发生违约行为,则由违约方向非违约方支付一笔额外的金钱。纵观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明确指出究竟何为补偿性违约金,何为惩罚性违约金。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出“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即我国立法者认可违约金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
(二)正当性基础
1.公平原则
违约金条款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司法本不该介入。但在实践中,为了促使债务人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往往会预先约定高额的违约金作为合同履行担保。在发生违约行为后,如若要求债务人承担过高的违约金责任,债权人会因此获得不正当利益,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就需要司法的介入。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意在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达到均衡状态。
2.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在违约金司法酌减案件中发挥两个作用:其一,规范作用,即能够指导当事人正确进行民事活动。当事人应当遵守交易道德,不得采取欺诈、胁迫方式订立显失公平的违约金条款;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得恶意违约。其二,补充作用,即能够弥补法律的不足。当遇到立法不明确的情况或者尚未预见的新问题时,法官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并依照诚信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是否酌减环节存在的问题
(一)酌减原则存在问题
在司法实务中,债务人请求酌减违约金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比例高达七成,被驳回的比例不到三成。违约金条款本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这是“以不酌减为原则,以酌减为例外”的体现。相反,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如下问题:人民法院主动对违约金进行调整,打破了“以不酌减为原则”的违约金调整方式,不利于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
(二)对于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认定存在问题
1.对违约金性质的把握存在争议
由于法律中并未对两类性质的违约金进行区分,从而导致理论界对于违约金酌减规则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针对惩罚性违约金的法律地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114条第1、2款属于赔偿性违约金,第3款属于惩罚性违约金。另有学者认为第3款仍属于赔偿性违约金,其是针对迟延损害的赔偿额预定。另一方面,针对两类违约金是否统一适用“过高”标准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两类违约金的调整方法应当是一致的,通过对比违约金数额与实际损失数额,适用“30%”的衡量标准。笔者不赞同此种做法,如此“一刀切”的做法忽视合同自由原则,无法发挥惩罚性违约金的功能。
2.“实际损失”与“造成的损失”关系不明确
《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规定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而《合同法》第114条着眼于“造成的损失”,应当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合同法》第113条规定了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预期利益,此时又该如何解读“实际损失”、“造成的损失”与“预期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酌减多少环节存在的问题
1.合同履行情況
合同双方对合同的履行程度会影响司法机关对违约金酌减的程度,在比较法上,存在独立酌减模式,即独立于违约金过高酌减规则的部分履行酌减规则,以法国法最为典型。我国未对部分履行与违约金约定过高做区别对待,适用的是一体规制模式。由此需考虑我国司法机关在对违约金进行酌减时,是否有必要把独立酌减模式纳入考量范围。
2.当事人过错程度
根据《合同法》规定,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违约金责任之成立一般遵循严格责任原则,不问债务人的可归责性。据此表明当事人的过错跟承担违约责任无关,但为何《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规定当事人过错作为判定违约金司法酌减的考量因素之一?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才能使违约金调整的数额与当事人过错程度正确衔接?
3.预期利益
《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规定在对违约金酌减时,要兼顾预期利益进行综合衡量。此条仅是模糊规定要兼顾预期利益,实务中如何将预期利益作为参考因素进行酌减,并没有条文具体规定。
四、完善违约金酌减规则之建议
(一)明确“以不酌减为原则、以酌减为例外”
违约金司法酌减时,首先要明确“以不酌减为原则、以酌减为例外”的思想。究其原因,其一,从合同自由原则出发,在私法领域内,法不禁止皆可为。违约金条款是合同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司法机关不应过度干涉。其二,从违约金的功能出发,违约金兼具赔偿功能和压力功能。一方面约定违约金能够在发生纠纷时直接填补债权人的损失,如果法官无限制的酌减违约金,则有损违约金的赔偿功能;另一方面,对于交易双方,通常会约定一个较高的违约金数额来担保合同之履行,而发生违约行为后,债务人一般会主张违约金过高请求司法机关予以酌减,此时的违约金便无法发挥压力功能。
(二)明确规定违约金的性质并区分对待不同性质的违约金
1.明确规定惩罚性违约金的法律地位
违约金作为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其具有补偿、担保、惩罚之作用。一方面,承认惩罚性违约金彰显合同自由和公平原则。虽然在缔结合同时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可能不平等,但违约金条款却是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结果。另一方面,若利用违约金条款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则会导致另一种不公平,所以要通过法律形式对惩罚性违约金作出明确限制。
2.区分对待不同性质的违约金
赔偿性违约金,是对损失赔偿额的预定,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一般不会高于实际损失,所以对于适用《合同法》第114条“过分高于”和《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30%”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惩罚性违约金的设定本身就具有惩罚违约方的目的,因此,针对惩罚性违约金数额的酌减,笔者建议:其一,应当充分考虑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其二,应当参考合同标的额和合同未履行部分的总值,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其三,可以参考定金罚则,即惩罚性违约金的数额不宜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三)不特意区分“实际损失”与“造成的损失”
笔者认为,“实际损失”与“造成的损失”应作同一理解,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损失,不应特意区分这三者的含义,重点应放在如何确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数额上。原因在于,其一,法律明确规定在对违约金酌减时,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如果将其限制在信赖利益范围之内,会有损于违约金填补损害的功能。其二,《指导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调整过高违约金时,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由此可以看出“实际损失”与违约“造成的损失”是作同一理解的。其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预期利益明确纳入损失的范围,尊重违约金的约定,有利于解決预期利益估算困难的问题。
(四)综合衡量因素应当具体把握
1.合同履行情况
在债务人方面,若债务人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应视履行情况对其进行酌减。在债务人部分履行的场合,也应综合衡量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预期利益,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在债权人方面,当债务人已经构成违约时,若债权人仍按照合同条款和诚实信用原则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可以构成在司法酌减上获得优待的正当理由。
2.当事人的过错程度
在司法酌减中注重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可以减少在违约责任成立时严格责任原则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在债务人方面,债务人的过错程度越高,违约金酌减的程度越低甚至不予酌减。在债权人方面,若债权人故意创造条件诱使债务人违约,属于“不正当地促进条件成就”,应视为停止条件未成就,此时不成立违约金责任,也就不存在违约金酌减的问题。这就导致债权人完全丧失了违约金请求权,后果较为严重,应该仅仅限制在债权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极端情况。
3.预期利益
预期利益属于“造成的损失”的一部分,在衡量预期利益时,除了考虑损失之外,还应重视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本意。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意在使意思自治和公平正义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因此司法机关在对违约金进行酌减时,应该注重当事人通过约定违约金数额所表达的对合同顺利履行后所获利益的期待。《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了预期利益的法律地位,强调了当事人意思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姚明斌.违约金双重功能论[J].清华法学,2016(5):134-150.
[2]韩世远.违约金的理论问题——以合同法第114条为中心的解释论[J].法学研究,2003(4):15-30.]
[3]崔建远.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上册)[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25.
[4]王泽鉴.债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3.
[5]罗昆.我国违约金司法酌减的限制与排除[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2):115-126.
[6]雷继平.违约金司法调整的标准和相关因素[J].法律适用,2009.(11):24-28.
[7]姚明斌.违约金司法酌减的规范构成[J].法学,2014(1):130-141.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659.
[9]靳学军,李颖.违约金调整的司法难题及解决[J].人民司法,2008(19):48-54.
[10]王利明.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研究[J].中国法学,2017(2):25-47.
[11]姚明斌.违约金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314.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