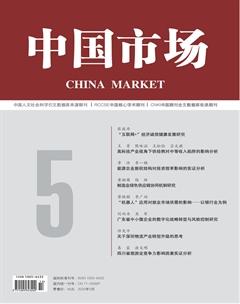企业技术合作创新的问题研究
冯轶伦 郭将
[摘 要]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实中,技术创新却一直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造两端摇摆,缺乏突破。文章认为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从长期来看也是缺乏持续性的。政府主导的创新平台的建设在当前阶段更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技术创新;合作;政府
[DOI]10.13939/j.cnki.zgsc.2020.14.165
1 引言
如何实现国家经济有质量的快速增长?这一命题一直都被各个国家和地区思考和实践着。斯密很早就提出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大量累积。但是,资本积累理论中边际收益递减的困扰却并没有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相反,一定量的资本投入却产生了,甚至超越了资本应该有的收益。面对这个多余的增长量,索洛提出技术是资本之后必须面对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技术可以有效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较大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成为技术追捧的重要原因。技术和资本就像经济增长的双翼。而评价和分析任何经济体的增长问题,都必须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投入足够的关注。技术,乃至于如何实现有效的技术创新自然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最常见如下的方式。
第一,技术引进。技术引进对于一个地区的技术提高是最快的。掠过了技术的研发和设计过程,直接通过技术购买等方式用于经济生产活动中,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引进的技术,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一个地区发展的实际。比如引进技术过高,可能无法和现实的技术水平形成有效的对接。由此雷迪曾经在他著名的“适用技术论”中提出,引进技术不应过度介意技术的先进性,关键是适用。但是在一个技术层出不穷的世界里,技术的支点效应不断被放大,很难接受引进一个不具备领先性的技术。
第二,技术自我创新。技术的自我创造首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术引进的问题。较强的适用性让自我创造的技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技术植根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而由此形成的技术创造能够恰到好处地满足地区的技术需求。但是,自我创新一项技术的先进性是与研发时间有着密切联系的。换言之,技术的先进性取决于什么时候研发出来。今天任何一个落后的技术相比一百年前都可能具有绝对的先进性。但是这些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很难起到得天独厚的支持。因此,如果某一技术不能尽快研发成功,就会延误发展时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的引进和自我创新有着各自先天的不足。学者们于是提出一边引进,一边学习和创造,亦即模仿创新。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各自问题的尖锐性,但是,面临的却常常演变了一场复制和抄袭的闹剧。那么,怎样的技术创新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并更符合今天中国的实际,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2 技术合作创新的困境
中国要以最短的时间达成最大的发展效果,实现伟大民族与国力复兴就必须追求效率。最简单的措施是模仿发达国家的一、二、三产业发展模式,这导致政府政策倾斜,催化企业发展。但是企业只注重经济增长,通过技术引进占据市场,却无法提供中国所需要的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中国制造企业不断降低利润来谋求市场,但是实际经济增长不如预期。这背后是大量资源在竞争中被挥霍浪费,难以谋求突破。
于是,技术先进性上的执著有了其基本的逻辑。因为技术的支点作用不断被各国创造的增长奇迹所论证。更先进的技术,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大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实现更为有效的技术创新呢?是不是企业一定要等到拥有足够的资本、技术基础和人才之后才能加入技术创新的序列中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能够找到一种万事俱备的状态来进行创新。客观事实更表现为某一企业在基础研发上颇具实力,但是市场洞察上略显迟钝。某一企业在资金上较为充足,却在研究人才上较为脆弱。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试图进行技术创新必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不是短期可以补足的。于是,双方资源的互补成为合作创新的依据,亦即资源的整合和拼凑。
但是,在资源互补合作创新的过程中,是不是会有效地形成创新合力呢?在忽略了相关管理问题之后,却发现企业合作创新中一种可怕的要素流动。表现为,两个企业合作过程中,技术强势一方因为其可能对技术研发具有相对重要的位置,往往会引发弱势一方的资本流向自身。当资本形成集聚后,可能带来的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上涨又会吸引技术弱势一方的人才开始向它流动。由此,技术和资本乃至于人才都会在技术强势一方形成有效的集聚。其結果会让其演变出更大的技术向心力。这种强大的向心力会向任何合作创新的企业形成一种虹吸效应,从而让自己越来越强大,造成了企业技术研发的不平衡发展。相比而言,技术弱势的一方,投入了资本、人才等要素参与,虽然可能对研发技术进行分享,但是,在技术经验积累上并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迹。
具体来说,技术强势一方,会逐渐演变为行业中技术领先者,并有条件兼并收购其他中小型企业,整合资源统一分配,以此降低这些中小型企业在独立研发竞争中的资源浪费。在有实力的大企业带领下,中小型企业研发资源被整合,资源汇集到一起,得到集中调配和管控,便于尝试更多的技术自主研发和创新。
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盲目地进行技术资源拼凑和整合,只会逐渐造成“真空窒息”现象。既得利益的不断扩大和中小型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萎缩。而同等规模的大企业为了保留自己的技术地位甚至抢占更多市场不被逐渐淘汰,必然纷纷效仿,大举进入技术合作开发的过程,但是,其结果往往是让合作的小企业实现了单次的某种收益,却丧失了后续长期的研发能力。
但是,一旦技术创新主体巨型企业统治了创新市场,就会制定价格和技术标准,甚至以大规模经济效益压榨中小企业和相关原材料提供商。中小型企业资源越来越匮乏,并在大型企业的夹缝间生存,曾经的优势会逐渐丧失。
3 困境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中国制造的品牌名声已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可,Made in China 成为了产品质量的保证和低成本的象征。但是中国制造过度依赖低廉价劳动力成本,消耗大量国有环境资源,片面追求粗放式高速经济增长,缺乏本国技术创新和自主特征。因此,尽管已经成功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现状的相对落后性和未来可预期的疲软性仍令人担忧。即使个别领域在世界层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大量核心技术仍然紧握在有限的发达国家手中,几乎可预期到未来科技想要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国际技术壁垒将会造成的影响。
具体来说,中国东西部地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一二线省会城市与三四五线小城市,资源依赖型城市,人口过度密集城市等发展极不均衡,第三产业比重差异巨大,呈现轻重不一的发展困境。国家和不少大企业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发展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窘态。
但是,现实中推进的合作性创新模式,随着资源拼凑在短期中造成的利好现象,资金雄厚的大型企业必然会继续兼并上下产业链的中小型企业,以期形成较为完整的企业自主产业链。如中间材料加工商向下并购原材料提供商、大型原料生产商向上兼并简易成品企业等。由此会造成巨型企业的臃肿状态,企业管理层需要兼顾企业各个层面的市场,维持日常流转的资金压力和所需要达到市场回报目标也日趋增加,对创新的关注会不可避免地下降。而过程中,有两个原因需要关注。
第一,人才积累不够。中国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已经创造了足够的资本。但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都是外贸出口型增长的模式,由此,积累和需要的是普通的劳动力。因为中国制造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高新技术人才。而中国所累积的相关人才也基本导向了制造技术的积累。这里有两点。其一,大量先进的技术,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而中国一直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其积累的都是制造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因为其技术的先进性,确立了技术标准,在这种技术标准下进行创新是很难的。其二,普通的劳动力,曾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曾经有效推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对于技术创新来看,影响了技术创新的进步。所以,人才确实已经成为了影响创新的根本原因。
第二,制度创新不够。制度对于人才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人才的缺乏最本质的原因是缺乏激励和培养人才的制度。具体来说,中国现阶段的高端人才储备以及相关人才发展自我的平台仍相当匮乏。人才的发展和利用缺乏相应规范的制度条件。
我国人才的缺乏来源于教育体制的尚不完全,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普及,但是高中生入读大学的概率仍然令人担忧。且中国大学的质量层次不齐,世界顶尖层次的学府极度稀少,仅有六所大学入选世界前一百名大学排名。
4 有效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招商引资等措施,积极与外国企业合作,经济得到迅速发展,GDP增速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但是这样迅速发展的背后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不均衡和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中国已成为被全球广泛认可的“世界工厂”,而这样的“世界工厂”是通过中国大规模的人口红利而达成的。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向世界证明了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且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工作效率也是世界工人中首屈一指的,由此得到了大量外国企业的青睐,他们斥巨资在中国建厂,加工产品,中国工人生产,组装一切,向世界的出口量年年递增,但中国却并没有可以向全世界输出的理念,本国企业难以自我创新创造。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制造的升级是乏力的。我国制造业依附性极强,长期依靠外国企业的加工订单,自身资本匮乏,有限的资本未能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且劳动技术水平低,技术单一。中国制造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缺乏技术的自我创造。大量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2012年之后开始没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成本上涨过快,而亚洲的其他地区如越南等还存在着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着外商[1]。
由此,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需求性和紧迫性显著上升。中国要寻找自主控制上游的产业发展途径,提倡拥有自主控制能力和长期发展动力,管控恶性经济效率追求,并提高中国软实力的发展。政府需成立各行各业市场相关情况监测与监督委员会,对企业的资源拼凑和市场份额占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禁止寡头巨型企业过度压榨中小型企业生存空间,给予新秀异军突起的可能和支持。
笔者认为,需要由政府主导成立一个关注各行各业自主创新进程的平台,独立于各大企业之外,将企业盈利与人才自主创新分离开。同时,制定一套关于创新人才评级的机制,以及由相关专业富有资质的专家教授和行业企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将人才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评级。而这项评级系统并不是依靠在某一段固定时间内对创新的数量取胜,而是完全看中创新的质量和其深远影响,以防止为了评级级别提高而取巧产出大量无效创新,同时拟评级名单将会在该平台上持续公示以得到2/3企业代表的认可,防止平台徇私舞弊,各方相互监督公开透明。此外,已获得相关评级的人才会根据自身的级别在不同的时间内予以相应的降级。如第一级别人才十年后降为第二等人才,第二级别人才五年后降为第三等人才,依此类推,持续激发人才创新原动力和与时俱进性。创新人员退休后则以本人所取得的最高人才级别对待,以彰显国家政府对创新型人才的鼓励与感谢。
同时,政府根据各个城市的不同特征和居民文化接受度,对全国进行规划,分配不同创新结果的试验地区,并给予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和专家指导。在试验成果有成效的前提下,创新人才及团队短暂的选择企业加入并指导改革工作和创新的应用以扩大效果提高效率。在创新成果广泛应用后,创新人才需返回创新平台编制。
资本方面,银行和各家企业需要在每年的利潤中抽离一定比例的资金,或由政府规定成立相关人才创新支持的基金会,根据上述平台的评级,对不同级别的人才所需进行的市场试验、科研需求等进行风险评估和更进一步符合章程的投资和规划。创新人才及团队可在企业代表认可的情况下进入企业进行一段时间的实际考察和观测,以了解现实市场,提高创新措施或机械的实际应用性。未被平台所认可的人员也可自行前往相关基金会进行申请。
技术创新之于企业、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起步较早,成规模的时间较早,因此也早已其他企业与外国接轨,生产外国订单,由此也得到了相关国家政策的福利支持。即使该企业是仅掌握末端生产技术,发展畸形化,其他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只能复制其发展模式,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催化发展。这类企业的资本与影响力在行业中逐渐雄厚和深远,原本追求自我发展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只能被这些大企业所压榨,最终越来越难以超越,重新主导中国企业发展模式与方向,两者的不平衡性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增加。
因此,盲目地推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会引发强势一方对于研发能力的快速提高,却无形中透析了弱势一方未来研发能力的上升空间。因此,笔者更认为政府应该及时地推出有力的创新平台,让全部的企业能够分享创新技术,有序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创新技术的热情,实现更快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AMITRAJEET A BATABYAL.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3(4).
[2]沈静芳.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市场,2017(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产业互联‘智造供需网的结构、演化及其动力学研究”(项目编号:71871144)。
[作者简介]冯轶伦(2000—),男,上海人,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