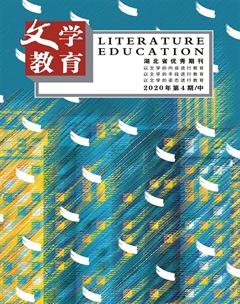《等待野蛮人》的后殖民分析
内容摘要:南非作家库切的长篇小说《等待野蛮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与野蛮人接壤的某边陲小镇行政长官所见所闻所感,形象地描绘了乔尔上校为代表的帝国殖民主义者的种种罪行,表现出作者对帝国殖民主义残酷、凶暴行径的愤慨与批判,也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中的库切对后殖民社会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库切 《等待野蛮人》 后殖民主义
一.库切及其《等待野蛮人》
南非作家库切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于1940年2月9日出生于南非开普敦市,其先祖是17世纪到南非的荷兰裔殖民者,母亲是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德国人,但库切以英语为母语。1961年他从开普敦大学毕业后离开来到伦敦,做过一段时间的计算机程序员。随后他前往得克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因为绿卡申请失败,库切只好返回南非,并于1972年成为开普敦大学的一名英国文学教授,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1974年,库切发表《黑暗地带》登上文坛,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作为一个荷兰裔南非作家,又有着长期在国外居住的经历,使得库切能够以一种“异乡人”的眼光来认识南非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种族隔离制度,在其后殖民主义的写作中,他反复揭露种族隔离制度下殘缺畸形的南非生活。如《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以一个被殖民者的视角表现了这一主题;《福》在对经典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颠覆中再次表现了这一主题;《耻》更是直接将小说的背景置于南非来表现这一主题。而库切最早表现这一主题的是1980年发表的《等待野蛮人》。
《等待野蛮人》是库切的第三部小说,曾经获得布莱克纪念奖、法伯奖和1980年的CNA文学奖。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某边陲小镇行政长官“我”的眼光展开叙事。我是毗邻土著居住地的边陲小镇的行政长官。虽然与野蛮人接壤,但是这里却是一个安宁和平的小镇,人们安居乐业,几乎看不到刑事案件,甚至连关押犯人的场所都没有。附近的土著偶尔会到镇上出售他们的猎物和购买生活必需品,与他们和睦相处。但是帝国军队第三处的乔尔上校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四处流传着野蛮人会来抢劫、攻击的谣言。为了证实这些谣言,以便帝国能够“及时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乔尔不遗余力地寻找蛛丝马迹,以种种暴力行为去坐实土著莫名的图谋不轨。他对来小镇看病的男孩及其年迈的舅舅严刑拷打,得到所谓野蛮人即将来犯的证据,悍然发动对无辜的野蛮人的战争,将小镇变成一座恐怖的监狱。乔尔带着胜利的光环离开,给小镇留下一群遍体鳞伤的囚犯和鲜血淋漓的尸骸。“我”释放了所有无辜的囚犯,并收留了一个在刑讯中双腿致残、两眼几乎失明的蛮族少女。充满同情与愧疚的我在少女伤好了后,将其送回到她的部落,返回小镇却成为“通敌叛国”的罪犯,被乔尔关进监狱,遭受非人的待遇。为了防范野蛮人,帝国军队烧毁河边的芦苇,也遭到野蛮人的疯狂报复,小镇的大片良田被毁,乔尔也带着部下仓皇撤退,留下威严扫地的“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小说虽然没有出现明确的时间与地点,但是评论者普遍认为作品是当代南非社会的隐喻,反映了南非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作者对后殖民社会深刻的理解。
二.《等待野蛮人》的后殖民分析
“后殖民”一词最初被历史学家用来描述殖民化后的时期,在文学批评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被用来讨论殖民主义的各种文化、政治和语言影响。作为一个术语,德里克认为,“后殖民”的第一重含义就是对前殖民地现状的描绘。库切在《等待野蛮人》这部小说中,通过无名小镇及周边土著的悲惨遭遇,形象地揭露了帝国殖民中的黑暗与暴虐。
殖民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往往会制造舆论,使自己对被殖民者的掠夺的行为合法化。如早期的哥伦布为了得到土著身上的黄金,将热情好客的土著妖魔化为凶残的食人族。英国学者博埃墨指出,“殖民主义按照所谓文明的需要对他者进行建构,以此来证明自己对被殖民者权力掠夺的合理性。”库切的《等待野蛮人》以形象化的文学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帝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散布出种种谣言,每一个被报道的袭击或强奸或抢劫案件,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是野蛮人所为,却都指向了野蛮人。甚至进一步传出野蛮人会来攻击、抢劫边陲小镇,荒唐的是这谣言来自于遥远的帝国首都,导致平静安宁的小镇居民人心惶惶,期盼帝国军队能够早日到边疆平乱。在作品中,帝国凭借者话语权的优势,以假想的敌人为借口,达到了其要征服、掠夺与消灭野蛮人的目的。乔尔上校一次又一次地带兵进入土著人的领地,大肆掠夺他们的财物。
虽然在这一地区几乎看不见野蛮人,但帝国的士兵却对居民甚至附近的渔民进行凌辱、拷打或镇压,视他们为野蛮人。为了证明他们对野蛮人的殖民统治,乔尔抓捕了12名俘虏(当地渔民),认为他们计划袭击帝国,在城镇广场上展示这些囚犯,用木炭在他们的背部写上“敌人”,以此来证明野蛮人的存在。但行政长官认为,木炭留下的记号在被刻上之后不久就被抹去了。这似乎证明了在帝国列强的历史上抹去他者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殖民统治时,除了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之外,往往会以暴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库切在《等待野蛮人》中,既写到了帝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意发动对野蛮人的战争,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利用酷刑来颠倒黑白达到自己的意图。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冷酷无情的乔尔上校审问了镇上的当地人,并给他们贴上了“野蛮人”的标签,他认为这些人对小镇和帝国的存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乔尔上校的刑讯方式和历史上的殖民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小说开头描述的是对到小镇寻医的甥舅(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和一个年迈的老人)的审讯。乔尔以库房抢劫案嫌犯的名义逮捕他们。“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对待。他们被绑着丢在储藏室,身上散发出“陈屎积尿”的气味,男孩脸上带着淤青,显然已经被拷打过。尽管我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一再向乔尔强调一个老人和病恹恹的孩子不可能是抢劫犯,但是乔尔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审讯才能确定。作者委婉地写了这次审讯的经过。乔尔以“我”会厌恶审讯的场面而拒绝了“我”参与审讯,但是从人们所听到的封闭的储藏室传出的叫喊声可以想象审讯场面的惨烈。而我再次见到两个囚犯的惨状也印证了这一点。男孩紧闭双眼,满身伤痕,老人更是惨不忍睹,已经被缝进了裹尸布,“我”打开裹尸布,看到他“灰色胡须上粘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框成了一个血洞。”而审讯记录却漏洞百出地记载着犯人攻击审讯官,在扭打的过程中自己撞到墙上死去。
另一个落入帝国无情之手的受害者是一个所谓来自野蛮人的女孩,实际她是与当地土著的一员。与男孩的遭遇相似,她的父亲死于审问当中,她也被乔尔残酷地折磨和致残。在“我”遣散乔尔逮捕的她那些族人后,“我”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在审讯中双目几近失明、跛足的野蛮女孩孤苦无依地在大街上乞讨。在小说中,库切依然没有直接描绘酷刑的过程,只是通过女孩身上的伤残来诉说着刑讯的残暴。
帝国对“野蛮人”酷刑的使用,不仅仅给他们带来肉体上的伤害,给他们造成的精神戕害更深。当“我”试图了解刑讯的过程时,作为受害者的男孩和少女都选择了沉默,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去回忆那令人恐怖的场面。
作为镇上的行政长官,“我”与镇上的土著和平相处,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野蛮人”世界里。当乔尔向我了解野蛮人的情况时,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在这里是和平的,我们没有敌人”。小说中帝国所畏惧的野蛮人的存在是模糊的。尽管对看不见的野蛮人的攻击和侵犯的谣言总是在镇上流传,却没有人见过他们。关于镇上野蛮人的存在,行政长官说野蛮人是“那些过得太安逸的人想象出来的”。一般而言,作為帝国统治者、殖民者希望殖民地社会群体彼此分离,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群体的融合会威胁到他们的殖民统治。尽管“我”是帝国的一员,多年来一直掌管着这座城市,却并不对蛮族部落统一的想法感到不安,而且我将受害的野蛮人少女送回了他们的部落,我也成为受害者,被控“通敌叛国”罪,遭到帝国士兵的监禁和拷打,并视为野蛮人。当乔尔上校审问他时,地方法官指控乔尔上校才是真正的敌人。“上校……你才是敌人,是你发动了战争,一年前你在这里犯下你的第一个肮脏的野蛮行为”。很明显在库切的小说中,“文明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在小说结尾,行政长官总结说,帝国的入侵是为了证明它对当地人的权力,这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殖民过程,即抹去非西方民族的存在,否认他们历史的存在。由此,这个地方对于另一种文化的意义就消失了,住在那里的人就成了不存在的居民。在整部小说中,殖民和帝国主义对当地居民施加的折磨、压迫和暴力都清晰可见。
与南非其他小说家相比,尽管库切的小说不是那么直白,但《等待野蛮人》显然直接或间接地以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遭受的政治动荡为背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南非的一部分。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涉及到被压迫者/压迫者、侵犯者/被侵犯者、施虐者/被折磨者、自我/他人之间的普遍斗争。在等待野蛮人的过程中,这个不为镇上任何人所知的群体被视为帝国的威胁因素,从而呈现了被殖民者是西方霸权、种族主义和歧视所支配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库切.等待野蛮人[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2.萨义德等著.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库切的后殖民创作研究”(15YBB062)
(作者介绍:袁湘英,邵阳学院计财处副处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