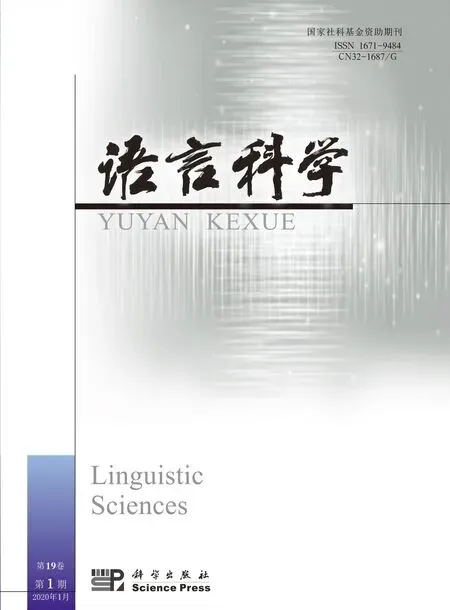量词的产生对指代词系统演化的影响*
汤敬安 石毓智
1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1 2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新加坡
提要 语法系统是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变化往往会影响到其他相关的部分,从而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演化模式。量词的产生深刻地改变了汉语名词短语的结构,并且使得原来的指代词系统不再适合新的结构规则而遭到淘汰,从而诱发了最普遍的两个量词“只”和“个”语法化为指代词,从而形成了当今南北方言的近指代词的两大分野。文章的研究对语言类型学具有直接的贡献,目前国际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指示代词是语言的基本范畴,不可能是从其他词汇语法化而来的,然而来自汉语史的强有力证据说明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汉语的指示代词是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从量词语法化而来的。
1 引言
语法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为:是不是所有的语法标记都必须是从具体词汇演化而来的?目前在国际语言学界的语言类型学和语法化这两大领域,关于指示代词的来源与发展就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指示代词属于语言的元语义范畴(primitive category),不可能是其他具体词汇语法化的结果(Plank 1979; Diessel 1999: 150)。然而Heine & Kuteva (2002: 159) 等则持另一种观点,指出在非洲的一种语言里,其相当于“go”行走义动词发展成了指示代词,Yue-Hashimoto(1995)也指出先秦汉语的“之”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可是因为这方面的例证太少,研究又不充分,所以并没有彻底解决指示代词是否也存在语法化的问题。
汉语拥有3000多年的不间断的文献记录历史,详细地记录了各个时期的演化过程,为探讨指代词的语法化问题提供了理想的语料证据。总体上看,汉语的指代词有两种词汇来源,一是来自于“去”或者“抵达”的动词,“之”“底”等属于这一类;二是来自于量词,北方方言的“这”和南方方言的“个”就属于这一类。本文只探讨第二类指示代词的演化情况。
指示代词是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式之一,属于语法中最稳定的成分。然而由于语法整体特性的改变,诱发一些更适合新语法体系的新指示代词产生,它们由少变多,由弱变强,最终取代了旧有的指代词。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唐宋以后新产生的指代词“这”“个”等对语言中业已存在上千年的“此”等的替代。
2 目前学界关于指示代词“这”(1)本文由于涉及到指示代词的字源问题,所以必要时使用繁简两种字体,如只~隻、这~這等。等词源的探讨
指示代词的更替是汉语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探讨。在语法化理论没有引进中国以前,人们尚缺乏语言的演化观,当探讨一个新语法形式如何产生时,就会去寻找它们在更早时期的对应形式。下面简单评介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
1)来自上古汉语的“者”。罗常培 (1933) 从历史方言资料上证明,“这”与“者”在读音上是相近的,推测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语源关系(蒋绍愚 2005:123)。吕叔湘(1985:184-185)明确指出,“这”源于上古汉语的“者”,“者”原为上声字,作指示代词的“者”和“这”在宋代已读去声。然而吕先生也承认,“这”字在《广韵》里读鱼变切,意为“迎也”,而当时近指代词的 “者” 为章也切,“遮” 为正摄切,语音上说不通(1985:244)。王力(1989:68)则指出,这种假设在功能上是难以成立的,“者”在先秦汉语只能作为被形容词、动词等修饰的中心语,如“贤者”“食者”,与唐时出现的新兴指代词功能完全不同。
2)来自于上古汉语的“之”。太田辰夫(1987:118)认为“这”的语源不明,只是推测可能是从上古汉语汉语的“之”发展而来的,因为那时有“之人”“之子”一类的用法,与新兴的指示代词功能相似。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一推断的可靠性不高,因为“之”早在魏晋时期已经逐渐消失了。王力(1989:69)则倾向于认为唐后兴起的近指代词就是“之”在口语里音变的结果,它在口语里与“者”读音相近,人们就选择用“者”表示,后来才改写为“这”。
然而,在我们看来,不仅从语音上看,“之”与当时的近指代词“这”不一样,语法功能上也说不通。“之”本来是个平声,而唐时的“这”则是一个入声字,语音上不对应。“这”在唐朝刚出现时,它和名词之间一般要有一个量词连接,即不能直接修饰名词,然而上古汉语的“之”只能直接修饰名词,它与名词中心语之间不能加任何语法标记。更重要的是,“之”在上古汉语的很多用法是新兴的指代词所没有的,诸如“德之不修”“穿窬之盗”等这种结构是新兴的指代词“这”所没有的。
3)来自指示代词“此”。“此”从先秦到唐代,一直都是个主要的指示代词。章太炎在《新方言》卷一推断唐朝开始流行的近指代词“者”“遮”等是“此”的当时的异体字。然而作为指示代词的“者”或者“遮”后来统一写为“这”, “这”与“此”虽然同时在使用,然而从语音上看,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吕叔湘 1985:185)。
4)来自中古时期其他词汇的合音形式。吕叔湘(1985:299)推测“只”“祗”可能跟“这”有关系,梅祖麟(1984)顺着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提出“这”的前身是“只者”,即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而成。冯春田(2000:91)则认为是“只么”的合音,也是同一思路。然而他们没有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原来只有语气词用法的“只”(2)“只”在上古汉语里是一个语气词,表示感叹,例如:“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诗经·柏舟》)它在中古时期又发展出了表示“仅仅”的副词用法,例如:“只想竹林眠。”(杜甫《示侄佐》)是如何获得指代功能的?
5)来自副词“適”(恰,正)。陈治文(1964)提出一个观点,认为“這”是“適”的草写,俞理明(1993:175-178)用更多例子证实了陈治文的观点。袁宾和何小宛(2009)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佛经中“適……时”的结构中“適”可能就是近指代词“這”的来源。然而,这一论述也存在明显的疑点,因为即使在指代词“这”产生的初期,其语法功能就明显有别于副词,比如它经常与量词搭配使用来指代事物(下文将详细讨论)。
蒋绍愚(2005:124)在评述各家关于指代词起源的各种假设后得出结论,目前学界的各种观点都有不完满的地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则认为,要对现代汉语指代词的起源做出成功的解释,必须从当时的语法系统来看问题,注意力只放在“这”一个词上是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与“这”产生的时间大致相当,汉语中还出现了另一个指代词“个”,其早期用例如(吕叔湘1985:243):
(1)个人讳底?(北齐书·徐子才)
(2)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
(3)观者满路旁,个是谁家子?(寒山11)
(4)若得个中意,纵横处处通。(寒山诗20)
(5)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嘉话录,广记)
(6)此景百年几度?个中下语千难。(东坡词)
指示代词“个”从魏晋产生之时起,一直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口语文献中。纵观当今南北方言的指代词系统,“这”多用于北方方言,“个”则多用于南方方言。根据曹志耘(2008: 10),在他们所调查到的783个方言点中,有465个方言点是用“这”作为近指代词,占63%;有273个方言点则是用“个”作为指示代词,占37%。不论从语音上还是从语法功能上看,指代词“个”都找不到它先秦的词源,所以探讨它的来源必须另辟蹊径,需要运用语法化的观念。如果把指代词“这”和“个”放在一起来考察,更容易发现问题的真相。
3 指示代词“这”来自其原来量词的用法
语法化总是首先发生在活的口语中。然而在口语中发生的变化往往不能及时而充分地反映在书面记录上,所以单纯依赖历史语料往往难以探讨一个语法化的详细变化过程。幸运的是,当今的方言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让我们可以重构历史上所发生的语法变化过程。
指代词“這”与量词“隻”同音也有历史证据。根据陈治文(1964)考证,“這”字系由“適”字的草体揩化而来的,都可读“之石切”,正与唐代新兴的指示代词同音,故“這”成为近指代词用字。在《广韵》中,与“適”同音的还有隻、炙、摭、拓等。由此可以推知,在隋唐时期“這”与“隻”是同音词。
张惠英(2001:172)根据很多方言的近指代词都与其量词“只(隻)”同音的现象,提出普通话的“这”就是来自中古量词“隻”的假设,这与其他方言的近指代词“个”来自于其量词用法的道理一样。她所引用的方言语音证据主要为:
1)闽语厦门话、福清话、顺昌话,都有跟“隻”同音读法。
2)保留入声的官话方言如山西长治、大同、江苏泰州等,近指代词“这”都读入声,都和“隻”同音。
3)失落入声的官话方言,如贵阳,“这”和“隻”同读支思韵阴平调。
在唐宋时期,近指代词有多种写法,如“這、者、只、遮、赭、则、拓”等。之所以有这么多异体字,原因由两个方面造成:一是指代用法与其原来的量词用法差别较大,一般人觉察不出其间的联系,就有一个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表示;二是各地方言发音不同,或者同一个方言有多种读法,因而选用不同的字体。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不同学者对当今方言指代词“个”的记录上,很多方言调查者没有意识到量词与其指代词之间的关系,就用“格、该、姑、葛、搿”等来记录。可是,“這”在当时就是占绝对优势的写法,后来逐渐淘汰了其他字形,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成为后来唯一规范的写法。“這”在竞争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与它在当时与量词“隻”的发音完全相同不无关系。
张惠英(2001:174)也指出,虽然在普通话里量词“隻”与“這”的元音不同,这是语音在不同地域发展不平行的结果。在很多方言里,它们的元音都是央元音[]。例如:
1)山西长治方言(侯精一 1985:56):“这”读阴入调ts54,和“隻”同音。太原方言情况相同。
2)江苏泰州(俞扬 1991:262)“这”读阴入调ts33,跟“只”“隻”、“则”同音。
3)山西文水话“这”(胡双宝1988:48)读阳入调ts213。
4)山西平遥话“这”(侯精一 1989:179)读不卷舌声母的阴入调ts13,跟“则”同音。
5)山西大同话(马文忠 1986:46)“这”读入声tʂ32,音同“只”“隻”等。
至于为什么“这”在普通话中读去声,“只”读阴平,这也符合入声向其他三个声调演化的规律。原来的入声在普通中消失后,归入平、上、去三个调类。因为“只”和“这”的功能不同,写法又不一样,它们的韵母和声调就产生了分化。
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只有“只”和“个”这两个两个量词发展成为指示代词,而且它们的指代词用法分别使用于不同的方言?原因有两个:一是它们是所有量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而且在不同的地域里,它们的使用频率又有所不同。“人”是所有名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以与这个名词的搭配为例,有的方言选择“个”,而有些方言则选择“只”。根据曹志耘(2008:194),有81个方言点是用“只”来搭配“人”的,虽然远不及“个”的781个此用法多,但也足以说明“只”在不少方言里是最普遍的量词。现在已无法确切知道“只”在唐朝时期各个地域的具体使用情况,但是根据历史语料来看,它在当时使用的地域应该是很广的。
4 从量词到指示代词的发展机制
如上所述,张惠英(2001:172-192;2014)从当今方言语音上证明了量词“只”和“个”在不同的地域演化成了指示代词,她又同时指出数词“一”也在一些方言发展成了指代词。其实这三种发展都与数量“一”的表达有关,因为只有数词为“一”时,量词前的数词才可以省略,而量词“只”和“个”都是在数词为“一”并且出现于谓语之前的情况下才发展成指代词的。然而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数字“一”在其他语言里倾向于发展成不定冠词的标记,英语的不定冠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不见发展成有定性的指代词现象(Heine & Kuteva 2002:220)。汉语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发展,是与魏晋时期汉语形成的结构赋义规律分不开的。根据石毓智(2002),汉语中存在一个“结构赋义规律”: 谓语动词之前的光杆名词(通常为主语)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性语义特征,之后的成分(通常为宾语)则自动被赋予一个无定性特征。例如:
(7)a.人来了。 来人了。
b.书我看了。 我看了书。
上述两组的左边例子中“人”和“书”所指都是交际双方共知的,因此是表示有定的;然而右边对应的宾语名词则可以指任何个体,是无定的。这是一条严格的语法规律,强制作用于普通的光杆名词。
上述规律普遍作用于汉语的各方言。在普通话里,当数词为“一”时,“量+名”短语可以在宾语的位置上出现,表示“无定”。量词本身在有定、无定的表达上是中性的,这里的“无定”含义是来自于结构赋义,即在宾语的位置上被自动赋予这个语义特征。如上例所示,普通话(北方方言)一般不允许“量+名”短语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因此它无法获得“有定”的语义特征。然而在广大南方方言中,当表示单一的个体时,“量+名”短语可以自由地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受结构赋义规律的作用,表示有定的事物,功能相当于加上一个指示代词。
大量的方言研究报告指出,量词具有表示定指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指示代词。杨剑桥(1988)根据对从不同方言得来的大量有关资料的观察,指出其实量词自身并没有指示作用,这里的指示作用是由名词的主语地位决定的。其根据是,在吴语和粤语中“量+名”表定指的用法基本是在主语的位置,在宾语的位置相当少见。也就是说,这是汉语的结构赋义规律作用的结果,“量+名”短语自身只表示单一个体,有定性主要来自句法位置,两者合起来才具有定指的功能。
“量+名”短语在以下方言中的定指用法,只限于谓语动词之前的位置,主要包括主语、话题和处置式中的受事。例如:
(8)只录音机啥人拿去勒。(那台录音机谁拿走了。)上海话
(9)支笔不好写。(这支笔不好写。)温州话
(10)本书奠你读。(这本书给你读。)永康话
(11)张画雅绝。(这张画漂亮极了。)闽方言
(12)个人肥肥。(这个人很胖。)汕头话
(13)张纸克来。(那张纸拿来。)潮州话
更有启发性的是贵州遵义方言(胡光斌1989),该方言的“名+量”可以表示定指,但是只限于谓语动词之前,比如“鞋双烂了”意为“这双鞋烂了”,然而在谓语动词之后表定指时则必须加上含“有定”义的修饰语,比如“这是你的钢笔支,还你”。
我们认为在广大南方方言中“量+名”表定指的现象,是由其所出现的句法位置所赋予的,而不是自身所固有的。这一论断可以得到以下跨方言的证据的支持。
1)不允许“量+名”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特别是主语位置)的方言,它们就没有表定指的用法。比如广大的北方方言就属于这种情况。
2)在有“量+名”表定指用法的方言中,定指用法限于或者主要出现于主语的位置,在宾语的位置上不用或者有定、无定两可。但是没有相反的情况。上面所看到的南方方言都属于此类。
虽然量词的定指用法本来是结构赋义现象,而不是其词义本身所固有的。这种用法的长期和高频率使用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表“有定”的意义最后永久固定在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个量词上,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个”在很多方言中的指代用法,它已经相当于一个指代词,不再受句法位置的限制。二是很多量词都同时获得表有定的意义,它们的定指用法可以逐渐出现于宾语的位置。
然而,在先秦时期,并不存在上述的结构赋义规律。以“人”为例,当它不加任何修饰语而出现于句首时,仍然是表示不定指的。下述例句句首位置的“人”到了现代汉语就必须加上限定成分,比如“别人”“有人”“一个人”等。
(14)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15)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16)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结构赋义规律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下例中的“人尽不知”中的“人”表示有定,指“参加受法的人”。该规律形成的另一证据是,如果表示不定指,则一般要加上不定指标记“有”字。例如:
(17)其夜受法,人盡不知。(六祖坛经)
(18)有人告报:路府留后押街画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19)有人问真觉大师:“丹霞烧木佛,上座有何过?”(祖堂集·丹霞和尚)
下例中的“只(隻)”被一些学者解读为近指代词“这”(梅祖麟1986;张惠英2001:174),其实这很可能是量词“只”在主谓位置临时被结构赋予的定制现象,即结构赋义的具体用例。
(20)金殿乍开皆失色,只言知了尽悲伤。(敦煌变文·欢喜国王缘)
吕叔湘(1985:243)所列出的3例魏晋时期“个”作指代词的例子,全部都是在主语的位置,可以看做这是指代词“个”早期结构赋义用例,而不是典型的指代词用例。
(21)真成个镜特相宜。(庾子山集27)
(22)个人讳底?(北齐书·徐子才)
(23)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
5 指示代词与数词语法功能的一致性
从语法功能上看,量词与数词、指示代词之间的语法关系最密切。数词和名词中心语之间必须加量词,而且“数 + 量”短语可以脱离中心语而直接替代整个名词短语,比如“两本书”也可以说成“两本”。同样,指示代词作名词定语时通常也要有量词连接,而且也可以省略名词中心语。例如:
(24)我看了三本书。 我看了三本。*我看了三书。
我看了这本书。 我看了这本。*我看了这书。
虽然在普通话里或者部分方言里,指示代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这人去哪了”“这书很有意思”等,然而在不少方言里,指示代词则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其间必须有量词连接。根据黄伯荣(1996:467),在兰州话、上海话、成都话、闽南话、海口话、潮州话、汕头话等方言里,指示代词和名词中心语之间都必须由量词连接。比如在成都话里,只能说“这支笔”而不能说“这笔”,只能说“这个小学生”而不能说“这小学生”(张一舟等 2001:221)。这说明这些方言中指示代词的句法行为与数词一致,都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必须用量词连接。
汉语历史上出现过多个指示代词,它们的具体语法功能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其概念义是一致的。当它们修饰名词时,既表示定指,又指示一个数目字“一”。也就是说,“指示代词+名”短语中的名词都是单数。例如:
(25)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诗经·燕燕)
(26)斯人长而好学。(三国志·吕蒙传)
(27)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8)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三国志·姜维传)
如果要表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数目,则需要在其间加上具体的数目字。例如:
(29)之二虫又何知?(庄子·逍遥游)
(30)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抱朴子·仙藥)
(31)斯二者,天也。(孟子·离娄上)
(32)此三物皆可各單行。(抱朴子·登涉)
根据我们的考察,在现代汉语中,“这/那 + 名”一般只表示单数,如果要表示复数,要么用“这些/那些”,要么加上具体的数量词(石毓智 2004: 200-201)。例如:
(33)你看余得利,那勺子都快吃下去了。(冯小刚·编辑部的故事)
(34)可是我刚才确实在望远镜里看到那星星了。(同上)
(35)那姑娘心不坏。(同上)
(36)那人为她闪开道,回头看了她一眼。(同上)
既然指示代词的语义特征和语法性质跟数词密切相关,而数词单独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与量词搭配使用,那就不难理解两次的出现对已有指示代词系统的冲击。
6 量词的产生对指代词系统的影响
如前所述,指代词是最常见的语言现象之一,使用频率极高,不大容易消失。先秦汉语常见的近指代词有“是”“斯”“兹”“此”等,到了唐代只剩下“此”一个。其中的“是”在秦汉之际语法化为判断词,从而蜕化掉了其原来的指代用法(石毓智 2016:21-37)。“斯”和“兹”可能是方言变体,使用范围一直不广。隋唐时期最盛行的近指代词主要就是“此”这一个指代词了。
纵观汉语发展史,新出现的语法标记往往都是使用频率低,出现范围有限,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战胜业已存在的强大竞争者,其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就是语法系统的整体变化。新产生的语法标记与新的语法系统和谐一致,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最后取代了旧有的语法标记。相反,旧有的语法标记虽然实力强大,但是保守的旧用法与新的语法体系相抵触,其使用范围不断被消弱,最终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唐朝出现的指示代词“这”虽然在使用频率上远不及“此”,但是在与量词的搭配使用上则远高于“此”。这就是为什么“这”能够后来者居上的原因。我们下面选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3)刘坚和蒋绍愚主编,1990年,商务印书馆。作为统计范围,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有三个:一是该书将近24万字,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二是该书的文体全面,更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口语状况;三是近指代词“這”在那个时期有多种写法,该书做了文字规范整理,可以减少因为异体字而导致的统计不准确。
表1指代词“此”与“这”在唐五代的功能差异

总用例独用指代+名指代+量+名“指代+量”独用指代+数+量+名指代+里 此100943055916400 这1885305349149
从上述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唐五代时期。占绝对优势的近指代词仍然是“此”,共1009例。而新出现的“这”则只有188例,只有“此”使用频率的19%。
2)然而在与数量词的搭配能力上,新兴的指代词“这”共有103例与量词一起使用,33例则不带量词,前者是后者的三倍以上。
3)在新兴的地点指代词表达上,“这里”共有49例,“此”则没有这种用法。
“此”是先秦汉语的主要指代词之一,在量词没有产生之前,它修饰名词的格式只能是“此+名”。因为它是一个高频率的词汇,旧有的语法格式拥有强大的保守力量,所以即使在量词高度发达的唐代,当其作名词修饰定语时,与量词搭配的用法在整个文献里仅有20例,只有全部用例的2%,而且其与量词省去中心语单独使用只有4例,其中2例还是出自同一文献的同一表达的重复。例如:
(37)此个老人前后听法来一年,尚自不会《涅盘经》中之义理。(庐山远公话)
(38)此个厮儿,要多小来钱卖?(同上)
(39)若闻冥建刑要处,无过此个大将军。(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40)见狱主驱无量罪人入此地狱。目连问曰:“此个名何地狱?”(同上)
(41)见一马头罗刹,手把铁杈,意气而立。目连问曰:“此个名何地狱?”(同上)
上述最后两例的“此个”独用,都是出自同一个文献。可见,“此”的这一用法极其罕见。
事实上,“此”与量词的搭配能力比文献反映出来的现象还要弱。吕叔湘(1985:184-185)指出,在唐五代文献里,“此个”实际上是口语里“这个”在书面语里的“沿袭”写法,因为“此个”与“这个”在同一文献里同时出现。例如:
(42)这个修行是道场。(维摩诘)
(43)此个名为真道场。(同上)
(44)这个老人来也不曾通名。(庐山远公话)
(45)此个老人前后听法来一年。(庐山远公话)
唐五代时期的指示代词“这”与数词的语法功能平行一致。在这个时期,量词系统并没有完全建立,虽然“数+量+名”格式逐渐取得优势,然而仍然可见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现象,而且“数+量”还可以出现在名词中心语之后(石毓智和李讷 2001:282-304)。
(46)其中七十早希,三人同受百岁,能得几时?(庐山远公话)
(47)玉貌细看花一朵,蝉鬓窈窕似神仙。(丑女缘起)
所以,唐五代时期的“这”作定语修饰名词时,64%的用例加量词,36%的用例不加量词。
1)“这+名”构式。如上所述,在当今的很多方言里,指代词和名词之间必须有量词连接,否则就不合语法。然而这种严格的规律始终没有在北方共同语里形成,自“这”产生起至今都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只是这种用法越来越受限,多用于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指代。例如:
(48)以此思量这丈夫,何必将心生爱恋?(敦煌变文·佛说观弥勒菩萨)
(49)只为这婴孩相系绊,致令日夜费心神。(敦煌变文·父母恩重)
(50)这小儿子,养来到十六,并不曾见他语话。(祖堂集·慧忠国师)
(51)这汉,我向你道不相到,谁向汝道断?(同上)
(52)这阿师他后子孙,噤却天下人口去。(祖堂集·石头和尚)
(53)若能晓了骊珠后,只这骊珠在我身。(祖堂集·丹霞和尚)
(54)这多口新戒,出去!(祖堂集·长髭和尚)
(55)这老和尚有什么事急?(祖堂集·洞山和尚)
2)“这+量+名”构式。此类用法为“这”所有用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占全部用法的28%,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新兴的近指代词就是为了适应量词系统的建立而带来的新的语法规则。而“此”到了唐代已经在汉语中使用了1000多年,它在量词没有产生之前,只能直接修饰名词,然而在量词建立后,由于其原来用法的类推力量带来强大的惯性,所以适应新语法体系的能量非常有限,这种用法只占其总用法的1.6%。这就是为什么“此”逐渐被“这”替代的原因。例如:
(56)不要称怨道苦,早晚得这个新妇?(敦煌变文·丑女缘起)
(57)犹有这个纹彩在。(祖堂集·道信和尚)
(58)那得有这个言词障于某甲善心?(祖堂集·慧忠国师)
(59)即这个不污染底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祖堂集·怀让和尚)
(60)这个行者,何不教伊?大无礼生!(祖堂集·丹霞和尚)
(61)贫道这里无这个闲家具。(祖堂集·药山和尚)
(62)汝与我斫却,这个树碍我路。(祖堂集·长髭和尚)
(63)这个功课从无人边得,不由聪明强记。(祖堂集·云嵒和尚)
(64)此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摩生?(祖堂集·洞山和尚)
(65)这一片田地,好个卓庵。(祖堂集·南泉和尚)
3)“这+量”构式。量词拥有双重的语法功能,既具有称数性,也具有指代性,比如“三个”可以指“三个人”等。新兴代词的这一用法使用频率也非常高,共49例,占总用例的26%。然而“此”的这一用法受到极大的限制,在共1009例中只有4例是这种格式,只占0.4%。例如:
(66)彼中还有这个也无?(祖堂集·石头和尚)
(67)师乃指一柴橛曰:“马师何似这个?”(祖堂集·石头和尚)
(68)道吾曰:“用沙弥童行作什摩?”师曰:“为有这个。”(祖堂集·药山和尚)
(69)这个是某甲兄,欲投师出家,还得也无?(同上)
(70)师拈起绵卷子曰:“争奈这个何?”(同上)
(71)师曰:“这个犹是儿子。”(祖堂集·云嵒和尚)
(72)有也,过于这个无用处。(同上)
4)“这里”用例。指称方位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用法,“这”可以加上“里”来指称地点,而“此”则没有这一用法。例如:
(73)若是佛法,我这里亦有小许。(祖堂集·鸟窠和尚)
(74)如何是这里佛法?(同上)
(75)我这里有刀子。(祖堂集·长髭和尚)
5)“这”单独使用例子。在能否独用上,“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唐五代时期的“此”仍然秉承着上古汉语沿袭下来的用法,可以自由地独用,共430例,占其总用法的43%。然而“这”的独用受到很大限制,共5例,只占其总用法的不足3%。例如:
(76)世人悟道非从耳,耳患虽加这亦分。(祖堂集·长庆和尚)
(77)某甲东道西这也得,只是于人无利益。(祖堂集·福先招庆和尚)
(78)第七遍捏作此,更不裂损,每事易为,所要者智应矣。(入唐求法巡礼记)
(79)窃惟未必然矣,此乃众生果报所感矣。(同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量”短语也可以用来称数动作行为。随着名量词的产生,动词也出现了平行变化,也出现了动量词。“这”可以加上动量词指代动作行为,也可以加量词修饰动词。例如:
(80)这遍若不取我指扬,不免相公边请杖,决了趁出寺门,不得闻经。
(81)进曰:“为什摩不道?”师云:“你也虚有这个问!”
先秦汉语中出现的“斯”、“兹”等到了唐代早已不用,只保留在少数书面语中,所以在我们统计的范围里,不见一例它们与量词搭配的情况。由于量词的产生,“数+量+名”产生了强大的类推力量,不仅促使了结构助词“的(底)”的语法化(石毓智和李讷 1997),而且也导致了指代词系统的嬗变。根据我们的考察,量词系统的最后建立大约是在元明之际,“此”应该是在这个时期在口语里完全被“这”替代。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水浒传》中,“此个”则不见一例,这是“此”在口语里消失的重要迹象之一。
7 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今南北方言的两个近指代词“这”和“个”分别是量词语法化的结果。其他学者已经从语音上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发展关系,我们又从当今方言和历史语料重构它们的语法化过程。
量词的产生对指代词的嬗变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量词,在谓语动词之前的句法环境里逐渐变成一个指代词;二是量词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汉语名词短语的结构,从而使得原有的指代词不适合新建立的语法体系,而使新产生的更符合量词特性的指代词最后取而代之。语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带来语法系统的演化。结构助词“的”的产生和指代词系统的嬗变,都是量词系统的建立而带来的变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北方方言的“这”,也论及了南方方言和近代汉语的“个”,它们皆为近指代词。关于远指代词“那”的来源尚不清楚,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在很多方言里的同一个指示代词既可以近指也可以远指,比如山东潍县话,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