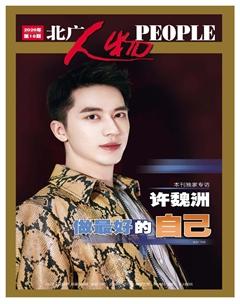李洱:生活在词与物的午后(上)

大年初三,李洱就从老家河南济源回到了北京。他原计划是要在老家待到正月十五的,因为他奶奶要在那天过九十五岁大寿。是新冠病毒改变了他的计划……
昨日重现
跟李洱通电话,再次访谈,才想起去年1 2月1日,在北京,第一次对他进行访谈时,武汉已有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彼时,他正奔波于各地,参加活动,有公事,也有私事。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出行最密集的一段时间。
他患了急性咽喉炎。12月上旬,出席华东师大和上海作协的活动,讲话声音低沉。时有医生通过他太太告诉他,医院里有类似SARS的病毒出现,让他小心。但“我为什么没有重视呢?”李洱说,“当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后,也都没有料到,之后会蔓延到这种地步……”李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83级的学生。他进入大学时,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发展的阶段。当时活跃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作家和评论家,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时候,所有中国人都是进化论者,都认为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思想开放,日新月异。”李洱说。
当年的一个场景始终在李洱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甚至把它写进了《应物兄》———李泽厚先生是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他的到来让人们激动不已。李先生到来的前一天,应物兄去澡堂洗澡,人们谈起明天如何抢座位,有人竟激动地做出了跨栏的动作,滑倒在了地上。那真是一个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的时代。我十年前采访过李泽厚,他说:“其实在80年代,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多出名,后来知道了,就有点后悔,我应该多去大学走走。”2014年,已多年没到大学讲过课的李先生,又去华东师大讲了一次,就又碰到了一件让他哭笑不得的事。“前年,李先生到上海某大学演讲,刚一露面,女生们就高呼上当了。原来,她们误把海报上的名字看成了李嘉诚先生的公子李泽楷。”这是《应物兄》里的另一段文字,也是当年新闻的再现。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的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在颁奖前见到了应物兄,我说你写的李泽厚在华东师大的讲座,我就在現场。没错,他就说了不到一刻钟。那是1 986年。应物兄很得意:我没瞎写吧。”现在,朋友们都喜欢直接称李洱为“应物兄”了。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教授黄平是研究李洱的。《应物兄》的结尾:“应物兄被车撞倒,一个声音从天上飘来:‘他是应物兄。”黄平认为他的这句话将当代文学中的自我又向前再推一步,塑造出了第三重自我———局内人自我。李洱在1999年1 2月写的《局内人写作》中,也解释过这个概念。黄平把这称作“第三自我”。李洱喜欢加缪。黄平认为“加缪可以被视为李洱写作的思想背景”。那个午后,我和李洱又在电话里聊起了加缪和他的《鼠疫》。这让我想起了李洱曾将自己的写作总结为“午后的诗学”,还有加缪曾说自己的思想是“正午的思想”。
已知和未知的日常
回到1 2月1日的午后,李洱为了说明奥登对于诗学的拓展,背诵起了奥登的《怀念叶芝》:
但是那个午后,却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唯一/流言的午后,到处走动着护士/他身体的各省都反叛了/精神的广场空空如许/寂静已经侵入大脑的郊区……一个死者的文字/要在活人的腑肺间被润色。”他背得非常投入,全情沉浸在其间。“奥登为什么要怀念叶芝?因为在叶芝之前,诗歌在现代派诗人那里都是自我的抒情。而到了叶芝这里,他提出了诗是和自我的争论。和别人争论产生的多是废话,和自我争论产生的才是诗学。到了奥登这里,又往前发展了,跟广大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李洱边背诵诗句,边穿插着解释,“但这实在又太难了。”如何反思知识,如何让知识进入小说,进入文本,这是他要思考的问题。《应物兄》就是他在一部中国小说里,大面积处理知识的一次尝试。
疫情中,也有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录一首诗来表达对抗击疫情的支持。他没有在对方提供的选项里做选择,而是选择了甘肃支援湖北医疗队一位护士写的《日常》:
雾霾,阴雨/五天里,潮湿和凄静/冷和毒,泪和伤/这些灰暗的词/多么希望你们远离……
李洱把这首诗称为“新国风”。他说:“诗三百中的‘风都是民间的声音,平白如话,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修辞。”在电话里,我再次和他说起了《鼠疫》的结尾。他坦白他在《应物兄》里写到济哥时,就是受了《鼠疫》结尾的影响。济哥是《应物兄》中济州消失的一种蝈蝈,后又获得了重生。他想表达希望所在,同时也想表达,这是某种病毒式的存在。他直接写过病毒,在他的成名作《花腔》里,巴士底病毒。这种虚构的源于法国的病毒是经由一条狗传到中国的,书中的主要人物“蚕豆”被这种病毒感染了,差点死掉。而到了《应物兄》里,“巴士底病毒”又以知识的形式重新出现了一遍。知识和人在李洱的小说中正在连成一个整体,形成庞大而繁复的体系。
《应物兄》里,邓林说:“老师们肯定知道葛任先生。葛任先生的女儿,准确地说是养女,名叫蚕豆。葛任先生写过一首诗《蚕豆花》,就是献给女儿的。葛任先生的岳父名叫胡安,他在法国的时候,曾在巴士底狱门口捡了一条狗,后来把它带回了中国。这条狗就叫巴士底。它的后代也叫巴士底。巴士底身上带有某种病毒,就叫巴士底病毒,染上这种病毒,人就会发烧,脸颊绯红。蚕豆就传染过这种病毒,差点死掉。”
这段话就可视作是《花腔》和《应物兄》相连而成的一个结点。葛任是《花腔》的主人公。他在小说中所写的《蚕豆花》,是寻找小说谜底的核心线索。只有读懂了这些文字,才能合上李洱小说的语汇节拍。李洱仿佛给自己的小说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洋葱皮。其最核心之物是什么?是真实的吗?或者什么都找不到。洋葱需要读者动用智力去剥开,所以读他的小说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
那庞杂的百科全书式的《应物兄》,想要处理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是“在当下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言知行合一的难题和困境”。这是他告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樊晓哲的话,她又转述给了我。
李洱在写《应物兄》的后记时,流了眼泪,但他并没有将眼泪写到后记里,樊晓哲却亲眼看到了这些眼泪。她站在桌边,看到李洱正在修改后记。“出于编辑的习惯,我一字一句念出了声,为的是看文字在身形音节上是不是合衬。刚刚念完非常简短的第一段,我察觉一旁的李洱有些异样。转过头,我看到了一个热泪盈眶的李洱,这是我认识他十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如此动容。”
(未完待续)
据中国作家网卫毅/文整理
——论李洱《应物兄》的空间叙事
——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