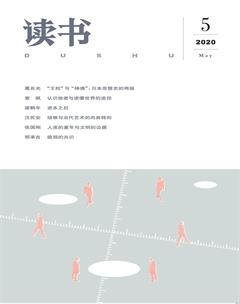文学的母题
王一方
在电脑键盘上敲击“wenyi”,并列跳出“瘟疫”与“文艺”,这便勾起我对这两个表面上不相关主题的关联性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使大家都被迫宅在家中,成了各路野狐禅的“坐家”,让真正的作家们心生醋意。曾几何时,蜂起的网络作家早已将头顶着人类灵魂工程师光环的精神贵族扯下神坛,遁入平民階层,沦为“坐以待币”的职业写手。坊间还有意无意,谐趣地将“作协”误读为“做鞋”,实在是大不恭。此时此刻,职业惶惑有增无减,作家之为作家的价值何在?全民疫情恐惧之下的深呼吸、睿思考投射何处?继而叩问文学的母题又是什么。即使有人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击蒙了,一些笔墨抖落到了地上,但不会集体休克,放弃对母题的思考。要知道疫情中每一位患者都有一个受伤的灵魂,而非只是一个气喘吁吁的“白肺”,如何面对这一个个受伤的灵魂,需要医学的陪伴、救助,也呼唤文学的疗愈, 作家的共情、抚慰、安顿。
生命即为文学的母题,因为生命是生活的舟楫。在我看来,生命的本质, 不是“ 身体写作”所渲染的声色犬马、肉欲张扬,而是战乱、饥荒、瘟疫卷起的苦难波涛、死亡战栗中的人性升降、灵魂开阖。一场“二战”催生了佳作绵绵的战后文学,其核心似乎不是战争本身, 而是由苦难、死亡母题透视人心,洗涤人性的文学机制。中国当代的史诗性作品《白鹿原》《活着》在宏大的时代跨度中书写了战争、饥荒、动乱的场景,却刻意淡化或回避了疫病元素。不管怎么说,文学无法摆脱人类苦难、死亡的拷打,也无法逃脱生命悬崖上人性何以安放的终极思考。
因防疫而封城,人们会自然地联想起加缪笔下的《鼠疫》,那也是一次围城阻疫,在加缪的笔下,瘟疫不仅瞬间夺命,也解剖着人性的善恶。其实,要究根溯源,曾经是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加缪,他当时要展现的是法西斯病毒蔓延的欧洲危机,鼠疫的扩散与阻击只是一个隐喻。或者我们还可以联想起影片《卡桑德拉大桥》,那辆即将冲向危桥的瘟疫列车,时间随着车轮的飞转在消失,空间被压缩在狭小的车厢,各色人等都在显露自己的本能与本色。灾难是人性的课堂,苦难是人生的导师,这堂沉重的生命课教会我们,珍惜生命乃人之本能,生命权、健康权也是第一人权。但就在此时,生命的真谛似乎被遮蔽了,生命不是永恒的瞬间,它是一个充满玄机的历程,生机无限与危机重重并存,道高一尺与魔高一丈同在。
什么是生命?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生命是一个“人之为人”的过程,一次次“成为自我”的冲动与行动,少不了生命巅峰的冲刺,试图去成就生命的圆满,抵达生命的彼岸。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山路,途中有多风光,就有多险峻,头上苦乐一线牵,脚下生死两茫茫。但是,人类似乎不接受无理由的苦难,也不接纳无先兆的死亡,常常会发出为何厄运总是降临在好人头上的诘问。因为,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是有着罪(原罪)与罚,蛊(阴谋)与罚、辜(非罪之虞)与罚的生死逻辑。从这个意义上看,瘟疫是一次大考,是对整个社会,也是对那些背负作家名声的思想者、书写者的大考。
很显然,间歇式的瘟疫散发并不构成作家们的集体关注,也不必将苦难、死亡的沉思全都系在瘟疫事件里, 在敏锐的作家,尤其是医生作家那里,完全可能泛化为疾苦灵性与人文、社会病理的关注点。这是另一种身体写作,一种反身性体验。包括疾苦折磨、煎熬的体验,他者的叙事与自我的宣泄,自我希冀与觉悟,绝望与豁达,求生欲望与自我放弃,濒死恐惧与彷徨,死后的归途, 未了的心愿;敬畏与悲悯、恩宠与勇气的导入,关注长期照顾期心智的安宁,临终时节的安详,灵魂的安顿,失能、失智之身的舒适、体面、尊严;亲情、友情的冷暖、疏离与断裂,被抛弃、被冷漠的恐惧,陪伴的渴望,被见证的希冀,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共情耗竭,病患期的家庭矛盾与和解;财务短绌与破产的担忧与恐惧,连累家人与家庭,自我的罪感,厌世、自杀意识的萌生。遇上有质感的文学叙事,将更进一步淬炼出苦难峡谷的穿越与超越, 生死的恐惧、接纳与豁达,宿命的顺应与适度的抗争,生命尽头高品质的陪伴与见证,如何缔造爱的遗产,身外/ 身后的遥望等人生母题的深度挖掘。
在非疫时期,癌症文学无疑是一曲生命的箫声,书单可以开出一大摞,既有获诺贝尔奖作品《癌病房》(索尔仁尼琴),也有网红作品《滚蛋吧,肿瘤君》(熊顿)、《此生未完成》(于娟),既有文坛翘楚周大新的力作《安魂》,也有哲学家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如果说癌症是一次托付生命的壮游,彻动灵魂的远行,癌症文学就是一部记录人生历险的游记,这份游记不仅值得个人珍藏,也值得每一个希望生命精彩的人细细品味、分享。癌症文学作为文学化的癌症经历反刍,癌症罹难的文学化叙事、省思,具有生命书写的类型意义,不仅其体裁多样,包括:纪实文学,这是一份源自医者、患者、家属亲历体验以及有疾苦体验的作家的质朴的白描与现场的反思;小说,着力于癌症人格的塑造,人性的透视;诗歌,富含癌症的隐喻、比兴;随笔,流淌着病中的生命体察与感念;还有戏剧、电影,不一而足。其价值不限于对疗愈叙事的拓展,更深刻地揭示癌症的宿命面相,它是灵魂的裸舞,是生命险境中人性、灵性、诗性的抒发,是一部人类的疾苦与蒙难史,也是真真切切的患者超越疾苦与死亡的生命历险记,一次生命失落、失意、失重、失控、失速、失魂、幻灭的体验。癌症文学的精神阅读史是肉身痛苦,心灵苦难、生死宿命、救疗体验的接受史,感受史、投射史。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借他人的苦难,得自身的彻悟。如果说踢球观球是男人格斗欲与英雄梦的替代,癌症文学就是健康人、幸福人(只是幸存者)生命两极体验的品味与遥望。
在癌症文学的字里行间,浸透着灵与肉的呻吟,癌症分明是意象中的上帝惩罚,是命运的当头一棒,是苦海夜航,黑暗包围,冰冷包裹,也是爱与希望,癌症家庭、癌症社区中的情感纽带与关爱支撑,生命希望幻灭的心理历程。细读每一部癌症文学,都能发现其文学桥段十分丰富,可谓步步惊心,每一步都是杜鹃泣血的呜咽,初诊时如同瞬间掉进冰窟、深渊,万箭穿心,心乱如麻;抗争期又一波三折,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度日如年,复发的纠结难以接受,屡败屡战之后的人财两空更是心碎滴血;病中还伴随着癌症与爱欲的纠结,他者(爱情、亲情、医护情、友情、宠物情)的爱,自我之爱,神圣之爱的忽明忽暗;灵修的自我救渡(阅读,修炼),爱书/ 书写的患者不孤独,与书/ 灵为伴,可以与神对话,催生病中的精神发育,写作也是解脱,由倾诉而寄情、遥想、沉浸、稀释、放下;最难的莫过于坦荡地诉说最后的心事,从遗产、遗愿、遗恨、遗情的咀嚼到道别、道情、道谢、道歉、道爱的余韵绕梁;还有放手、别离时的豁达,不要在我的坟头哭泣, 我不在那里,灵性归宿,魂归何处,彼岸抵达;还有未亡人的哀伤记忆的平复、消退。这样的书写具有何种意义?回答是肯定的,只有生命故事可以抵达生命的彼岸,只有接受生命,才能疗愈生命;故事,是一种自见,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自我;说/ 写故事,可以转化躯体痛苦,是一种疗愈的美学,它是一种彻悟生命的途径,可以重新获得支撑的力量,它还可以创造一种生命的链接,找回人性的根本,重新抒写生命。
实话实说,癌症文学的确有些沉重,只因为肿瘤是人生最急的转弯,童话变成噩梦,它与人类苦难、死亡距離最近,不仅痛苦最悲切,且死期可遥望,身心社灵的震荡最激烈。以至于那些人生旅程中春风得意的人们会敬而远之,还有那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或许不应该给他们过早展示生命的残酷面。然而故事可以温宁不惊,但文学的母题并不会逃逸,譬如经典的儿童文学童话作品《夏洛的网》。
在E.B. 怀特的笔下,小猪威伯的生活很惬意:“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冬天还是夏天,秋天还是冬天,不论是雾霾密布的阴天还是阳光明媚的晴天,谷仓里的生活都是一样的美……这温馨的仓底,有鹅嘎嘎不休,还有季节的变换,有太阳送暖,有燕子来去,有灵鼠为邻,有绵延相似得难分彼此,有蜘蛛们相亲相爱,有农家肥气味飘荡,一切都是喜气洋洋。”他全然没有意识到死亡。然而,蜘蛛夏洛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在夏末死去,于是她在默默地规划着死亡的降临。“她知道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为此,她做好了盘算,产了卵,告诉朋友去日无多,并向他们告别,她做的这一切让浓浓的平和安宁将死亡包裹,尽管她对蜘蛛的寿命长短心里有数,那是一个定数,无法改变,可是,夏洛依然可以对其死法有所选择……她在自己的蜘蛛网上写下了赞美威伯的话,这就让威伯变成一只出名的猪而免遭屠宰。”童话语境中的威伯与夏洛,展现了两种生死眺望,但怀特并没有粗暴地宣扬文学的苦难、死亡母题,也没有单向度地面对死亡话题,而是表达出一个超然的信念:自然的便是善的,自然的、与自然一致的死亡是善的死亡,是可以接受的死亡。不自然的死亡是恶的死亡,是应当与其抗争的死亡。威伯还是一只稚嫩的小猪,所面临的首次死亡威胁是不善的,应当努力去抗争,而夏洛正常地过完一辈子后才去赴死,这是善终之死,是可以接受的。
告别文学,回到科技社会里,生老病死的规律有了更加充分的科学的分析,统计学家运用大数据编列出某一阶段的死亡谱来,让世人都觉得事出有因,譬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车祸、运动、风险职业致死。百年前位居前列的传染病致死,因为屡屡未爆发大规模疫情而逐渐垫底,被移除到前十位之外。当突然遭遇疫情杀“回马枪”,便立马警觉起来,只因它原本是计划外死亡。其实,细想起来,疫病呈现周期性活动规律,隔三岔五地造访人类,不会消停。细数新世纪的二十年,疫情的烽火台不时燃起狼烟,SARS、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感染、新冠肺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愿这次疫情早日得到有效控制,并从中取得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