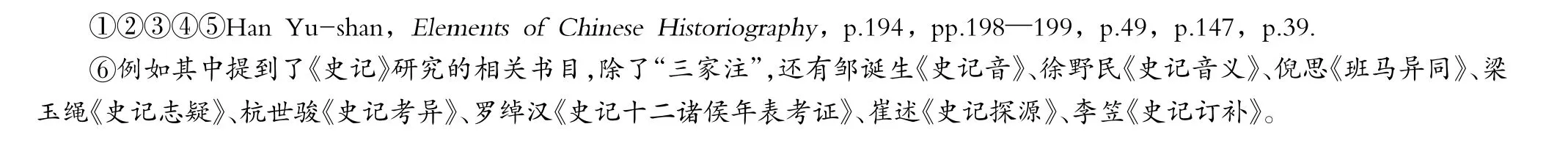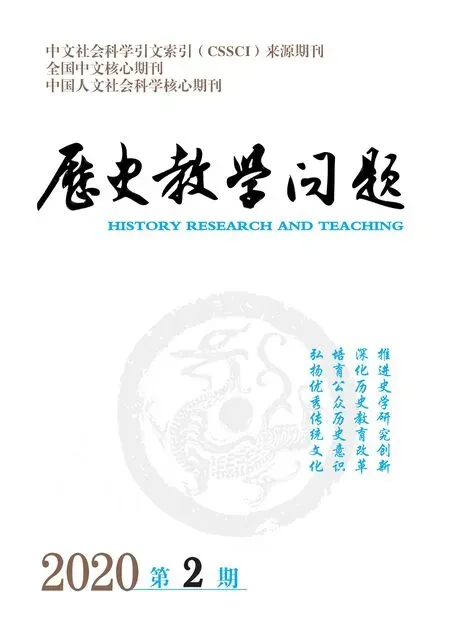20 世纪中前期两部英文中国史学史
胡 青 松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关注始于19 世纪前叶的传教士汉学时期,在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所办《中国丛报》(1832—1851)中已有对于《史记》《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历史典籍的介绍。然而,用英文来书写中国史学史则是在一个世纪之后。20 世纪中前叶先有贾德纳,后有韩玉珊写就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英文专著。迄今已有相当成熟和充实的英文版中国史学史专著——《世鉴:中国传统史学》,1○但在今日依然有必要回望以英文来撰述中国史学史的历程。国内学界到了新世纪也开始注意到这两本专著。朱政惠先生在论文中最早提到这两本著作,称贾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为“世界上第一本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史学史著作”,2○也将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称为“一本有影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3○伍安祖、王晴佳在《世鉴:中国传统史学》一书的导言里也肯定了这两本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认为它们属于“具有巨大学术价值的开创性成果”,《中国传统史学》是“美国第一本关于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4○
一、《中国传统史学》
美国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又译为嘉德纳、贾天纳)于1938 年通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史学》()一书,此书在美国堪称最早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史学史的英文专著,虽为薄薄一册,却富有开创性意义。

贾德纳(1900—1966)乃目录学家,是首位在哈佛以西方汉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美国学者,20世纪美国汉学界的先驱者之一,因其名望于1949 年当选为远东协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主席。1922 年贾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23 年获硕士学位,1924 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5○1933—1934年,时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的贾德纳加入哈佛燕京学社,教授“中文20:中国历史”,此乃首个交叉课程,既在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也在历史系讲授。1934—1935 年,贾氏又开设“中文12: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1935 年,贾氏以题为《〈清史稿·圣祖本纪〉译注》的毕业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35—1936 年,贾氏开设一学年的中国历史纲要课程“中文11: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的演变”。1936—1937 年,贾氏的中国历史纲要课重新登记为“历史85:中国历史——从古至今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演进”。1○1937 年贾氏被聘为东亚系助理教授。
1938—1939年贾德纳受学社资助在北平休假、进修,其间经洪业介绍,聘周一良为研究助理,帮助代看日文书报。后周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美读博,乃托钱稻孙物色继任者,钱遂推荐刚从清华毕业的杨联升。贾与杨一见如故,杨每周与贾见三次,用中英文交谈,协助贾看日语学报如《东方学报》等,做英文提要,帮贾氏选购古籍。1939年贾氏回国,知杨无收入来源,遂请杨为其标点百衲本《宋史》及《后汉书》,仍按月付酬。1940年贾电报邀请杨赴美继续任自己的助理,并让杨以半工半读形式读博,杨于是在1942年2月至美。最初一年,杨之学费、生活费皆由贾提供。杨先入哈佛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然后于1942年秋入远东系读博,于1946年2月获博士学位。杨氏毕业论文为《〈晋书·食货志〉译注》,与贾氏之前的博士论文同属一类,论文选题应该是受到贾之指点。在杨氏哈佛求学期间,贾德纳夫妇对杨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杨也曾经住于贾之寓所。1940年9月贾氏三年助理教授聘期已满,但哈佛燕京学社又为之延长一年,让其带薪休假一年。1941年秋贾氏不得不离开哈佛。杨认为贾氏错过终身教职的原因是,为了帮助他人而耗费太多时间,“太不自私,而且对自己的著作,定的标准太高,差一点的就不肯随便发表”。2○贾氏之于美国汉学的一大贡献是,将杨提携为一流的汉学家。杨在《自传》中云:“1941年4月春假,贾公命游纽约、华盛顿等处,见学界老辈,贾公每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3○杨对贾也是至为感激,在回忆文章中称:“贾德纳是我最好的西友,也是我能来美国的大恩人……贾德纳为人,异常的忠厚正直,最喜欢帮人,尤其是学生。”4○杨之所以能成为“汉学第一人”(费正清语),与贾德纳的倾力栽培是分不开的。1943—1945年,贾德纳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陆军特别训练计划·中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室”助理主任。1945—194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史,1947年教日本史。5○1947年又至耶鲁教目录学及远东文化史,聘期也是一年。1948—1949年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任中国史顾问。6○杨在1947年致胡适书信中提到,贾之所以在以上学校皆难以安身,可能是因“这位先生外交是吃亏点,学问实在不错”。7○杨对贾学术水平的评价是,“精于目录之学,除了对西洋汉学著作如数家珍之外,对中国、日本学人的造诣,也颇了解。……我虽帮他中日文,在其他方面,实在是他的学徒”。8○根据杨的回忆文章,贾晚年患有健忘症,见杨竟有“你认识我的中国朋友杨联升吗”之问。
贾德纳还是一位藏书家。上世纪20、30 年代两次来华访学,分别是1925—1928 年和1938—1939年,在华期间为自己以及哈佛燕京学社购买了大量古籍。杨联升称:“贾的中西日文书收藏之富在美国个人中要算罕见。”9○当其晚年时,贾氏因其子任教于布朗大学之故,于1961 年将35000 多册线装藏书悉数捐给布朗大学图书馆,其中有经史子集共77部、5000 多册明清善本以及362 部民国版《四部丛刊》古籍等。现今在北美颇有规模的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即是在“贾德纳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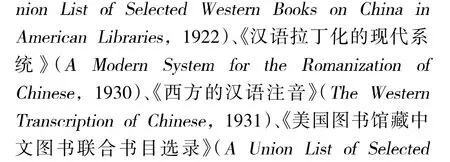


贾氏除《中国传统史学》一书外,还有以下著述:《美国图书馆藏西人中国研究联合书目选录》(览》(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A Survey of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1935)、《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1944)。1940 年贾氏还参与了William L. Langer 主编的《世界历史大百科全书》的编写。1○杨联升在1947 年致胡适书信中说,贾德纳还想做“汉学入门”,“可惜一直没动笔,我真替他着急。这位先生人太好,总是热心给人家帮忙,自己的事情却耽误了”。2○
贾德纳在《中国传统史学》一书介绍中坦言,著述的目的并非是写一部完整详细的中国史学史,毕竟这个填补空白的任务过重,他只是想去尝试描述中西史学写作的相异之处。3○
《中国传统史学》共分为7 章。首章简要梳理了自清代乾嘉以来至20 世纪20、30 年代的史学批评发展历程,介绍了清代的朴学、19 世纪末史学批评的复兴、胡适与梁启超分别倡导的新的史学及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作者才回溯到中国传统史学:第二章名为“动机”(Motivation),列举了自上古而下的一系列系谱,从《竹书纪年》《世本》到《尚书》,同时也分析了以《春秋》为代表的另一类史书,指出两类不同的著史动机,前一类忠实于记录帝王世系,而后一类含有道德褒贬,最后还谈到《左传》和《史记》所代表的“信史”观念。第三、第四两章从文本批评和历史批评两个角度介绍了中国经典文本的流传以及与西方迥异的历史观念。第五章分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方法——综合法。第六章进而深入到中国史学“同一性”的风格,最后第七章介绍了中国传统史籍的具体分类,4○还详细分析了正史的体裁、史料来源。
贾德纳在书中对中西史学观念进行了一番比较。在他看来,西方史学是以逻辑的顺序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和分类,按照起因和结果来呈现材料;而中国史家视过去为一系列具体事件和行为,历史只是对事件的准确、冷静的记录,因此史家不能将个性投射到作品当中,且不能呈现自己对于真实因果关系的思考。5○贾德纳还注意到,中国传统史著更像是共同著述,而不像是个人创作,因为其中有不少对先前历史记录的复制,但是这在中国古代不会被视为抄袭,反而是一个颇为自然的现象,如此一来,中国传统历史撰述并非是创造性地构建出与之前史书同等篇幅的作品,而是对之前史书进行材料选择和编排。贾德纳将此种编写方法称为“原始的综合法”,即对早先作品进行“解剖”,再以编年顺序对这些零散的断片进行排列。贾德纳以为,此种编纂方法特别看重文本的完整性,故而不会尝试去合并那些并列的文献记录。他从西方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些互相作为补充的不同表述只能算作历史材料,而非历史本身。
在对中西史学进行了如上比较之后,贾德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如下批评:一、中国传统史家的撰述最为欠缺的是没有参考目录和参考文献,故而很难从中找出材料的出处。二、中国传统的史学写作最明显的问题是省去了事件的背景,而且极少指出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三、读者在阅读传统历史典籍时,因为史家在作品中的隐匿,读者难以与史家建立一种联系,文本缺乏启示性。7○
尽管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批评,贾德纳对《史记》的评价依然很高,认为《史记》是一部比《春秋》更伟大的历史著作,其伟大之处在于,司马迁以其所能接触到的材料对自己民族的整个过去做了一个完整的刻画,且首次突破了传统框架的限制。贾德纳以《史记》为司马氏父子的共同创作,称之为“”,8○他分析说,司马谈著史的动机在于青史留名,通过忠实记录他人的荣耀和堕落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不朽,但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位明断秋毫的史家,自己要做的是,通过完整的叙述可以为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人物带来公正,将他们从湮没无闻之中拯救出来。9○贾德纳认为,司马迁继承了《左传》而下的信史精神,后世史家也以此为鹄的,于是撰写信史成为中国史家最普遍也是最高的目标,对于完全的信史的设想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写作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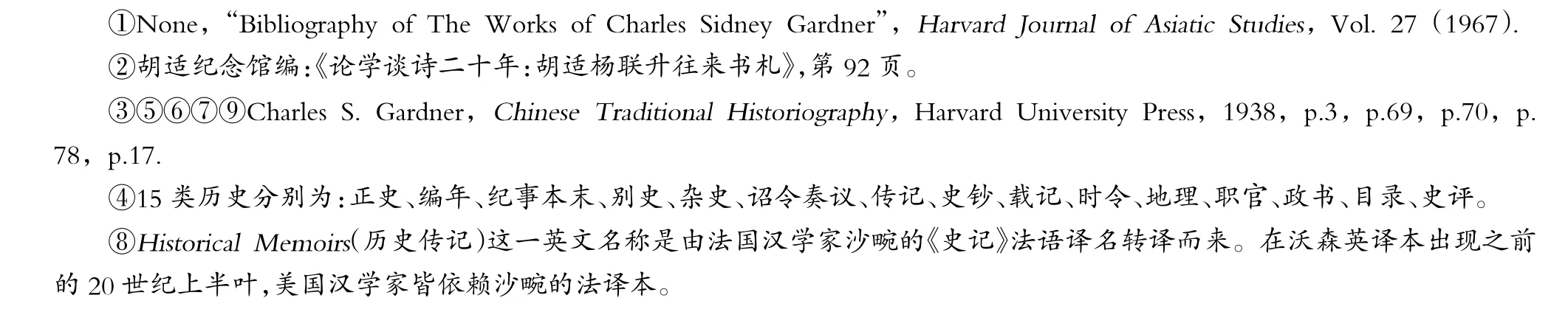
贾德纳有关《史记》的观点多出自于沙畹的《史记》法译本。在提及《世本》时,贾德纳引用了《史记》法译本中的材料,指出司马迁虽然没有提到《世本》,但是他在《史记》中所提之《五帝系》或源于《世本》。再如,关于《春秋》的作者,贾德纳也是参考了沙畹的《史记》译本,引了《孔子世家》里的说法,即孔子作《春秋》。尽管盛赞《史记》为巨著,让贾德纳感到困惑的是,《史记》的风格相当非个人化,作者似乎是隐匿的,无法确定哪些段落为作者自己所写,哪些是直接从其它史料中采录而来。1○
《中国传统史学》在绝版后由杨联升在1966 年为之作序再版。近半个世纪以来凡是关于中国史学通史的汉学文章都会提到这本具有开拓意义的小书。平日吝于夸赞欧美汉学家的杨联升对此书有较高评价:“我今年又细读他的《中国旧史学》,觉得他对于法国(学)派几位大师之说,都能贯通,如关于群经的几个脚注,作得真算不坏。绝非卖野人头者可比。”2○欧美汉学家如荷兰的戴闻达(J.J.L.Duyvendak)、英国的韦利(Arthur Waley)、美国的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德国的福克司(Walter Fuchs)等都为此书写过书评。戴闻达强烈推荐此书,认为这本绝佳的小书不仅可作学生研习汉学的入门和指南,还可以让欧美的史学家了解中国史学的问题。3○
二、《中国史学纲要》
韩玉珊(1899—1983)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下简称为UCLA)历史学系第一位华裔教授。1899 年出生于北京,1924 年获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29 年波士顿大学博士毕业。1930 年归国之后,曾追随晏阳初先生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在定县任社会式教育委员会干事。1929 至1933 年居于北平。1933 年携美国夫人Edna Nona Quick 移居上海,任职于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夫人教授英文,韩氏教授历史与政治学,同时负责历史系行政工作。韩氏还曾任职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曾任上海第二届人力车夫互助会理事。1937 年淞沪会战爆发,又前往美国定居。1941—1966 年间任职于UCLA 历史系。韩氏也是一名收藏家。1984 年其个人收藏品由韩氏遗嘱执行人捐赠给UCLA 东亚图书馆。这份藏品被标为“Han Yu-Shan collection(1646—1910)”,包括刊于1684—1910 年间的24 部书院史、1798 年的《金刚经》印本、一套《金刚经》原版木刻印版、500 份清代科举考卷(1646—1904)、朝廷诏书以及手稿卷轴。4○
韩玉珊是学者型官员,著述不多,除《中国史学纲要》这本专著外,还参与过《中国》一书的编写,写了第一章“民族塑造”。5○此外,还有4 篇论文、十几篇书评,且这些文章多发于上世纪40、50 年代,此后60 年代只有2 篇书评,70 年代惟1 篇书评,就此淡出了学界视野。4 篇论文分别为:《当代中国哲学趋势》(Some Tendenc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Vol.25,No.19,1928)、《中国的科举考试:昨天和今天》(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Yesterday and Today,Vol.15,No.2,1946)、《中国史家的地位》6○(The Role of Historian in China,Vol.16,No.2,1947)、《福尔摩萨所受的三段统治》(Formosa Under Three Rules, Vol.19,No.4,1950)。韩氏为汉学名家的著作写的书评有:《傅路德〈中国人简史〉书评》(由上可见,韩玉珊在《太平洋历史评论》发表的文章最多,其次是《美国历史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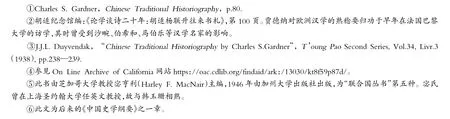


在《中国史学纲要》序言中,韩玉珊称17 年前贾德纳写了美国第一本中国史学史著作,而自己的著作较之前者,更注重中文文献资料,且做了拓展和延伸,篇幅更大,涵盖的时段更长。《中国史学纲要》一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书中有各种详细的术语翻译和书目列表,此书可与《中国传统史学》一起作为西方汉学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入门读物。费正清在为此书写的书评中写道,书中充满了大量有用和貌似无用的材料,但是这些貌似无用的材料对于初入行的汉学家来说也具有独特价值,韩玉珊提供了一种宝贵的视角,可以让这些初学者见识到中国传统史学这一领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
与贾德纳略为不同,在韩玉珊看来,中国史学的持续性无论被视为缺陷或者优点,都是其固有特质,为了维持自由与束缚、多样和统一、求新与传承之间的平衡,中国史学常表现出一种积极努力。作者自称在书中主要参考了以下著作:金毓黻版《中国史学史》、徐浩《廿五史论纲》及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Hummel)的《清代名人传》()。当然,韩在著作体例和一些观点上也参考了贾德纳的著作,在书中称赞贾氏《中国传统史学》为“有价值的一本小书”,在论述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存在的缺乏参考目录、参考文献的问题时,韩也大段引用了贾德纳的文字。2○与贾德纳一样,韩玉珊也使用了双语的方法,涉及中国史学的专名都列出了魏妥码(Wade System)、中文和英文翻译,如“Cheng-shih 正史or Standard Histories”,此方法为当时欧美汉学界通行的方法,可谓惠及后学之法。
全书共分为12 章。第一章题为“中国史家的力量”(附录:自公元前256 年至公元1911 年历代史官所属机构名称、职责),介绍了史官的职能、作用及官修史书和私修、合修史书的具体分类。第二章对中国史学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第三、四、五3 章乃是关于中国古代经典及史书的分类、通史及专史。3○第六、七、八3 章有关中国史学术语的翻译和解释,其中有242 个与中国传统史学编撰有关的术语,且列出了46 位清代以来的史家及作品。第九章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类型作了详细的列举。4○第十章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史学批评史。第十一章有关历史地理。最后一章从编纂、体裁角度分析了“二十六史”。
韩玉珊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肯定之处颇多。在第一章里,韩氏写道,自古至今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可谓独一无二,这是中国人有意选择传承的一大民族特性。在他看来,这与中国特有的方块文字有关——中国人对文字的崇敬让记录人事的想法更为强烈,于是这种投入几乎带有一种宗教的色彩。5○接着他从字源角度分析了“史”字的含义,并一一列出史官在上古的各种名称(如《周官》“六史”),指出“太史”职责在先秦有双重职能,要同时观察和记录自然和人事。韩氏将史官的职能分为三种:天文、修史和监察,认为在汉代以前,史官主要负责前两者,而到了公元前后,更多负责后两者,以往合为一体的星象和修史职责逐渐分离,而修史和监察的职责逐渐合一,科学的史学写作与史官地位的上升(被擢升至监察之职)出现于同一时期,即武帝之时。韩氏还高度评价了史官对后世的影响,认为尽管现代学者视关于史官的记载为杜撰或者想象,但这些记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史官无论在修史或是行御史之职,要勇敢面对帝王的盛怒。为了证明史官的独立精神,韩氏举了《明史》的例子,史官们抵制了统治者的干涉达90 年之久,从1645 年至1735年,终于修成《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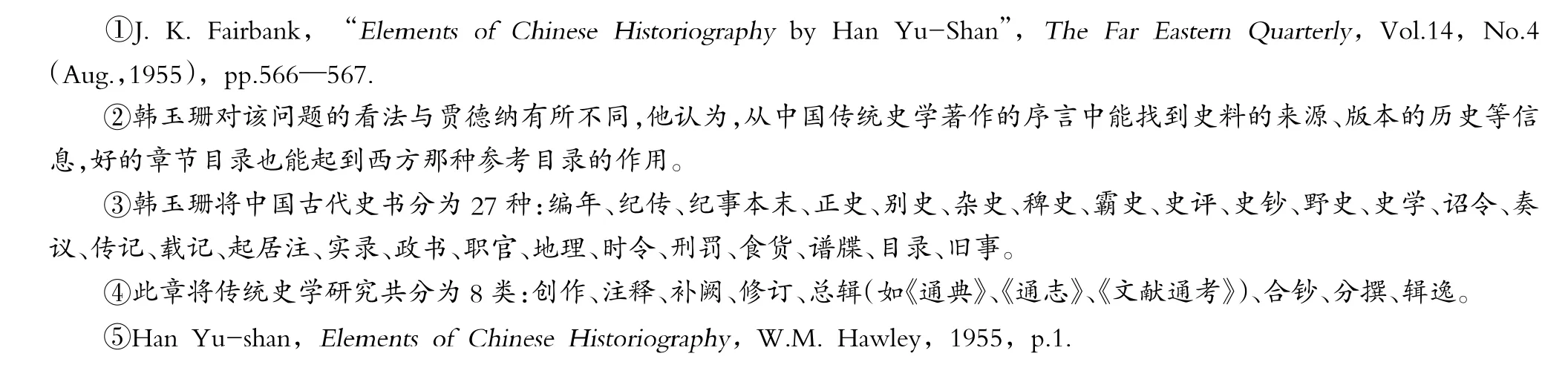
在肯定史官功绩的同时,韩玉珊也对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第二章里一一列举了这些问题:一、名称的混乱。无论是人名、年号还是地名,繁复多样。二、缺乏省时的研究方法。1○三、不准确的问题。四、引用史料篇幅太多的问题。五、过于简略的问题。六、过于“客观”的问题。七、后世添加和删改的问题。八、地下材料难以获取的问题。九、固守范式的问题。2○其中,作者在批判时着力较多的是第三、第六和第七个问题。在谈到不够准确的问题时,韩氏举了刘知几的例子,说刘知几尽管对前人史著中参考文献的不准确和古旧的表达极为不满,自己的行文中也是堆满了典故。中国史书有相当明显的一个特征,即在记录不同的事件时,所用表述雷同;另外影响准确性的一大问题是对材料的任意选择,以至于史家在用古代材料时,必须去搜寻那些对立的、异端的和被遗弃的史料。韩氏所言过于“客观”的问题乃是针对中国古代史书中缺少作者自己的声音这一现象,这是西方汉学家极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韩氏也引了《汉书》研究者德孝骞的话——“中国史学的一个常见特征是将叙述和解读截然分开”,而贾德纳也表达过同样的疑问。韩玉珊为此问题提供的解释是,历代史家追求这种“客观性”(即信史),是受儒家思想的限制,古代史家基本上都是儒生出身,在修史时自然也秉承这一原则。追求不朽的信仰深植于中国史家的心中,为了实现不朽,史家需要通过立言,而为了立言,史家就要不偏不倚地记录历史,这些记录本身即可为人伦道德提供标准,为后世提供镜鉴。当然,韩玉珊也写道,实际上是无法取得客观性的,因为在保存少量的原始材料同时,也淘汰了其它材料,另外,在史料的选择和编排上也暗含着史家的判断和诠释。关于后世对前人史书的添加和删改,韩玉珊先是分析了出现这一问题的客观原因,即古籍在历史进程中受到的各种严重损坏,在恢复古籍的过程中出现了篡改的问题,以致后世难辨这些古代经典的真伪;另一原因是公元2 世纪之前没有将经典的原文与注释分开的方法,直至马融创立了双行之法才解决了这一问题。韩与贾德纳一样,将中国古代史家爱好进行文本批评(即考证)归结于经典的篡改和伪书的通行,在他们看来,文本批评的流行极大限制了历史批评的发展。3○
虽然与西方汉学家一样,韩玉珊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缓慢,但在第十章《史学批评的延续》里,还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做了一番梳理。他首先分析了发展缓慢的原因:史料多为官方掌握;古代史家的目标只是客观叙述历史事件,对古代史家而言注释、补阙比批评更为重要;在官修史书的领域,有限制批评的倾向。韩玉珊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主要是由后辈史家对前辈撰述的批评、改正所推动,例如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荀悦在《汉纪》里对班固《汉书》的批评、袁宏在《后汉纪》中对范晔《后汉书》的订正。另外,另修新史也被视为间接的史学批评,如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是断裂的,在停滞了将近8 个世纪以后,史学批评在乾嘉时期才再次受到了史家们的重视,韩氏列举了其时知名学人及著作,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赵翼的《廿二史撘记》、崔述的《考信录》。在第十章,韩玉珊着重提到的两位古代史家是刘知几和章学诚。韩以刘知几《史通》为跨世纪的史学著作,标志着史学批评开始占据史学的中心位置。当然,作者也提到了刘知几的思想渊源,认为其史学观点依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史观的延续,并受到扬雄和刘勰等前辈史家的影响。尽管如此,韩玉珊高度赞扬了刘知几精神和方法的革命性,一一列出了刘提倡的几大准则:疑古、杂驳、忤时、点烦及覈才。而紧随刘知几即是关于章学诚的介绍,作者看来,章学诚开辟了一条新路,六经和其它文学材料都可以成为历史的材料,而且在章眼中,历史还是规范性的,为人类提供基本准则,故不仅仅是资料的汇集或者事件的记录。最后,韩氏还简要谈及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史学批评,提到了梁启超的“新史学”、章炳麟的通史观、何炳松的新史学方法及顾颉刚的“古史辨”。4○

《史记》作为正史之首,在整书中也占据了一定篇幅。首先,无论在历史上“正史”的内涵有多么频繁的变动,《史记》一直为正史之首。韩玉珊在第十二章“二十六史”里详细介绍了正史名称的演变,从“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到“十史”“十三代史”“十七史”“十八史”“十九史”“二十一史”“廿二史”“二十四史”“二十六史”。韩认可的名称是“二十六史”,从《史记》至《清史稿》,还加入了柯绍忞的《新元史》。在第十二章韩氏一一列举了“二十六史”的简明编撰信息。1○在介绍《史记》《汉书》的编撰时,韩认为司马迁和班固二人都是奉旨撰史,而实际情况是,司马父子和班氏父子的修史都是自发、私人的行为,并非得到了官方的授意,故而班固会因为私修史书而获罪。这是一个明显的讹误。韩氏也对“二十六史”之中传记的比重作了统计,结果是人物传记共覆盖了62%的卷数,结论是中国古代史家以个人价值和成就为造就历史的关键因素。2○其次,《史记》是最能体现通史之风的中国史书之一。在第四章“通史”里,作者称《史记》为第一部成功的通史,而“通史”之名称要始于南朝梁代吴均的作品。韩氏还提到了通史的标准——“会通”,并介绍了章学诚的通史观,尤其着重于其通史有“六便”“二长”“三弊”之观点。3○再次,《史记》对后世的史书影响深远。韩氏在谈到中国古代史学陈陈相因的问题时,将最初的范式归为司马迁的首创,认为《史记》堪称为“创作”,而中国古代史书极少可称“创作”者,“创作”必须是开拓性的、独特的,无论是在形式、方法还是综合方面要有创新。从形式来看,在介绍“二十六史”时,韩着重讨论了司马迁创立的“五体”,对“书”的评价极高,认为“书”以及后来的“志”为重建中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保证。韩氏还以《史记》三家注为研究“注释”类著作的最佳材料。4○从方法上来看,在论及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方法时,韩氏将之总结为以下几点:对历史材料的鉴别、对历史的安排、对历史终极目的的清晰构想。当然,《史记》的“五体”也并非完全出自于司马迁的凭空想象。韩玉珊也提到司马迁的源本——《世本》,以之为历史分类的原型,因《世本》中已有六种体裁,如“帝系、纪、世家、传、居、作”,司马迁正是受《世本》的启发才构建了自己的“五体”。韩玉珊以这种史学作品的内部分类为历史分类的开端。5○另外,对于为后世史家批评的《史记》体例不纯的问题,韩氏以《史记》里的“本纪”为例谈了自己的理解,为司马迁做了辩护:虽然“本纪”一般是以帝王为中心,但是在《史记》中就有例外,如《项羽本纪》与《吕后本纪》,司马迁之所以给项羽而非义帝、吕后而非惠帝作本纪,乃是因为前两者是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而后两位几乎完全被操控。
三、结 语
《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史学纲要》虽然只是两本小书,却可以作为以汉学为专业的欧美学生研习中国史学的入门读物以及工具书。《中国传统史学》一一列举了史部总共15 类著作,而《中国史学纲要》列出了242 个中国传统史学术语的英译及解释,也在介绍“二十六史”时制作了一个完整的表格,里面有每一部正史的详细编撰信息,还为主要史籍列出了参考书目。6○这些书目虽然还不够完备,但是对于一个入门者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然而,两位学人并不满足于编一本中国传统史学的工具书,在各自的书中也对中西史学的差异进行了一番思考。例如贾德纳对中西史学著作的编撰方式进行了对比,认为西方史著更注重逻辑和因果关系,而中国古代的史籍则只是材料的排列;而韩玉珊和贾德纳一样,也注意到中国古代史籍编撰中作者隐匿这一现象。要之,两书虽为小书,犹有可观之处,而且,以英文撰写中国史学史,具有开山之功。今日若要研究美国汉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这两本书必是难以绕过的材料。对于欧美研习汉学的学生而言,在读了这两本中国史学通史著作之后,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也会有一个大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