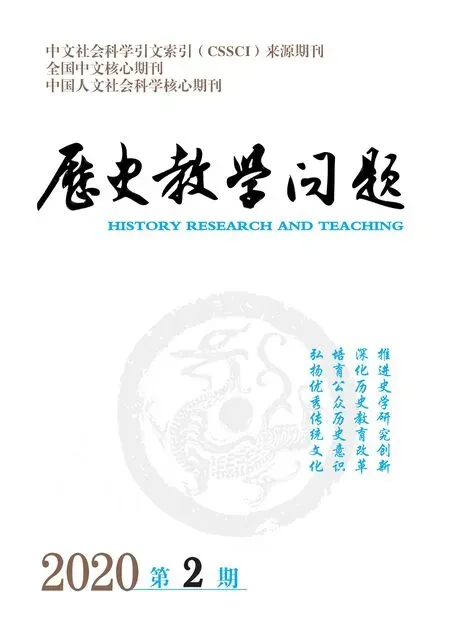“美国与甲午战争”研究中的若干史料辨正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还是“参赞署理全权事务大臣田夏礼”?
冯高峰 师嘉林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正确无误地解读和运用史料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要求,误用史料即便下笔万言,也只能是凭虚御空。然而,在史料编撰或史学研究中,要使每一条史料都准确无误实非易事。近年来,笔者发现,国内学界在研究美国与甲午战争问题以及编撰相关史料时,常把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署理全权事务大臣田夏礼”与其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相混淆。而且,在这些错误中,田贝父子都是以美国在华最高外交代表身份出现,这就使看似简单的人名混淆导致了相关史料的严重错误,对认识美国对甲午战争的政策、中日战争与议和以及中美关系关碍甚大,很有必要加以考辨。
一、“田贝”与“田夏礼”的混淆之误
“田贝”和“田夏礼”分别是美国驻华公使“Charles Denby”和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Charles Denby Jr.”在与清政府官方交往中所使用的中文名字,1○二人是父子关系。当时,中国没有拼音文字,无法写出外国人名,到中国的外国人需要取一个由两到三个汉字组成的中文名字。2○所以,这两个名字不应因翻译而造成混淆,而且,在他们各自发给总理衙门和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中,记载都非常清楚、明确。
甲午战争爆发前,田贝因病请假回美国做手术,3○直到战争爆发七个月后才返回北京。这期间,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全权事务由田夏礼署理。也是在这段时间,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多次请求列强调停未果、远东局势日益复杂化,美国对待这场战争的政策也逐渐由纵容日本侵略转向积极操控议和,国务卿还因此急迫地催促尚在养病中的田贝返回任所,结束田夏礼对全权事务的署理。可见,这一时期田贝父子在美国对甲午战争政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国内学界时常将他们的名字混淆,致使张冠李戴的错误在相关史料中频频出现。

首先,国内出版的一些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中,田贝父子常被混淆。阎广耀、方生两位先生选译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被广为引用的重要史料,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曾在序言中说:“这样较系统、较全面地选译美国官方原始材料,在我国中美外交史研究中,真可视为创举。……对关心和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件值得庆欣之事。”4○该史料集选译了13 份有关甲午战争的文件。笔者查阅相关档案文件后发现,其中有10 份是田贝与美国国务卿在1894 年10 月30 日至1895 年3 月20 日间的往来文件,然而译者把这些文件中田贝的名字全部误译为田夏礼。1○因为这时田贝已经返回北京任所并已开始履行公使职责,田夏礼的署理使命也已结束,不可能继续代行美国驻华公使职责了;2○而且,这些译文对应原文的署名都是田贝与国务院往来公文中常用的“Charles Denby”,3○“Denby”,4○或者“Mr.Denby”,5○而不是田夏礼署理公使时所常用的“Chas. Denby,Jr.”,“Chas.Denby Jr. Charge d′affaires ad interim”,或“Denby Charge”,6○故此,将其译为“田夏礼”显然是错误的。
朱士嘉所编的《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辑录了1894 年8 月4 日—9 月1 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美国侵略者包庇日本奸细等情形”的档案14 件。其中,与田贝父子直接相关的12 件照会文件,全部把“田夏礼”误为“田贝”。7○该史料集在“编辑说明”中提到这些档案源于“美国国立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然而,美国驻华公使馆与总理衙门往来照会档案,对上述文件的记载中却显示,美国使馆方面的署名都是“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署理全权事务大臣田”,8○即田夏礼与总理衙门往来的官方署名,不是田贝在华任职时的官方署名“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札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田”。9○所以,这一史料集也混淆了田贝父子。
其次,在已发表的有关美国与甲午战争的重要论著中,把田夏礼误为田贝的错误也层见叠出。《历史研究》2011 年第2 期发表的《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一文是近年来该研究领域发表的一篇权威之作,其中有一处将田夏礼误为田贝。该文在论证“美国希望通过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引用了如下史料:“1894 年10 月23 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写给美国政府的秘密报告中就反对接受清政府的和谈请求,明确表示在中国军队被日本逐出朝鲜之后即结束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应让战争继续进行,要使清朝帝国能够与这个世界和平、融洽,非武力不行。中国遭到败北,直到其皇朝受到威胁,都是有益的事。只有这样的时机到来之际,才是外国进行干涉之时。”10○然而,查对该文注释中所引美国外交文件1○后发现,原文件的署名是“Chas.Denby Jr. Charge d′affaires ad interim”,12○即参赞署理全权事务大臣田夏礼,而不是“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可见,该文是解读原始史料时将田夏礼误为了田贝。此外,该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5年第4 期上发表的英文版中,也把这份文件视为田贝发给国务院的,13○可能也是此前错误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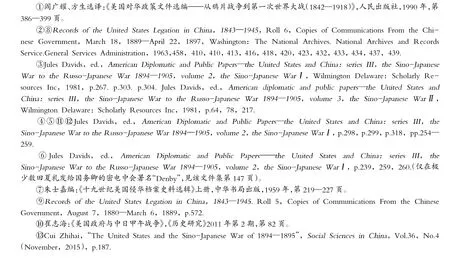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期所载《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之探析》一文,在研究发生于1894 年8 月1 日至9 月1日间的“美国对日本间谍的蓄意‘纵容’”问题时,把田夏礼的外交活动全部误为田贝所为。1○比如:该文在第174 页讲道:清政府“要求美驻华公使田贝,迅速转饬其驻上海领事,‘速将该倭人二名即交上海道审办’”。然而,查阅文中注释原文后发现,应该是“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署理全权事务大臣田”,2○即田夏礼,文中其他几处误用也与此类似。
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所著的《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在论述1894 年8 月1 日至9 月初的“日本间谍案与中美交涉”问题时,一开始曾谈到“美国驻华临时代理公使田夏礼”,而且在第229 页也明确提到田贝当时还未返回任所,但是,仍有近10 处将田夏礼误为田贝。3○另外,戚先生2014 年出版的《甲午战争史》在论述8 月4 日总理衙门致美国公使馆的照会时,也将田夏礼误为了田贝。4○戚先生在文中主要参考的是《朝鲜档案》,然而,笔者查阅美国驻华公使馆与总理衙门往来照会和美国政府外交公文两份原始文件集后发现,田贝这一时段根本不在中国。其一,美国驻华公使馆与总理衙门往来照会文件,对田贝离开和返回任所的时间有明确的记载:1894 年3 月17 日,田贝照会总署:“本大臣现经请假回国,所有全权大臣事务,例应交本馆头等参赞田夏礼署理”;5○而后,他离开了中国,直到10 月29 日才返回任所,并正式照会总理衙门“所有全权事务,业于十月初一日(10 月29 日)接任”。6○其二,笔者认真核对了上述两份文件集,在田贝离开任所期间,所载美国驻华公使馆与总理衙门往来的全部照会81 件和它与国务院的每一封来往文件,发现其中的署名皆为“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参赞署理全权事务大臣田”或田夏礼的英文名“Chas. Denby Jr.”“Denby Charge”等,而与田贝无关。7○也就是说,在1894 年3 月17 日至10 月29 日间,代表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只应是田夏礼,而不是田贝。戚先生文中这几个“田贝”皆为误用。
此外,著名中美关系史学家李抱宏所著的《中美外交关系》也有同样的问题。书中有论述道:“至八月一日中日宣战。……其时驻华美使田贝亦曾报告美国政府……”8○然而,据书中注释追查原文后发现,这段史料对应档案文件的署名是“Chas. Denby,Jr.”即田夏礼,而不是田贝。9○
综上所述,在1894 年3 月17 日至10 月29 日间,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全权事务代表应是田夏礼,而不是田贝,这一时段之后则是田贝而不是田夏礼。混淆田贝与田夏礼的错误主要出现于田贝请假回美,田夏礼署理美国在华全权事务这段时间,错误形式主要是把“田夏礼”误为“田贝”;只有《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将田贝返回任所后所发的文件误为田夏礼所为,相关论著中笔者尚未发现此类错误。无论何种原因,对于当时美国驻华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相关论著和档案汇编中出现如此多的错误,而且影响至今,都是必须予以重视并纠正的。
二、不可混淆的角色
田贝与田夏礼父子二人不仅是在甲午战争的不同时间段执掌美国驻华公使馆全权事务,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对美国远东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迥异,所以,在研究美国与甲午战争问题时,必须将二人区分清楚,二者的角色不可混淆。

第一,甲午战争中,田贝与田夏礼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同。战争爆发后,田夏礼一直极其亲日,甚至还不顾美国的“中立”政策,竭力庇护日本间谍。比如在上海发生间谍案时,他就对上司的命令一再推延,直到国务卿于8月21、29、31日连续三次电令他正确理解保护日本侨民的概念、坚持美国的“中立”政策、将日本间谍移交清政府处理时,才交出了日本间谍。10○日本大肆侵入中国后,他仍然支持日本侵略。在10月23日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中,他就建议:美国不必急于调停,让战争“顺其自然地继续下去,通过干涉获得的和平是不长久的,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与世界相融洽”,直到清王朝面临威胁时列强干涉的时机才算成熟。1○田贝在战争爆发后的态度则与之不同,他一到北京就积极倡导美国调停。10月31日,也就是他接任使馆全权事务后的第二天,当清政府依中美1858年条约的相关规定向他请求美国调停时,他立即答应将该提议转达国务卿。而且,在清政府答应以书面形式向美国保证“承认朝鲜绝对独立”后,他又在当天发给国务卿的文件中提出:“这个王朝正面临灭亡的威胁,这个帝国行将崩溃。……您的调停很可能挽救这个王朝、这个帝国。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应通过电报使您给予重视。”2○11月3日清政府再次向欧美五国公使提出调停请求时,田贝当日就电告国务卿,并明确提出:“作为挽救这个王朝、这个帝国的最后努力,我建议调停。”3○可见,相关档案记载的史实是,甲午战争时期田贝积极倡导美国调停,进而操控中日议和,而田夏礼则一直极力支持日本侵略,二者对待这场战争的策略截然不同。
第二,田贝和田夏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不同。当时,田夏礼缺乏经验,又年轻自负,听不进同事尤其是使馆翻译哲士(Duncan Fleming Cheshire)的意见,还一心想使“华盛顿相信自己对使馆事务的执掌”;而哲士也对田夏礼漠视自己的建议非常不满,还觊觎署理公使之位,所以,经常向国务院的好友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写信贬低田夏礼。他们二人的对立状态使田夏礼“不愿泄露北京那些可能反映出他缺乏经验的问题。因此,国务卿不指望美国驻华公使馆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或者成熟的建议”。4○中日战争一爆发,国务卿就希望田贝能早日返回北京,取代田夏礼,掌管使馆工作。为此,他迫不及待地发电报,询问刚做完手术不久的田贝是否已经恢复到可以返回北京的程度了。考虑到田贝对儿子充满信心,国务卿在电文中还说:“你的儿子无疑会像你一样照顾好我们的在华利益”,但是,总统认为“你如果在那里,情况会更好”。5○此后不久,田夏礼违背美国“中立”政策庇护日本间谍一事,使国务卿“断定最好是让他的有经验的公使尽早返回中国”,而且他很快就把这一决定告知了田贝。6○由此可见,田夏礼在美国远东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而且,他在中国的一些行为甚至有违美国的远东政策,所以,通过他的外交活动来认识美国此时的远东政策时就应谨慎鉴别。
与田夏礼不同,田贝一直深得国务卿格雷沙姆(Walter Q. Gresham)信赖,而且,他的建议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的外交活动也都得到了国务卿的认可,与美国的政策相一致。格雷沙姆是1893年1月被当选的总统克利夫兰提名为国务卿的,当时,他认为自己不了解外交事务,不适合担任外交机构首长的职务,曾拒绝了这一提议,后来在总统和其他内阁成员的要求下才接受了任命。7○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为了制定出更为有利的远东政策,“国务卿需要国务院中熟知该地区事务的职员提供建议”。8○但是,当时国务院的远东事务专家只有艾迪(Alvey A. Adee)和柔克义两人,且与国务卿的关系都不密切,所以,格雷沙姆很少询问他们的建议,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驻远东的外交使节。在驻远东的外交官中,国务卿又认为署理驻华公使田夏礼、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驻朝公使西尔(John M.B.Sill),要么缺乏外交经验,要么对远东外交并无深解,再或者是固执己见……都不能为政府制定远东政策提供令他满意的建议;唯一可信赖的是熟知远东外交事务的故友田贝。格雷沙姆在一封写给驻英公使贝亚德(Thomas Francis Bayard)的信中就曾表示,非常希望得到田贝的“指导”,还深情地说:“我希望全美国充满着这样的人”。9○11 月初,国务卿决定接受清政府的调停请求,但又对日方态度顾虑重重,这时,正是田贝建议美国出面调停的电报使他的调停之心更加坚定了;10○美国的政策也开始由袖手旁观、纵容日本侵略转向了积极推动中日停战议和。而且,田贝在中日议和期间的努力斡旋,都得到了国务卿的认可与支持。所以说,田贝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力是田夏礼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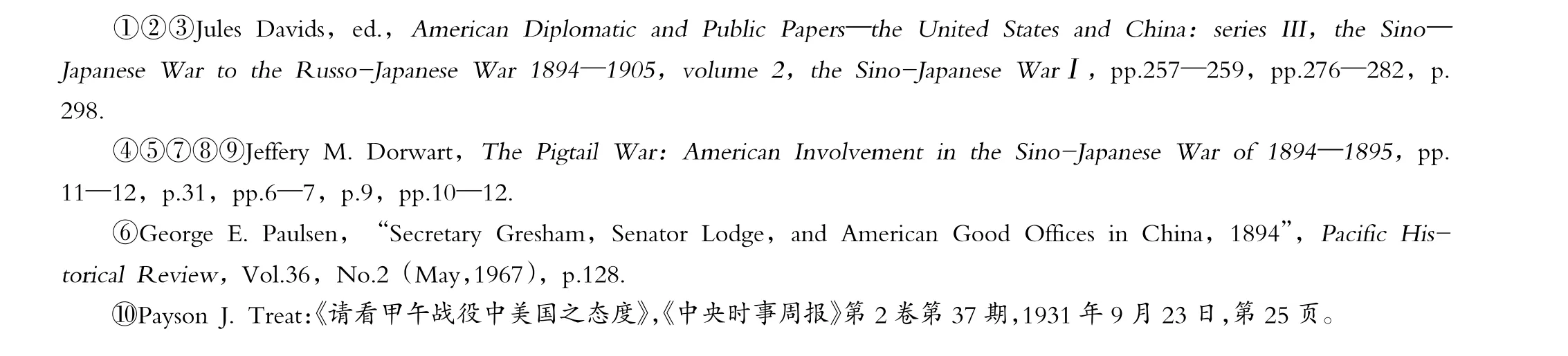
第三,田贝与田夏礼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同。田夏礼在中日战争爆发后极力支持日本侵略,并把美国驻华使领馆变成了日本间谍的庇护所,还由此引发了中美间围绕日本间谍案的频繁交涉,显然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田贝虽也亲日,但他更关心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在华贸易的发展,因此,他自1885 年使华开始就与清政府的许多要员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早在1889 年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政府准备更换田贝时,清政府就竭力抵制诸如何天爵(Chaster Holcombe)之类难以驾驭的狡猾之徒使华,1○并通过外交努力“设法暂留田贝”;2○1891 年美国决定以排华分子布莱尔(William Henry Blair)接任田贝的职务时,清政府仍希望田贝能被继续留任,3○并电令驻美公使崔国因以美国废除“苛待华工新例”为条件进行交涉,4○最终迫使布莱尔主动辞呈,5○使田贝又一次获得了留任;1893 年克利夫兰再次入主白宫后,在决定田贝去留问题上,国务卿格雷沙姆也专门向中国驻美公使崔国因询问了中国的态度,6○后来,克利夫兰总统认为没有理由更换田贝,7○无疑清政府是乐意接受田贝留任的。这说明田贝的外交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认可,自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甲午中日议和时期,总理大臣们更是极为信赖田贝,把他视为“老师”和“向导”,非常乐于听取他的建议。8○田贝本人也把帮助清政府向日本求和视为扩大美国在华利益的机会,积极响应清政府的请求,推动美国从中斡旋。在11 月16 日发给国务卿的文件中,他就表示将采取一切与自己职责相适应的措施,通过建议的方式帮助清政府,使她转向更加信赖美国。9○他不仅推动美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促成中日议和的斡旋中,还以传递信息的“居间人”角色促成了清政府期盼已久的议和之门的开启,而且,在日本破坏广岛议和时,他还曾积极地帮助清政府,尝试挽救谈判,在马关议和前后他同样积极斡旋。为此,清政府曾令驻美公使杨儒照会美国政府,“转达真诚的谢意”;10○田贝本人也收到了许多来自清政府的致谢,其中还有光绪帝亲笔题写的感谢信,同时,也有许多外国人赞誉他为远东和平所付出的努力。1○因此,可以说田贝与田夏礼在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以及远东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相去甚远。
总之,史料是“史家认识和重建过去的中介;没有史料,就无从谈及治史”。12○研究历史课题时,不仅要尽可能广博地占有史料,尤其是“原始资料”,同时,更要正确地鉴别、解读和运用史料。严耕望曾强调解读史料“不要轻易改字”,并将此视为大家都能认同的一则治史规律。13○对待一个字尚且如此,那么对史料中的关键人名、事件等就更无须多论了。甲午战争中,田贝是美国国务卿在远东政策上的倚重,也是总理衙门所信赖的和谈信息传递者,他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建议、对中日停战议和的积极斡旋,直接影响着美国的远东政策、中美关系以及远东局势的发展,而田夏礼的作用则完全不同,所以,在史料编撰和研究论著中必须将二者区分清楚,绝不能相互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