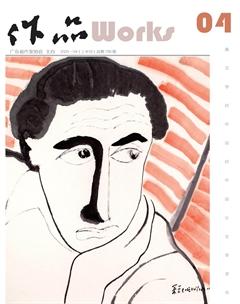大家都是手起刀落的成年人了(短篇小说)
横行胭脂
我无数次设想过用自杀来将经历的那么多慌张、孤独告诉你,以期得到你深切的回应,深切的。
转眼,我生活在衣橱里已经六个月零六天,我觉得这算另一种自杀的方式。
余小地,如果你知道我躲在衣橱里,你会生气我选择这么古怪的一个方式。
你还记得五年前我们一起去骊山春游吗?我,你,我的同事费娜,你的朋友岳林涛。我们开车到骊山脚下,然后步行上山,岳林涛说,大家比拼一下体力,今天看谁是落后分子。我们从上午十点一直走到下午三点,我还好,费娜几次三番喊撑不住。费娜埋怨我们临时组织这次徒步,她连早点都没来得及吃。岳林涛在背包里掏来掏去,掏出一根牛肉干。费娜一把夺过去,说,我饿得能吃掉一头象外加一只虎,你也不多带点。岳林涛说,这还不知是哪天落在包里的,你先看看保质期过没过。费娜说,过期我也吃。岳林涛说,我看能不能找一户人家,叫人给咱们做点饭?我们又走了很久,没有见到一户人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谁组织这个馊活动,我饿死便该谁负责!”费娜气得坐在地上,不停埋怨岳林濤。岳林涛说,现在返回也困难,那这样,你们原地休息,我去前面探探,找到人家,立马回来告诉你们,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们只能按原路返回,回城吃饭。费娜说,如果不吃饭,按原路我是返不回的,除非你背我下山。岳林涛说,你叫我怎么做都成。岳林涛把包挂在一棵榆树上,他说,减轻负重。山路弯弯绕绕,我们很快看不见他的身影了。我们就地休息。三人都喊饿。你说,哎呀,我怎么忘了榆钱叶子能吃。你摘榆钱叶子,递给我和费娜,费娜赌气,不接。我用餐巾纸擦擦叶面上的灰尘,一片一片咀嚼榆钱叶子。这种叶子带点甜味,还不难吃。我哄费娜吃,费娜气鼓鼓地将一把叶子塞进嘴里。她被叶子噎着,比画手势让我拍她的背。我们等岳林涛两个多小时,他没回来。费娜说,我们下山。我叫你给岳林涛打电话,手机在榆树上响起来。这家伙,走时忘记带手机。我们喊岳林涛的名字,山谷中传来回响。我们筋疲力尽,懒得再喊下去。你说,岳林涛保准被野猪林的猪抓去,献给它们的首领——一只大母猪。哈哈。我附和着你笑。费娜说,我没力气笑。我们从岳林涛的包里掏出车钥匙,把包仍旧挂回榆树上。我们原路返回,下山,找到车,开回城。
费娜说,他一中年油腻男,丢了没啥可惜的。你说,他一交警,应该不会迷路,说不定从另一条路下了山。
我们那天都没担心什么,因为岳林涛是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队长,我们心里都觉得他有超于我们的能力。
可是,岳林涛再没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因为我“失踪”以后,你见到过他)。
那一段日子,你蛮有把握地对我说,陈珍珠,岳林涛会回来!几年过去,你给我说,岳林涛在你梦里回来过很多次。我说,余小地,我梦见岳林涛死了。你吼我,你再说一句这样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说,怎么个不客气法?你想了想,说,离婚。我从此不说岳林涛死了。
三年前,七月的某天,我,你,我的闺蜜王芙蓉,一起逛街,我们到“舍念服装店”看衣服。王芙蓉看中一款大红裙子,一款大红风衣,一款大红裤子,一根时尚大红皮带,她刚好本命年,说穿红驱邪。王芙蓉进格子间试衣服,好久没出来。我喊王芙蓉,你快点,叫我们等你等到地老天荒啊?你说,别催,那么大一堆衣服,脱来换去,肯定费时间。那个长得妩媚娇小的女店员进去催促她两次,我听见店员说,大姐,这个试衣间还有别人等着用。王芙蓉在里面说,你叫他们等着,先来后到,我先进来的。娇小的店员出来给我们说,您的朋友心真细,一个挨一个针眼看质量。我了解王芙蓉的死性子,即便买一个拖布,也要把整个超市的样品逐一看遍,掂重量,比颜色,论优劣,得五个小时。午后,店里生意冷清下来,小店员给我们倒过好几次水,哈欠不断,我对她说,你要累你睡,我替你看店。她对我使个鬼脸,趴在收银台上睡去。她细微的鼾声感染着我们,你说你很困,想眯一会儿。你把头倚到我肩上,沉沉睡去。我打着哈欠,努力和睡眠抗争,最终失败了。
是一个古怪的梦将我吓醒。梦里,王芙蓉在葵花街来回奔跑,她扯下大红裙子,又穿上,又扯下……葵花街空空的,没有商铺,没有人,王芙蓉喊“救命”,声音砸在葵花街的青石板上,青石板一块块裂碎……王芙蓉被绊倒,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坐在飞机上,看到这一幕,慌忙从飞机上跳下来,王芙蓉看见我,惊恐万状,跑向葵花街的尽头,消失在一片葵花中,我大喊大叫,王芙蓉你出来……“珍珠,你做噩梦了吧”,你摇醒我。我恍恍惚惚,问你,我们坐在服装店里干什么?你说,哦,我们在等王芙蓉!我说,天啦,王芙蓉在试衣间!我推开你,跑向试衣间。帘子垂着,里面一堆大红色的衣服,不见王芙蓉。我大叫,余小地,芙蓉不见了。女店员醒来,和你一起到试衣间查看。你们一致推断,王芙蓉看我们大家睡得香,不忍心叫醒我们,所以先回家了。
但王芙蓉从那天起,再没出现。
有一回,你对我说,陈珍珠,我觉得王芙蓉死了。我吼你,你再说一句这样的话,我对你不客气。你说,怎么个不客气法?我想也没想,说,离婚。你从此不再说王芙蓉死了。
余小地,就是他们,在和我捉迷藏,在暗中鼓励我去寻找他们。我对你说,余小地,我知道岳林涛躲在哪里。你说,在哪里?我说,在他家的衣橱里。你哈哈大笑。你说,那王芙蓉也在她家的衣橱里是不是?我点点头。你说,你真是脑洞大开。你接着说,不过,我总想不明白他们干嘛无缘无故失踪,工作单位好, 在西城算中上等阶层,家庭也美满,究竟为啥?我说,余小地,只有你不会隐身法。你说,陈珍珠,你会隐身法?那你隐给我看看。我说,没到时候。你哈哈大笑,陈珍珠,这么多年我最欣赏你的脑细胞——永远区别于别人。我说,因此,你爱我?你说,因此,我爱你。我说,如果我隐身而去,你会更爱我?你说,肝肠寸断。
岳林涛是你的朋友,对于他的失踪,我有焦灼,有不安,而王芙蓉的抽离,带给我揪心之痛。在西城,我只有王芙蓉一个朋友。你说,不对,你还有费娜。我纠正你说,费娜是同事,算不得推心置腹的朋友。从夏天到秋天,我走在阳光下,看到地上投射的不是我的影子,而是王芙蓉的影子。我回家痛哭,余小地,我的影子丢了。你抱住我,你说,陈珍珠,没事的,你还有我,我是你的影子。我说,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影子属于个体,没有影子,这个人破碎,不完整,余小地,你是完整的,我残缺了。你说,走,我陪你找影子。我和你走在秋日的阳光下,从骊山上下来的风浸着凉意,我缩起脖子。我说,余小地,我缩起脖子,我的影子应该小一些,你看地面上,居然比你的都魁梧!你再看影子的头发,那么短,我的头发这么长!余小地仔细查看,惊奇地说,陈珍珠,我平常以为你胡说,以为你因芙蓉失踪,过于悲伤所致,没想到是真的,地上这个影子确实是芙蓉的。
费娜到我们家半个月,天天去画室里看你画画,慢慢地,她看你时,眼睛里闪着光。我知道有戏。你说,好吧,你要折腾,我便随你折腾,如果真的能治疗你的病,我哪怕牺牲自己。
我决定给你们制造机会。我没有告诉你便离家去往徘徊镇。我在徘徊镇的头一晚,梦见你们举行婚礼。费娜穿着婚纱,肚子高高隆起,牵着你的手走向宾客,你目光游离,并不望向宾客,也不望向费娜,朝一扇门看去,那扇门隐在巨型大厅的暗角,黑洞洞的。伴郎岳林涛,西服绷得紧紧的,看起来很拘束。伴娘我不认识,长得像明星姚晨,一直张着红唇,嘴巴显得格外夸张。王芙蓉在宾客中大着嗓子说话。司仪喊,安静安静!王芙蓉故意打着呼哨。费娜拉着你走向王芙蓉。你对王芙蓉说,陈珍珠,你叫我结婚的,你又来捣乱。王芙蓉说,你个没良心的,我刚刚回来,就见你和别人结婚,陈珍珠呢我问你?你说,你就是陈珍珠!王芙蓉说,我不是!王芙蓉将一杯酒泼到你脸上,一脚踢向费娜,费娜捂着肚子蹲下去……
“珍珠你别折腾了好不好?”我坐在徘徊镇一条废弃的铁轨上,听着你一连串反复的请求。我来徘徊镇一个星期,天天坐在这里,听你给我打这样的电话。黄金在天上舞蹈。这条铁轨曾不知将多少人带向远方,而现在,只有荒草蔓延铺展,伸向远方。如果燃起一把火,能不能烧到远方?
一个小男孩在锈轨上滚铁环。铁环向前走不到一圈,倒在荒草中,小男孩慌忙捡起铁环,再次往前推,铁环被蔓草挂住,男孩用手扯蔓草,由于用力过猛,他向后仰倒下去。很快,他又爬起来,继续玩游戏,还时不时用手臂擦脸上的汗水。夕阳即将落在远处的蔓草丛里。有个割草的妇女向小男孩招手,喊他,程远,回家喽,回家喽。男孩把铁环挂在胳膊上,向割草的妇女跑去。
我在徘徊镇待了整整两个月,回西城那天,正好赶上立秋。
我、你和费娜一起去观看《长恨歌》水上舞剧。我们买的是贵宾区的票,票价每张九百九十九元。费娜说,贵一点贵一点,秋天看伤感剧,容易催泪。费娜整个上半身靠在你身上,你有些躲闪。费娜说,珍珠姐你不介意的对吧?你看着我,等我做出表决。我心里一酸,对着你们点点头。你说,我看你的表情很开心!我差点说,我很心酸。你说,但愿今天两场演出能帮助到你。费娜说,对,舞台上一场,我们一场。费娜用嘴去亲吻你,我胸口一阵钝痛。剧中杨贵妃和唐明皇夜夜欢好,费娜哭,她说太感动;杨贵妃被赐死,一袭白绫在空中飞扬,费娜大声哭起来。你拍她的背,替她擦脸上的泪水,她顺势把头埋在你怀里。周围很多女人也在哭,互相递纸巾。我胸中悲伤翻涌,从支流到江海,已经决堤,可眼睛很干,很涩,流不出泪。散场后,费娜似乎依然被巨大的悲伤主宰,走路摇摇晃晃,你搀扶着她,她将整个身体落到你身上。我跟在后面。过两个红绿灯路口。你说,珍珠你先回家,我把费娜送回去。费娜说,我要住你们家。你说,今天不行。
你一晚上没回来。我整夜无眠,在两只枕头中,痛苦地思考明天。
早晨六点你走进我们的卧室,找衣服,换衣服,咳嗽一声,小声说,我去晨跑。我没吱声,假装睡得很熟。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十月二十日,我生日。你说,生日快乐!今天天气好,白天我们去凤凰谷看秋菊,晚上去“雪月”餐厅吃饭,怎么样?我笑起来,白天风花,晚上雪月呀!你说,陈珍珠,你笑起来真好看。我赶忙收缩脸部的笑肌。你叹一口气,“笑有什么不好,别整得哭没找回来,连笑也丢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吃完生日餐。你过来吻我。我将你推开。你回到座位上。
“三周后,我们分开吧”,你说。
第二天,我住进衣橱。你在西城的大街小巷贴满寻人启事。
我并不想窥视你和费娜的男女之情。我生活在橱柜里,视力却越来越好,我能透过阻碍,看到你的每天,还能看到骊山,山上挂着月亮。我能看见更多,这并不使我欣喜,并不。
我无数次设想过用自杀来将经历的这么多慌张、孤独告诉你,以期得到你深切的回应……深切的。
那天,你和费娜做爱,我听见了一切。你和费娜进屋子,我便闭上眼睛。费娜说要穿我的内衣,你居然应允!我伤心欲绝,仍然没有哭出来。费娜在衣橱里翻找,她的手摸到我的呼吸(只是她不知道)。我并没有屏住气——我为什么要屏住气!屋子里所有的空間都是我的,我才是屋子的女主人!
她的手隔着一件卫衣摸到我的鼻子,旋即缩回去。她仿佛对衣橱的兴趣不大,随便揪出两件内衣,关上橱柜。
费娜是来与我分手的。我在床上抱住她。看到墙上她的影子在摇晃,说真的,那影子在白墙上,显得单薄,凄清,孤独,我有些不忍。
费娜比陈珍珠瘦弱许多。她穿着陈珍珠的粉红胸罩、黑色蕾丝内裤,她说,珍珠比我性感?我点点头,觉得不妥,又摇摇头。
我和费娜最后一次做爱。费娜说,你心不在焉。
整个过程我闭着眼睛。费娜命令我把眼睛睁开。我没有。我看见陈珍珠在墙上的镜框里冷冷地看着我。
陈珍珠失踪六个月零六天了。
费娜趴到床底下,找出一根头发。她说,余小地,这是你从前和陈珍珠在一起落下的。我说,何以见得是我的头发?她说,陈珍珠的头发染成板栗色,我的染成雪青色,唯有你的是黑色。她又从床上找到一根黑色的头发。费娜说,这根是你和我刚才做爱时落下的,明天我将你的这两根头发送去Linda的实验室。她最近刚好搞一个实验,能通过头发,测出一个人做爱时分泌多巴胺的多少。到时候根据实验结果,我便可以看出,你与我、你与陈珍珠做爱的多巴胺数值,那么你对谁的情感如何会一清二楚。
我说,荒唐,有这个必要吗?费娜说,即便分手,我也不想当失败者。我说,其实,你们都没有失败,只有我余小地失败了,我对你们两个,深怀愧疚,我将带着对你们的愧疚艰难度日。
费娜与我分手的条件是,她必须当一天妻子——必须在我家当一天妻子,像陈珍珠一样。
如果陈珍珠不失踪,我会离开陈珍珠,与费娜结婚。
我还记得陈珍珠生日那天,我们驱车去凤凰谷看花,然后去“雪月”餐厅吃生日餐。就在那晚,我给陈珍珠说我要离开她。陈珍珠一时间慌张无措,她手里的筷子掉落在地。她俯身找筷子,我看见她的身子在抖,但她没有哭(她真的失去了哭的能力)。她捡回筷子,低头用餐巾纸擦来擦去,眼睛一直盯着筷子。我等着她对我一顿嘶吼,没想到她抬起头,看着我,笑起来。她说,好。为什么三周以后离开?我说,没有理由,觉得应该这样。陈珍珠说,你怕我伤心?你放心吧,你看,我在笑呢。我说,珍珠,对不起,不知道怎么走到今天这地步,费娜已经……怀孕三个月……陈珍珠把手伸过来,放到我手心里,说,余小地,这一切怪我,我种下因,我甘心得果。我对陈珍珠说,你原谅我。陈珍珠说,你没有过错。
“记住,今天!你演我丈夫!演成功,我们分手!演不好,不配合,我不答应分手!”费娜在电话里说。
我们约好去“雪月”餐厅,我和陈珍珠经常去的那家。老板娘说,珍珠回来没有?我说,没有。老板娘瞅瞅费娜,说,你这朋友真漂亮。费娜说,我比珍珠漂亮吗?老板娘说,不相上下。费娜说,总有个上下吧,不可能相等。老板娘说,你。费娜说,你把话说完整呀,我到底居上还是居下嘛?老板娘说,你下回来我再告诉你。费娜说,你是拉我做回头客?老板娘说,是啊是啊。老板娘转向我说,我就按你和珍珠一贯的口味给做几道菜,怎么样?我说好。老板娘转向费娜,你需要什么时令菜我去买,隔壁有家超市。费娜说,不用不用。
吃完饭,我们到我家。电梯间,恰好遇见对门胖婶。她拉着两条狗,看来是刚遛完狗回来。我看空间几无余地,示意费娜坐下一趟电梯,费娜坚持挤进去,还把我往里拽。胖婶使劲缩缩身体,仿佛在腾让空间。胖婶到过我家一次,那回她抱着一硬纸袋,纸袋里装着两条刚出生的小狗,问陈珍珠要不要。陈珍珠说不要,说到狗年自己生一只小狗。胖婶目光像透视镜一样打在费娜身上。费娜故意贴过来,双手箍住我的腰,踮起脚,要亲我。我推开她。费娜又用双手钳住我。胖婶狠狠咳一声,两条狗厉声叫起来,一起咬住费娜的裤腿。费娜无所畏惧,顺手用单肩包回击狗的挑衅。胖婶说,虎哥,仙女,你俩不许惹祸。狗听到主人命令,乖乖服从。
费娜要求:必须在我与陈珍珠的卧室里做爱。自陈珍珠失踪后,我几乎不进这间卧室。陈珍珠变成一块厚厚的乌云,压在我的头顶——她的失踪,责任在我!我觉得自己很残忍,我不该和费娜那样,不该提出离开她,作为丈夫,我没能分担她的痛苦,反而加重了她的痛苦……
我和费娜做完,我立即起身穿衣服。费娜说,你若对她不上心,不会心不在焉。她把枕头掷向我,接着又将陈珍珠的胸罩、内裤掷过来。我捂住眼睛。费娜跳下床,掰开我手指。她说,你哭了?我头一次见你哭啊,我们三个月的孩子流掉你都没哭,三个月啊,已经像只大老鼠,你好狠心……費娜哭起来。我抱住费娜。费娜用拳头砸我。我们抱在一起哭。费娜穿戴整齐,盯着我的眼睛问,我只想听你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珍珠不失踪,你真的会和我结婚吗?我点点头。费娜说,点头不算,你清楚地告诉我。我说,是,和你结婚,一起迎接我们的宝宝来到这个世界。费娜说,够了。她拉开门,走出去。(这里,我赘述一下三年后的某一天。我再见到费娜已是三年之后。那天,天气晴朗得令人不安,我们西城,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蓝的天,蓝得瑰丽壮阔,蓝得如梦似幻。我在街角摆画摊。费娜突然出现了。她喊,“嗨,余小地,今天生意怎样?”我愣怔。她拍打我的肩膀,“问你话呢,生意好吗?”我回过神,“一般。”她说,我偷窥你可有一段日子喽,感觉你很勤奋地生活着呀。我说,“我每天用塞林格的话督促自己,‘你最好让自己忙起来,伙计。只要你转身,该死的沙子就会落到你身上……”她说,余小地,如果你能保证心脏没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如今,我心脏能承受万吨重力。费娜哼了一声,说,陈珍珠——回来了!我的血液一下子拥挤到心脏,呼吸急促起来。费娜说,天啦,你眼睛瞪得要裂开,充分证明,你心脏没有那么好,我和你开玩笑的哦。我很生气,你拿陈珍珠开什么玩笑!费娜说,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我说,与珍珠无关的事,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懒得听。费娜说,这个人很有意义哦,仅次于陈珍珠!费娜冲街角喊,你出来!我看到岳林涛向我走来。我嘴巴张得大大的,喉头想喊岳林涛的名字,却发不出声。费娜说,这位岳林涛先生,现在是我丈夫!我说,这是梦吗?岳林涛这些年你躲在哪里?岳林涛说,你猜。我说,陈珍珠说你躲在衣橱里。岳林涛哈哈大笑,就你家珍珠能想出这样好玩的事情。我说,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岳林涛说,随上师闭关多年。我说,我怎么从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岳林涛说,每个人都是一堵墙,别人难以看穿。我一下子轻松起来,我想陈珍珠也许会在某一天像这样突然出现。费娜说,余小地,别太悲观,你看,岳林涛能回来,陈珍珠也会回来,包括王芙蓉,也会回来,她们,都会回来!)
终于有一天,余小地敲敲衣橱的门,说,陈珍珠,你出来,大家都是手起刀落的成年人了,你这样玩有意思吗?你给我出来!我在衣橱里面,心怦怦直跳,我等着余小地拉开衣橱的门。余小地没有拉开门。我继续生活在衣橱里。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