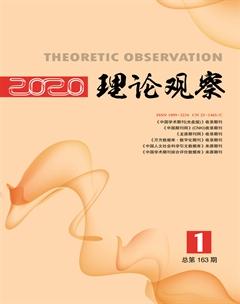从《嘉靖遗诏》看嘉靖帝生平
王敏敏
关键词:嘉靖;遗诏;大礼议;建醮修道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1 — 0102 — 03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武宗崩,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在慈寿皇太后(武宗母亲)和大学士杨廷和商议下,遵循《皇明祖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的原则,由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承大统。朱厚熜是宪宗之孙,与武宗朱厚照是堂兄弟关系,他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嘉靖帝。从即位到嘉靖四十五年(1567)皇帝驾崩,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五年,仅次于其孙子明神宗万历帝,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明后期皇帝多疏于政务,与大臣联系减少甚至不与大臣沟通,如明神宗虽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但避于后宫,不理政务。对于嘉靖帝的评价,也多认为其后期避居西苑,任用大权臣,但实际政事上权柄未移,仍握帝手,改变了我们对嘉靖帝一贯的认识。通过本篇文章希望对嘉靖帝有一个更清晰的不同于史书上的认知。
一、《嘉靖遗诏》
遺诏是皇帝在驾崩后给后人留下的的遗言、遗书,主要是对自己一生的行政得失的总结,或是表达了对后人完成自己未竟事业的期望。《嘉靖遗诏》是明世宗朱厚熜的遗诏,但并非明世宗生前所写,而是由内阁首辅徐阶、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在皇帝崩逝后共同纂写,以世宗自己的口吻来反省生前的错误,突破惯例,增加了纠正弊端的内容,借以确定国家大政方针。这份遗诏对当时的明朝所起的影响可以在《明史》的徐阶传中看出,“未几,帝崩,阶草遗诏,凡斋蘸、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1〕563徐阶为世宗所拟的遗诏中将世宗时弊政革除,因“大礼议”而获罪的臣子恢复其名誉、自由,对已逝去的则加以追封;精简丧仪,遵循祖制;臣子藩王不得擅离处所,以稳定朝政;劳民伤财之事务全部停止,以重获民心。《嘉靖遗诏》所起的作用要比世宗登极前杨廷和所拟的除去武宗时弊政、革故鼎新的登极诏书意义更大,同时更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认识自己错误并善于改正的皇帝的印象,从后继的统治者角度上说,更利于增强百姓对于自己统治的认同感,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在明代关键历史时期所起草的遗诏发挥了挽局面于既倒的重要历史作用。①
对于遗诏这种为尊讳的文书,即使记载皇帝的不当行为,也会只是经过修饰的或者是加以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难以展现。并且一般的遗诏都是对于皇帝的一生事迹的总结,多为恭维之语,而像徐阶这般书写皇帝在政务处理上错误之处的是极少数,但这有一个好处是对于后世的研究能更加公正的认识嘉靖帝这个形象。
二、《嘉靖遗诏》中的嘉靖帝
对于明代中期研究的相对薄弱,使得许多论著人云亦云,对于嘉靖帝认为其是个“混账皇帝”,昏庸、专横和残暴。①但不可否认的是前期的嘉靖帝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并且坚持己见的人,在入京即位时就曾就从东安门(藩王与臣子进出的门),还是大明门(天子进出的门)进入皇城与臣子有了争议,嘉靖帝以武宗遗诏中“以宗人入继大统”来与臣子说明自己嗣皇帝位而非太子位,拒从东安门入,以坚守祖训来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
而第二步的胜利便是嘉靖朝最有名的便是“大礼议”了,这在遗诏中并未直接提及,但可谓是贯穿嘉靖朝始末。这一事件从嘉靖元年(1521)四月“命礼臣集议兴献王封号”〔1〕216七月张璁言“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立兴献王庙于京师”〔1〕216开始,在皇帝和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众臣子中展开。这件事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献皇帝庙号睿宗,并奉睿宗神主祔太庙,跻武宗上”〔1〕228以嘉靖帝的胜利结束,对嘉靖年间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间,因反对尊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王为“皇考”而获罪受罚的臣子多达一百八十余人,其中多是文臣与言官,有的官员甚至被杖打而死,牵连甚广。这一做法触犯了“不可杀言官”的规定,并且深得民心的首辅杨廷和也因此而被皇帝排挤出势力集团,削职为民。嘉靖帝借助此事,将武宗所留下来的旧势力排除于朝堂之外,将自己所培植的新生势力扶植起来,在统治集团中站稳了脚并且成为了新的掌握实权的势力集团,真正的将权力握于手中。
从这两次的胜利中,可以看出嘉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谋略的人,他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正如对待大礼议这件事,在开始提出尊生父为皇考时,由于自己还未站稳脚,没有自己的势力,受到朝臣的反对后,暂时的妥协;但在他统治地位已经稳定,并且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团体可以和这些反对的臣子较量时才再次提出,即使持续了好多年,但仍坚持要尊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考。这除了体现了嘉靖帝的的谋略与才干外,还体现了对于亲生父母的孝。在古人观念中,孝是最为重要的品质,历史上孝顺的皇帝也很多。但像嘉靖帝一样,在其后四十余年时间里“……享国四十余年追慕献皇、献皇后如一日,每遇时节忌辰,侍臣窃窥,圣
容惨怛,承享精虔,无不泣于下者”〔2〕,如此重孝的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从大礼议后,嘉靖帝提拔了一批顺从自己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正如遗诏中所提及:一改武宗时政治、社会混乱的状态,革除弊政、减免赋役、广开言路、惩治佞臣江彬等;禁内监干预政务,避免再次出现武宗时“八虎”作乱干预政务的现象;勤于政务、整顿边防、清除外患,使朝政为之一新。从这些行政政策中可以看出嘉靖帝是一个很有才干、有自己想法的人,并且对明政局产生了重要作用,而“过求长生”,对于方术的沉迷使得嘉靖开始放松。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在安逸的环境下开始松懈,皇帝也是如此,社会安定,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也减少了,看到国家被自己治理的一派繁荣,便开始享受了。正如《嘉靖遗诏》中所写,嘉靖帝唯一的追求就是修道,想达到为尊者最想要的长生不老,于是便开始“渐兴寺观,崇奉诸教”“乾清诸处各建醮,连日夜不绝”〔3〕783为方士加封道号,敕建真人府,甚至进入各部院当官,对于修道的沉迷引起了臣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嘉靖十八年(1539)九月,太仆卿杨最因谏言“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3〕789而下狱,后死于狱中,这样的大臣不在少数。嘉靖二十一年(1542),便出现了宫女因每日早起采集修仙所需的晨露,不堪其扰,加上时常遭受皇帝的欺凌虐待,而准备造反欲杀死皇帝的“壬寅宫变”。历史上皇帝压迫宫人的事不在少数,但能逼得宫人不顾生命而造反的就只有嘉靖帝一个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皇帝后期因为对道教的沉迷的昏庸。而从这件事后,嘉靖帝“自是移御西苑,不复入大内矣”,认为自己是因为修道,仰赖天地鸿恩,才可以让自己躲过宫人的谋害从而更坚定修道的信念,也是从这开始进入了我们通常意义上了解的明朝历史上严嵩掌权的黑暗时期。
嘉靖后期,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侵东南沿海,造成了极大破坏;北面的俺答汗不断寇边,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南倭北虏”不断,战事的频繁失利使得在边事人员的任用上也是调动频繁,这又导致将领对于作战情况不熟悉而又使得作战困难重重,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政者嘉靖帝并未对战事的重视。皇帝沉溺方术、大兴土木所造成的靡费和频繁作战的支出使得财政负担加巨,国库衰微,大伤民力。所以在《嘉靖遗诏》中徐阶借皇帝口提出在丧事的办理上依照祖制,而未大规模操办,除了稳定朝势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是对于劳费民力的一种缓解。
嘉靖帝在位时,除了在嘉靖十八年(1539)立第二子朱载壑为太子且在其夭折后再未立过太子,而拒立太子的原因是相信道教宣传的“二龙不相见”,使得父子关系冷淡。对于接班人的培养上也是很不积极,到了嘉靖帝驾崩后只有一个裕王健在,且之前也未受过要成为下一任统治者的教育,种种原因使得继承者质量不高,这不得不依靠阁臣,而万历皇帝在当政时拒与臣子联系,自己也不理政,可以说是自掘坟墓。这一系列所作所为都使明朝开始由繁盛向衰落的过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明亡始于嘉靖。
三、对嘉靖帝的认识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编写的《国榷》中这样评价嘉靖帝:“凡新主之诏,多旋行旋格,美意不终。惟世宗初所兴除,靡不力也,革锦衣等诸衙内监局旗校工役,至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减粟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是社稷之长利也,无论其他矣,新都于先帝为補衰,于今上为纳牑。自三杨李文达后鲜见焉。” 〔4〕322谈迁在他写的史书中给予了嘉靖帝很高的评价。除了这些私人编修的史书,官修的史书中也对嘉靖帝进行了很贴切的评价。《明史·世宗本纪》赞日:“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1〕250《明世宗实录》中载“陛下嗣登大宝一月以来,用人无不当,行政無不宜,群小远斥,积弊一清,天下闻之,皆忻忻然,有太平之望,……尧舜之圣复见于今日。”〔2〕115在由清人和明人所编的史书中都给予了嘉靖帝很高的评价,或许从统治者角度来说嘉靖帝虽然任用了奸臣,但关键在他仍能把权力握于手中,大权不旁落而威柄在御,这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了。
对于嘉靖帝这个人的认识,不同阶级的人有产生不同的观点,或褒或贬,都不能简单的将其说明。不可否认的是他是前期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有被世人所尊崇学习的性格:孝,为尊亲生父母不惜与臣子抗争十几年;勤,勤于政务,亲决内则,每旦自问省;仁,世宗对初人户隐匿诡称,大户逃匿将负担压于小户,使“逋租日多,里甲日耗”,下令以实现人户一百一十户为准,不准以诡名女户和逃绝人户充数,禁止皇城内假冒皇亲、太监名义私揽财物,望能减轻百姓负担,既有政治谋略又关注民生。但他也有许多人性的弱点存在:心机深沉,善变多疑,玩弄权术,对于君主来说心机深是必要的,让臣子不能随意揣测君心,少些奉承。但多疑会让君主不轻易相信臣子,在解决政务中增加许多麻烦。
不可否认嘉靖帝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虽居西苑二十多年,但对于政局一清二楚,任用严嵩,可以说是给自己找了个听话的“代言人”,而严嵩也因为能解帝意,迎帝好而被提拔成为皇帝手中一把剔除异己的刀。严嵩在后期所谓的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可以说嘉靖帝都知道甚至默许的,目的是在臣子中树立一种威信,并借此将打压不听从自己命令的官员,实现权力的平衡。这样的好处是一旦人们的意见达到沸腾之时,可以用一个臣子的获罪而得以缓和,相反自己还不会有任何坏罪名,史书记载时可以说是被奸臣所蛊惑。正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臣子上谏而被罢官,此前多有臣子弹劾严嵩,而"上庇大学士嵩,嵩不能被治罪而上折臣子被治罪",甚至帝以传位给裕王而退居西苑来要挟臣子“莫敢言帝玄事及嵩罪”,而后严嵩却因一次上谏就被治罪。这么大的态度转变及严嵩当权二十余年而一纸圣意便能将其倾覆,都可以看出实权仍握于帝手,“故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2〕906而人们眼中的权臣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一枚君主欲加强君权的"烟雾弹"。
对于一个人的认识都很难正确全面,更不用说是对于一国之君了。嘉靖帝和大部分的人一样,有其可被人学习的一面,也有自己所真心所追逐的东西就是道,从日复一日的追求某件事上有,他的恒心值得夸赞。嘉靖帝本人也没认清自己的身份与责任,使得这份坚持是错误的,因为他身份的特殊性,他的作为又更加引起人们的评论批判。对于人物认识应结合时代背景和身份特点,不能单纯偏信一家之言,我们所借用的资料也是经过人加工、掺有个人情感的,这就必须要求我们会分析和使用资料,可能达不到百分百的真相,但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去接近最真实的历史,追求最接近真相的历史。
〔参 考 文 献〕
〔1〕徐阶.经世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5:439.
〔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63;216;228;250.
〔3〕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15;906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783;789.
〔5〕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322.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