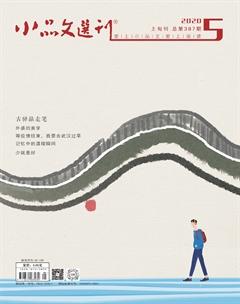假如没有那场大雨
张世勤
韩国电影《寄生虫》从剧情上说,应以“那场大雨”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大雨之前,豪宅的主人朴社长、朴太太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多惠和多颂外出度假,为小儿子多颂过生日。而留守在家的女佣忠淑毫无顾忌地招来丈夫金基泽、儿子金基宇和女儿金基婷,主人一般地尽情挥霍着短暂“上流社会”的生活体验。其实,在金家四人中,忠淑是最后一个进入朴家的。在此之前,先是基宇受朋友敏赫之托接替出国留学的敏赫,为金家女儿多惠进行英语辅导,女主人朴太太正苦于难以管教性格古怪、有点印第安控的小儿子,基宇便趁机推荐了基婷。然后,基婷设计陷害了朴社长的司机,让父亲基泽成功接替。然后排挤掉了原先的女佣雯光,忠淑马上趁虚而入。至此,原先没有工作的金家四口竟全部在富人朴家找到了工作,且对主人成功瞒过了他们本是一家人的真相。这一刻,与其说豪宅是朴家的,倒不如说是金家的。基婷一边在宽大的浴室洗澡,一边看着电视,还一边喝着上等的饮料。基宇四仰八叉地躺上舒适的大床。忠淑更是倾其美味,制造出了空前的盛宴。一家人面对窗外宽阔的绿地,饮酒狂欢,大快朵颐,兴奋和理所当然将应有的罪恶感完全淹没。这家人的“寄生”已足够“生猛”。
但随着雨夜中前任女佣雯光的到来,更加触目惊心的一组“寄生”被揭开了面纱。朴家现有的豪宅,朴家并非原住,原住人是南宫贤子。豪宅建造者为躲避有可能来自北方的进攻,而建有隐秘的地下室,地下室有着曲折仄长的甬道和应急的生活空间。但她在过手房产的时候却并没有让新主人知道这一切,而遗留下来继续为新主人服务的女佣雯光,便借机将开办台湾古早味蛋糕店倒闭、欠债被追的丈夫秘密安置了进来,这也就是女佣雯光的饭量一人顶两人的原因,因为她得不断地偷出东西,送往地下室的“寄生”者。她之所以雨夜赶来,就是趁着主人不在,去看看自己丈夫的死活。她所谓的走得急忘带一样东西,忘带的东西并不是东西,而是她的丈夫。这对“寄生”的夫妻竟让全家都是“寄生”者的金家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由此,朴主人家小儿子的古怪原因也便露出了端倪,所谓一岁时得病,不过是多颂一岁时在夜晚的餐厅遇见过从地下室爬上来找东西吃的雯光丈夫,那扇启动的暗门不用说当场把他吓出了白眼。所以他那些极具现代性和印象派手法的涂鸦,其实就是模模糊糊的雯光丈夫的影像,而每幅画右下角都有的让人倍感莫明其妙的标注,也不过就是那扇连通地下室和厨房的暗门。朴社长朴太太虽不得原因,却隐约知道只要离开别墅外出过生日,儿子就会开心。但一场大雨,让主人提前结束了行程,提前八分钟打进来的电话,让两组“寄生者”的对垒变得更加糟糕。也许,富人家花钱雇佣,过着优渥的生活无可非议,但他们一旦离开佣人,日子仿佛也是一地雞毛,一天也过不下去。从这个角度说,富人是否也是在“寄生”。
至于,房子的原主人有可能是日本人,新主人是与美国打交道的电子产业翘楚,女佣雯光一段模仿北方电视播音员的桥段等,以此推断影片其实是在讲述韩国历史,先是被日本殖民、然后南北不和、后又“寄生”美国的这一说法,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导演赋予“寄生”的肯定不只是生存问题,而是借由“寄生”这一概念,持续向社会和人性的深处扩展和挖掘,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让人又想笑、又想哭,无法赞美、也无法批判,必须沉思、却又抓不住理不清的尴尬的艺术文本,这或许也正是影片的致胜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是地上、半地下和地下三类人交集的故事。一场大雨,对地上来说,可能带足诗意,但对半地下来说,便是一场灾难。基泽一家,基本处于全家失业状态,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半地下,抬头就能看见近在咫尺在自家窗外撒尿的醉汉,全家人早已浑身润足了低层人身上所独有的发霉味道,但他们却毫无规划,最大的智慧都全部体现在低层人缺乏法理和尺度的小聪明上了。如果说,基宇为能顺利成为有资格的家教而伪造学历还有情可原,甚至为妹妹也能成为家教而向女主人谎瞒身份也或可理解,那么,妹妹基婷借朴社长司机送其回家,半路悄悄脱下内裤,使得司机不明所以便被解雇之事,便让人可恨。而且,随后当听说女佣对桃绒毛严重过敏时,一家人一起策划,相互配合,成功实施了对女佣的排挤。这其中,父亲和女儿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当在地下室两组“寄生”者不期而遇互握把柄时,也许正是他们可以互相接济和平解决事端之时,但却发生了不该有的惨烈冲突。女佣雯光的死,也直接导致了其丈夫走上地面,以刀相向。宇婷身亡、忠淑与雯光丈夫死拼之时,朴社长捏鼻不愿闻他们下层人身上那股发霉味道的举动,又瞬间激起了基泽的愤怒,从而失去理智。这是一起由荒诞的社会现实引发的人性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之劣才是人的最大“寄生”。
因此在我看来,有没有那场大雨都已经不重要。即使那场大雨不来,即使根本不存在地下室的事,单是一家四口,以不明身份进入到另一个四口之家中,即便是互相“寄生”,表面相安无事,也已经足够荒诞和恐怖的了。
人性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和“寄生者”,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跳不出千疮百孔、撒风漏气的这只人性篮子。一切社会秩序和文化文明,终究都是要在与人性的不懈搏斗中艰难前行!
选自《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