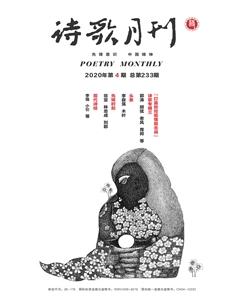写给一切不可预见的诗
尚兵的探索给了我们关丁现代诗写的新启示。
如果你初次读他的诗,可能瞠目结舌。然后,当你尝试全身心投入地阅读时,那么,一种可能是你接近诗的起点,耳日一新,因为,你此前绝不可能见过类似诗。另一种可能则是,你仿佛眼望着体量硕大的长臂猿在词语和意义的枝头跳荡来去,你尚未明确意图时,它便一晃消失了。
我们试读一首他的《作业练习》:
“放心遵从晃眼棉花地……亮脚丫子、午睡敬大人”。这首诗在词语从林中映射出模糊的意象:零碎的农村生活记忆,譬如棉花地里单调地摘棉花,频繁回头看是否有遗漏;纤细的粉尘在午后的空气里飘动,并不断刺激着鼻腔;孩子们捉鱼要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人威逼下午睡……然而,这些在我们想象中呈现的场景,却在具体元素组合中变形,你面对“遵从晃眼棉花地”“需……练习”“亮”“敬”这些表达时,内心必然会动摇。因为,我们依据习惯捕获到的意义,事实可能完全不是那样!
我们早习惯丁熟练地推测剧情发展,并沾沾白喜,仅仅是基丁生活逻辑性吗?还是一贯就想当然,无意间走在愉快的集体媚俗道路上?
再来读这首《纸飞机的冲动》,“捣衣惜力气……除掉‘于拉于还有‘一脸茫然可惦记吗?”在这样的诗中,如何找到你要的解释?显然,非常困难!因为尚兵操持的几乎是祝由之语。对尚兵的诗作表示不解是最正常不过的反应,那些暗藏深意的词语狂欢,足以摧垮阅读自信,敲响我们写作和阅读习惯的丧钟。 面对这样的诗作,我们很容易置之不理或矮人看戏,而把悠长自由之至的诗歌史抛之墙外。诗歌史早已告诉我们,任何时代出现的新诗都包含“非诗”成分,几乎没有哪样东西没被作为非诗元素质疑过,也几乎没有什么是诗歌不可具备,抑或必不可少的。一切过去的“非”都在融入未来新诗的短暂范式中,而部分人执着不放的“是”在道路上可能已被丢弃。
尚兵的诗可贵地呈现出反诗意和意义碎片化的倾向,甚至反意义倾向。这使他的诗在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批评支点。但尚兵的诗歌价值恰好因此绽现:本能、自发,甚至无理,充分具备现代美学意义上的可挖性。
他在诗歌中随意斩断日常语言的藤蔓,又重新拼接,在词语间进行平衡写作,构建平等词语关系。不同时空场景的碎片,在读者无法预见的前提下,与本源场景的意象和结构不断发生交错互换和形变,过去可有可无或可替换的词语变得独一无二,它们之间“互喻、对立”,在尚兵赋予的尊重下向所有方向上迸溅耀眼的光芒。没有理所当然的客观,只有词语激起链式反应后在读者那里产生宽广的诗意与无限时空可能,或许这正是尚兵的指涉目标——破坏常规组合,形成相互指涉的陌生而复杂的“气场”,增加诗歌的张力。
尚兵的诗并非一般的词语犴欢,而是有着深刻自律,是思想加速度跳跃,又驯服地收拢在规整的形式中,从重构词语关系到关注回环拓扑,高度严谨地服从丁某种星空般的秩序。这是天赋使然,才能写出这种罕见的格律。
在我们普通的阅读经验中,词义与秩序早已如伦理律法般存在,这是我们眺望世界的窗栏,但它也是拘同我们的牢笼,是最难敲碎的果壳。五四先贤做白话文写作尝试,正是基于這种模糊的理解。
尚兵在他的诗学随笔中,清楚地表达出对世界不解,试图从语言着于来认识世界,认为语言作为整体而存在,每个词语都有自身发展史,都可以赋予新意……对探索者尚兵而言,最重要的使命是对语言与此在关系的深刻挖掘与呈现,是怀疑与批判、反思与重构的漫长行旅。
尚兵诗歌也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虽然他有卓越的结构语言天赋,能构建旋转的语言星云;但却完整地漠视了读者感受,不容易在阅读者那里引起真正的回声。
另外,在诗语言的流动中,刻意性仍然存在。涂抹式的写作理念支点还不够坚实,支撑的体系化写作架构还未成形,可通过深入研究现代音乐、绘画、装置等艺术形式,汲取有益的养分。我相信尚兵会找到那个忽隐忽现的虫洞,快速完成诗探索的阶段性旅程。
哪怕最极端的探索者,也不能彻底远离时代。在《清爽恢复原形》一诗中,诗人回到过去熟悉的场景中,黎明狗吠,泉水叮咚,树木葱茏,池水无声……这是诗人内心同守着的世界。世界早已改变,只有最纯粹的诗人才坚信诗歌是对世界的有力对抗。而这对抗,并非那秦时桃源。
我们立身丁复杂多元的当代,也只有当下,才是诗歌写作最真实的羊水。
西边,诗人,生于1970年代,作品发表于《诗歌月刊》《安徽文学》《星星》等刊物。曾获曹植诗歌奖、紫蓬山诗歌节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