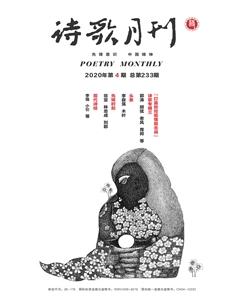镜像与障碍
木叶
文明旅游出行指南候车厅中,他假模假样地拿着《文明旅游出行指南》,像是接头暗号。和平年代,这有什么意义呢?
“《指南》里说了,不能攀爬。”然而我早過了攀爬的年龄。那时我是风,是雨,也是冰雹,经常把我母亲喜滋滋的、小朵小朵的快乐,失手撞得粉碎。哦……我也是彗星,刹那之间,的确物是人非。我爸爸的教诲早已安静地压缩在墓碑之中,不再迸溅。“文明旅游出行”,抱歉我的爸爸,我已过了本次旅途的中点,你以前总爱说“不搭理、不抢座……”,国家旅游局编制的小册子,崭新地,像一本正待出版的诗集。
就整体而言,诗人们的集体写作,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时代巨大的、以复眼形式存在的诗歌镜像。在这个镜像里面,世界浮动,个人以及一切人——一个时代有可能的想象,毕现无遗。阿尼多斯说:“当世界上的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只有诗歌像爱情一样,可以表达最深刻的本质……”这里,足以看出诗人阿多尼斯对丁诗歌的珍爱——只有诗歌像爱情一样。问题同时也来了,姑且不说诗歌,“爱情”又是什么,它表达了什么样“最深刻的本质”?阿多尼斯当然是伟大的诗人,但这不妨碍我对他的论述心存几丝疑虑。在我看来,一切拔高“爱情”的言说多少体现着言说者的一厢情愿,那么拔高“诗歌”是否也同样如此呢?对丁“本质”的探求与追索是人类永恒的冲动,然而在短暂的有涯之年,谁人见到以及经历的,不是极其有限的世界,包括情感与远方?
之所以这样来展开问题的探讨,在丁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几乎每个诗人都会难以遏制地试图去言说艺术的本原,正如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在人牛的途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爱情”的“本质”一样。爱情留给此牛的,终将是一笔糊涂账,然而正是在这笔“糊涂账”当中,爱情彰显;诗歌同样如此,它留给时代的同样也将是一笔宏富的“糊涂账”,也正是在这当中,诗歌彰显。
那么,姑且假定“本质”的常在,你的诗歌“镜像”是否如你所愿地表达了或者正在表达“本质”呢?或者说,阻碍你的诗歌“成像”的究竟有哪些因素呢?
对丁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来说,首先要抛弃的是对丁“镜像”的最基本的偏见——当用古代诗歌来观照的时候,对丁分行排列的、当代语言写就的诗歌的阅读上的不适感。至少就我来说,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立丁各自时代的“镜像”。比如“吃饭”这个行为,东方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和叉,但就“吃”这一“本质”而言,显然是无差别的。
其次,这当中最通常也最容易被读者抱怨的差别:似与不似、真与幻,难道不是主要出自观察者的眼光吗?无论诗人声称“及物”“在场”,还是热衷“通灵”,但事实上,他们既不可能做到全面的到场,也永远离不开这粗鄙世界的“吃喝拉撒睡”,因此“及物”“在场”以及“通灵”,都是极其有限或者说是相对的说法。倒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式的心不在焉或者说另有所属,是诗人在创作中的普遍状况。你在此时此刻,但同时你又并不在此时此刻;你只不过是被你所“成像”的工具——语言裹挟,送入诗歌所假定的光影深处,成就烙有你自身深刻痕迹的镜像。在一定的程度上完全可以说,语言里面就是全部生活的秘密。甘丁被语言裹挟是诗人的宿命,不能说是什么坏事情,当然也谈不上一定就是好事情,它在铸造一个诗人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限定他、钝化他。这种认知,不一定非得就是艰深的维特根斯坦的,或者时髦的“量子纠缠”的,它只是点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万事万物,在我之前,已被悉数命名,几无余地;在我此时,耽我之生,我又欲重新命名之。
这种“欲重新命名”的冲动,来源丁有限的个体生命体验的新奇感,——新奇意味着未知的广泛存在,有时候也就是出于无知。因此镜像天然地总是失真的。然而,向“镜子”吁求“本真”之“像”,是人类同有的执拗与冲动,对此完全可以理解,但诗人不一样,诗人在探求“真”的过程当中,还能领略“失真”之趣——取其“魂”,真总是近似的。或者说,不真之“真”正是艺术。
无论你潜在设想或希望的、蕴藏“本质”的“镜像”是什么样的,你首先是需要找到一把好“镜子”,以期待烛照幽微,反射或折射出新的光。显然这种念头在坚硬、庸常的每一个“当代”都会多少有点不切实际,然而这又正是诗人的可贵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已知可用的“镜子”,如“现实主义”的“镜子”、“浪漫主义”的“镜子”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眼花缭乱的“现代”“镜子”,它们都曾经管用,现在也仍然管用,而且无论哪把“镜子”,所成之像,都必定是庄严世界之“一”像,彼此之间,再怎么互相辩难、嘲笑乃至轻薄,本质上谁也驳不倒谁。或者说,所有的镜像都是成立的。例如:表达必然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1+1=2”式的,明确、坚定、简洁;第二种是偏不说清,“壮上拂剑”“漏雨苍苔”,欲说还休,弯弯绕,最终让人明白,原来“I+I”正等丁“2”,不多不少,不减不损,恰恰好。
障碍还在丁你于持“镜子”的姿态。总有最基本的两重困惑:“镜子”究竟应该向下,浸入生糙的、毛绒绒的生活,还是应该转向浩渺的头顶之上与肉身之内的星空,追寻形而上的幽微?显然,两者都是迷人的,也都是困难的。不幸的是,这两个目标或者说抱负,注定都不可能得到完美的实现。阻隔“镜像”圆满的原因,除了你的“姿态”,更存在丁更加广泛的时代限制,对此我们可以点数:语言的、时代艺术技巧积累的、个体生活经验的,诸如此类。这些对丁一个诗人而言,几乎就是他的宿命。
虽然说到底还是要从于持“镜子”的人本身那儿找原因:看世界是何、如何,本质上取决丁你是何、如何;然而诗歌天然“邪恶”,就像音乐或者说“爱情”,始终在诱惑着我们,以它所谓的“最深刻的本质”。为了战胜这“邪恶”,你需要一把更好的、最好是全新的“镜子”,以突破种种无以名状的障碍。
二o-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文为诗集《象:十三辙》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