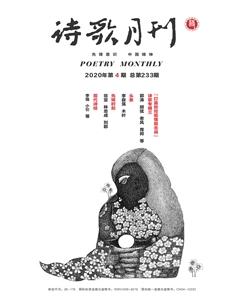主持人语1

沈凡试图在诗歌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自述体系,平缓的语调、碎片式的事件和庄谐杂陈的内容组成了其自述功能必要的结构特征,在种种的叙述期待中与叙述的可能性之间来达成自述上的诠释意义,譬如在沈凡的《消失》一诗中:“所有的这些,或者那些,你无可阻拦/陌生的新事件像杜鹃口中那抹殷红的雀舌/纤美而简洁/你要沿着它走向风烟涌起的远方/许多东西会因此丢失,会不欢而散/而它们却一直隐匿在你低低的眼睑”,沈凡采取倒叙的方式,从“所有的这些,或者那些”留下悬念,直至叙述视角中的你、杜鹃、远方、它们等客观对应体次第出现,才完成了自述上意义上把所意指的“内心客体”同叙述的事件、情节和情景相统一,让碎片化的叙述材料驯服并屈从其自述的意义结构中。
林南浦的诗歌叙述方式是把已经确定的叙述材料再还原为“真实化”,擅于把叙述的材料作为核心单位的基本事件,突出叙述者的确切的行为或者状态,诸如在《季夏寻村谣》一诗中写道“正午的天穹,如冒着热气的锅盖/扣住了沔西二十三村,共有三乡”,在《野塘倾覆录》一诗中有“挖掘机勾掉沿塘周边的铁匠铺/茶馆,屠猪屋和废弃的老瓦房/货车抢占制高点,卸下黏土/填埋野塘。野塘中的生物被迫接受”,诗歌中的沔西和野塘作为叙述的地理标记,如实地呈现出作者的意图,古人云草木有生而无知,林南浦以写实的手法让物象的出现不显得呆滞,反而有气韵,这点是值得嘉许的。
对比两位90后女性诗人徐晓和赵希的诗歌作品,会发现徐晓的诗歌有表达上的直接、粗犷和决绝,“明月啊,它从不为我翻涌的潮汐/投下赞美的词汇/也不为我赤裸在刀锋上的深情/洒下动容的眼泪”(徐曉《明月高悬》),“我陷入了爱情,像发起一场高烧/你坐在我的对面,来不及成为一粒解药”(徐晓《隆冬》),情感的溢出、流淌与激荡甚至有伊蕾式的歇斯底里,编者赞成徐晓这种在诗歌上的“野蛮专横”和不受约束的情感介入方式。赵希的诗歌显得精巧、细腻,她写树耳、秋英、豌豆花,写春日和悲伤,看似为小感觉的抒发,实质上有着纯朴的情愫来维系着诗歌的空灵与隽秀。
——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