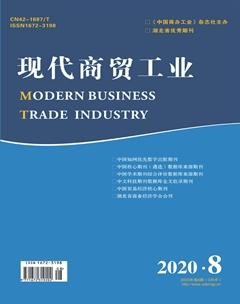从“被遗忘权”看个人信息保护
朱嘉玮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云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创新,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个人数据泄露,信息处理主体滥用个人信息带来的威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必须受到重视,因此围绕被遗忘权来讨论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关键词:被遗忘权;个人信息;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8.075
1 被遗忘权的立法背景
被遗忘权是一种保护个人信息的权利,2016年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将其确立,被遗忘权的概念正式推出。2017年11月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室内稿)》,在部分学者中征求意见,在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是赞成这样的立法举措的,只有在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大的立法背景下,被遗忘权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有一部分学者是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人格权在民法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只能在民法中碎片化的表达;二是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类型不同,不是独立的民事权利,理由如下:
我國之前的立法不重视人格权,比较重视物权,人格权在民法中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是因为我国之前的主要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物质条件相对匮乏,发展生产是重中之重,而之前说到的有的学者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因为人格权在民法中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只能在民法中碎片化表达恰恰是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由,正因为之前人格权没有得到重视,现在的社会发展对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对于人格权仅仅放在宪法之中或者《民法总则》象征性的规定中,只是起到一个宣告的作用,而是要进行具体的规定,使其能够切实的保护公民的权利。
有些学者认为人格权不同于民事权利,其本质具有社会公共秩序属性,因此,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在逻辑结构以及制度体系上,是缺乏基础和没有灵魂的,其规范选择的立场或价值判断也就会有很多变数。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人格权应该属于宪法调整范围,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004年,我国对宪法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此,王利明教授认为,宪法所规定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是民法上人个制度发展的基础,但并不能据此否定人格权的民事权利性质。本文赞同王利明教授的观点,不管是从法律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将人格权作为非财产权利,与身份权相对应,构成民事权利的基本类型,有明确的说法。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格权独立成编都势在必行,在人格权即将独立成编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讨论个人信息的保护。
2 被遗忘权刍议
上文已经介绍过被遗忘权的概念,一个权利首先要考虑权利主体,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是谁?是否还可以用传统民法中的自然人的概念?笔者认为并不合适,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是不可能说被遗忘就被遗忘的,或者说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达到被遗忘权想要达到的效果,无法保护被遗忘权想要保护的法益,被遗忘权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更多的是对网络的行为进行规制,使某个主体在网络上的信息被遗忘,这里对自然人的保护更多的是对与自然人相关的信息的保护,所以在这里用自然人当作权利主体来讨论并没有意义。被遗忘权是保护个人信息的权利,这里就借用信息主体这一概念,是指产生个人信息并享有个人信息权利的自然人。
被遗忘权保护的是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但是是否所有的个人信息都需要被遗忘权来进行保护?首先要说明个人信息的范围,齐爱民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比如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指纹,虹膜)等,王利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杨芳教授认为,个人信息也被称为“个人资料”或“个人咨询”,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护照号、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例、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联络方式、财务情况、社会活动等其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出该个人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能通过某个信息或者几个信息结合识别某个自然人,那么该信息就是个人信息。这样看来,个人信息的范围十分宽泛,必须要将比较重要的信息分离出来,但是信息不同于物,对于物来说,哪怕是对自然人意义非凡的物,比如生日礼物,结婚礼物,最终也只能按市场价进行赔偿,但是信息不同,信息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有些信息可能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有心者将一些信息收集起来却可能侵犯我们的权利,比如搜集我们的购物喜好,然后给我们推销商品,更有甚者将这些商品标上更高的价格。而且每个人所重视的信息并不相同,信息不能像物一样给出市场估价,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标准来界定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从概念中来看,个人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单一的信息就能识别个人;另一种则需要几条信息才能确定一个信息主体,在个人信息的分类上可以借鉴关于证据的分类,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而间接证据需要和其他证据一起证明案件事实,但是如果依据这种分类,即根据信息与个人的联系密切程度来分类,能根据一条信息就确定信息主体的是直接信息,根据几条信息才能确定信息主体的是间接信息,这显然是不行,因为直接信息少之又少,目前用得比较多的就是指纹和虹膜,对这两个信息进行保护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根据信息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来分类没有意义,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信息处理主体获取信息的难度来决定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比如姓名,年龄这种信息,他人很容易得知,但是像地理位置,购物痕迹,需要很高的技术难度,以信息处理主体获得信息的难度来判断信息主体信息的重要程度似乎还比较合理,那么笔者就暂且用这一标准作为前提进行讨论。
根据之前的结论,被遗忘权想要保护的就是信息处理主体相对难获取的信息,虽然被遗忘权要求的是断开与该个人信息的任何链接,销毁该个人信息的所有副本和复制件,但是这不切实际,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被遗忘权的行使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这一限制就是被遗忘权只保护信息处理主体相对难获取的信息。信息处理主体容易获取的信息甚至可以说信息主体有义务披露给信息处理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信息处理主体对信息的滥用,对于那些很简单就能获取的信息在个人信息保护时就没有保护的必要了,或者说已经由诸如合同法或者其他的法律进行过调整了,那么这里重点讨论的是那些难以被获取的信息,诸如位置信息,网页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购物记录,聊天记录,这些都属于个人信息,但是现在并没有法律对这一类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那么信息处理主体利用这些信息是否合法。
首先他们没有违约,合同中没有约定不能使用这一类信息,而且商家使用这一类信息似乎并没有直接对信息主体造成损失,可能还会给信息主体带来便利,比如位置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信息主体的安全,可以这样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侵权不是直接侵权,比如说信息处理主体获得了信息主体的聊天记录,这也是方便信息主体查找,但是如果其他主体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获得此信息就可能危害到信息主体的利益,这时候就是第三方的侵权,当然信息处理主体也有报管不当的责任,但是当信息处理主体尽到了保管义务还是没能阻止信息的泄露,此时信息主体也难以找到侵权的第三方,因为信息一旦泄露,在网络空间中会迅速的扩散,聊天记录或许可以用隐私权进行规制,那如果是地理位置信息呢?微信有一个功能叫查找附近的人,可以說我们关闭定位就是在行使被遗忘权,只是法律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罢了。也就是说,被遗忘权是存在的,只是立法者还没有认识到被遗忘权的存在,没有将被遗忘权纳入法律的明文规定中,而被遗忘权是有必要加入到法律的明文规定中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隐私权的出现。
被遗忘权与隐私权十分接近,可一说这是不同世界的同一权利,被遗忘权就是虚拟世界的隐私权。隐私权这一法学概念最早是来自于沃伦(Warren)和布兰代斯(Brandeis)在1890年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的一篇名为《隐私权》的文章,因为两位作者意识到新闻报道对生活产生的影响,他们把这种影响描述为正在“从每一个方向逾越财产和恰当的明显界限”,“大量的摄影企业和报刊企业”已经侵犯了私人生活和家居生活的神圣领域。作者从早期的英国和美国的案例出发,认为根据普通法,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思想传播的范围和形式,而不管是什么表达形式,不管这一思想有什么性质或者是价值,这一普通法上的权利依然存在。具体来说,这种权利完全独立于表达思想、情绪,或感情的物质载体或表达方式,不依赖于任何有形的实体就可以存在,就像说出去的话,演出的话剧一样,或者已经通过实物展现,比如写下一首诗歌,一小段文字,作者还是可以和纸张分离而并没有失去对作品本身的财产性权利,只有在作者将作品公开发表之后才会丧失这些权利。可以说它是完全独立于著作权法及其在艺术领域的延伸。著作权法的目的是保护作者,编者或者艺术家能够从作品中获得收益,普通法保护的则是他对出版这一行为的自由决定权,简而言之,在作品没有出版的时候,著作权法此时体现不出任何价值,作品出版之后,普通法的权利就会丧失。总之,在沃伦和布兰代斯看来,虽然财产权包括了保护人格免遭侵犯的权利,但是为了防止在“扩大外延和不寻常的意义上”使用财产权这一表述,他们将它称为隐私权,一个“独处的权利”,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跟财产有没有受到损失关系不大,法律对隐私权提供保护也不是为了保护财产,隐私权之所以存在,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隐私,是指除了包括狭义的隐私内容之外,隐私还包括他人对其姓名利益、肖像利益、声音利益、形象利益或者其他人格利益享有的利益。不论是广义的隐私还是狭义的隐私,如果全部加以保护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没有必要,像姓名,肖像,声音这些利益是一个自然人必须向外界公开的,一个自然人不可能因为其他人得知自己的姓名起诉其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如果擅自使用或者篡改姓名,也不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这种情况属于侵犯姓名权,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私人领域都属于隐私,难么触碰到哪些私人领域才属于侵犯隐私权呢,笔者认为,完全也可以以外界介入的难度来定性,如果其他自然人或者单位想要了解某个自然人的某个私人领域存在一定的难度,那么这一私人领域往往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个人信息的重要性程度大同小异,隐私权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和被遗忘权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被遗忘权可以说是第三次技术革新的产物。
那么对于信息主体来说,到底哪些信息能行使被遗忘权?笔者认为,首先,要有利于信息主体,可以主观为盈利客观为了信息主体,这和无因管理规定的主管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精神是一致的,不可能要求信息处理主体不盈利,只要是有利于信息主体,信息处理主体当然可以借此盈利。其次,不能妨碍其他信息主体,信息处理主体可以收集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信息,但是不能强行将信息主体联系起来,现在很多软件为了增加用户数量,会先读取某个用户的通讯录,然后再通过发短信的形式告知通讯录中其他信息主体他的联系人已经使用该软件,这个只能算是骚扰短信,不能称之为广告。最后,不能让其他信息处理主体或者信息主体得知该信息主体未公开或根据一般情况可推知不想公开的信息,比如聊天记录,谁都不希望自己和别人说点悄悄话天下皆知。在遵循这三点的前提下,信息处理主体可以不经同意使用信息主体的信息,比如记录浏览信息推荐浏览内容,或者分析信息主体的喜好来制作好的作品吸引更多的用户。当然,如果信息主体实在不愿意公开可以得到保护的个人信息的,可以行使被遗忘权,要求信息处理主体断开与自己信息的链接,删除副本和复制件,这样的信息主体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大数据也不会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一批人行使被遗忘权而受到影响,而且被遗忘权只是删除信息,不是删除数据。
3 结论
综上所述,被遗忘权是“告知—选择”模式的延伸。“告知—选择”模式给予了数据处理者从数据主体处取得、利用信息的正当性,却未能解决数据主体反悔时,已经交出的个人数据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关于被遗忘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值得保护,只有达到一定重要程度的个人信息才需要被保护。第二,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是由信息处理主体获取的技术难度决定的。第三,信息主体在网络上的大部分信息都是默认公开的个人信息,信息处理主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使用,只有信息主体主动行使被遗忘权时才需要将该个人信息与其他链接断开并删除该个人信息和副本。
参考文献
[1]李媛.被遗忘权之反思与建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2).
[2]邹海林.人格权为什么不能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OL].中国法学网,2018.
[3]王利明.王利明法学教科书——人格权法(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杨芳.论个人信息的隐私保护——信息自由原则之下的有限保护[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6,4(33):2.
[6]陈龙江.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7]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蔡培如.被遗忘权制度的反思与再建构[J].Tsinghua University Law Journal,201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