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书卷
☉[美]梭罗 著 戴欢 代诗圆 译
畅饮经典琼浆
倘若在选择自己的追求时,更加谨慎从事,所有的人可能多半愿去当个学生和观察家,因为这两种角色的性质和命运令所有人颇感兴趣。在我们为自己或子孙后代积累财富,成家或者立国,甚至沽名钓誉等多方面,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在探求真理时,我们却是超凡脱俗的,也无须惧怕改变或突发事件了。最古老的埃及或印度哲学家,掀起了神像的一角掩面轻纱。而这轻覆之物,如今在微微颤动,仍被撩起着,我凝视着它与往昔无异的清新的荣耀,因为他心中的“我”往昔是如此豪气万丈,而我心中的“他”如今还仰望着那景象。那掩面的神袍纤尘未染,自那神迹显现以来,岁月并未流逝。我们真正用到的时间,或者可以利用的时间,即非过去,也不是现在,更不是将来。
我的小木屋,与一所大学相比,不仅更适宜于思索,而且更适宜于严肃地读书。尽管我所阅读的书籍不在一般图书馆的借阅范围之内,我却比先前受到了那些全世界更流通的书籍的更多影响,那些书的段落最初是写在树皮之上的,如今只是偶尔临摹在亚麻纸上。诗人密尔·卡马·乌亭·马斯特说:“读书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坐着便可在精神世界里纵横驰骋。当我畅饮着深奧之学说的甘露玉浆之时,我便体验了一醉方休的快感。”整个夏季,我将荷马的《伊利亚特》摆在桌上,虽然只能偶尔翻阅一下他的传世诗篇。当初,我忙得不可开交,我要造好房子,同时要去锄豆子,难以抽空去作更多的阅读。但我一直有这种念头,我不久是可以尽情阅读的。我在忙碌之余,还读了一两本通俗易懂的旅游指南,但随后就自觉羞愧难当,我自责道,怎么就忘了自己现在所处的地方。
学生们读读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绝不会招来放纵或者奢靡的惊人之举,因为他自会仿效巨著中的英雄豪杰,在清晨的大好时光专心读书。这些英雄的诗篇,即使译成我们的母语刊印出来,在这个道德败坏的时代,也会变成一堆死寂的文字。因而,我们必得不辞辛劳地探寻每一个词和每一行诗的蕴意,绞尽我们的脑汁,勇猛而有雅量地琢磨出超越寻常应用的更深远的蕴意。
当今的出版社,虽然出版了大量而又廉价的译著,但并未使我们向那些古代的伟大作家靠得更近。这些译著令人不敢问津,它们的文字仍像以前一样被印得稀奇古怪。花费了宝贵的青春时光,即使研习了几句古文,也是颇为值得的,因为它们是街头巷尾中琐碎言谈的精粹,给你永恒的启迪和激励。农夫们偶然听到几句拉丁语警句,牢记在心,并时常挂在嘴边,也是有百益无一害的。某些人曾经说过,对古典著作的研究好像最终让位于更现代、更实用的研究了。但那些雄心勃勃的学生仍会常常去研究古典著作,无论它们是用何种文字写就,也无论它们的年代如何久远。倘若古典著作不是记录下人类最崇高的思想,那么古典又是何物呢?它们是独一无二、永不腐朽的神迹谕旨。即便去特尔斐和多多那求神明示,也是终不可得的对现代求问的解答,却在古典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或许不屑于去研究大自然,因为她已衰老了。好好读书,也就是说,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去阅读真实的书,这是一种高尚的历练,阅读者的劳神费力,已超过了世俗公认的任何历练。这需要一种锻炼,正如运动员要经常锻炼一样,终身不辍,持之以恒。书是务必要谨慎而又缄默地去阅读的,这与著书立说是同一种态度。
口语与文字的差异
即便你所讲的语言与原著相同,这仍是不够的,因为口语与书面语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一种是听说的语言,一种是阅读的语言。口语通常是说过即逝的一种声音或是舌音,是一种土语,几乎可说是很粗野的,我们能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里下意识地学会。书面语则是口语的成熟和精炼的表达。如果说口语是我们的母语,书面语则是我们的父语,它谨慎而精细的含义表达,并非听觉所能感触,我们必定要再次降生人世,从头学起。
中世纪时,有无数之人,他们可以流利地讲希腊语和拉丁语,因为身处不同的地域,他们难以读懂天才作家们以这两种文字写出的书卷,这些书卷并非以他们所熟知的希腊语或拉丁语,而是以精炼的文学语言写成,他们没有学过希腊和罗马的那种更高一级的方言,此种语言所写的书卷,在他们眼中不啻是一堆废纸,他们对一种低廉的当代文学倒能爱不释手。但是,当欧洲的几个国家拥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字,虽说不够成熟,但也表达无碍,他们的文艺便足以复兴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知识的复兴,学者们能够识别远古的传世佳作了。罗马和希腊的民众当时难以听懂的作品,在岁月流逝了数个世纪之后,少数学者已能读懂了,如今也只剩几个学者在研读这些作品了。
无论我们如何对演说家的精彩演讲赞不绝口,那最崇高的文字,仍时常地隐匿于口语之后,或是超越于瞬息万变的口语之上,宛若群星闪烁的天空为浮云所潜藏。群星浩瀚,但观星者皆可阅读它们。
经典传世
亚历山大率军征战时,爱在一只宝盒中放上一部《伊利亚特》随身携带,也就没什么令人疑惑不解了。文字是圣物精品中的精品,它与其他任何一种艺术作品相比,与我们最为亲近,又更具世界性,它是最靠近生活的艺术作品。它可以译成各种文字,不仅让人阅读还从人的口唇中吐露出来;它不仅显现于画面之上,或镌刻于大理石上,而且还塑造于生命自身的气息之中。一个古人思想的烙印被现代人常挂嘴边。
两千个夏季已然给希腊文学的丰碑镀上了一片璀璨,如同在希腊的大理石上,遗留下更为成熟的一如秋收的金黄色泽,因为他们让祥和而肃穆的氛围降临了整个大地,守护自己免受时间的侵蚀。书卷是世界的珍贵财富,是诸国代代相传的恰当遗产。书,年代最久和最好的书,自然而又得当地摆放在每间房内的书架上。它们没有任何诉求,但一旦它们启发并去鼓舞读者,他的常识会使他欣然接受。这些书的作者,在每一个社会之中,自然而无可抗拒地获得了贵族的尊位,他们对人类的影响比许多帝王更胜一筹。当那大字不识,或者还受人蔑视的商人,因为苦心经营,赢得了他渴望的休闲和自主,并跻身于财富与时尚的圈子之后,他最终将不免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禁地森严的知识分子和天才们的圈子,此时便会更加意识到他腹中空空,自己的所有财富也难以弥补虚荣,他便费心机,要让子孙后代获得他深感匮乏的智慧文化,于是这又证明了他敏锐的眼光,他因此成了这个家族的创立者。
经典必读
那些还没学会阅读古代经典名著原文的人,对人类历史的知识一定知之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经典名著仍未被译成当代的任何一个版本,除非我们文明自身姑且算作这样一个译本。荷马史诗还从未出过英译本,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也没被译成英文。这些名著是如此精练,如此纯粹,宛如霞光一般美丽。谈到以后的作家,无论我们是多么钦佩他们的写作天赋,但论其作品,堪与这些古代文学巨匠的精美的、全景式的、永世长存的、以毕生心血铸就的文艺结晶媲美的,却属凤毛麟角。对它们一无所知的那些人,一个劲嚷嚷叫人将它们打入冷宫。当我们具备了一定的学识与天赋,就能够去赏析它们,那些人的蠢话我们即抛在脑后了。当那些我们称之为圣物的古代经典巨著,以及比之更加古老,因而更鲜为人知的诸国的经典越积越多时;当梵蒂冈教廷里,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大作与《吠陀经》《波斯古经》和《圣经》荟萃一堂时;当后续的世纪连绵不绝地在世界的讲坛上陈列它们的战利品时,那个时代必将无比富饶。借助这堆积而成的文艺经典的山峰,我们最终有望登上天堂。
这些伟大诗人的诗篇,人类迄今从未阅览过,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懂它们。众人阅读这些诗人的大作,有如抬头观望满天繁星,至多是为了观测星相,而不是做什么天文学探索。大多数人学会了读书,只是为了贪图微不足道的便利,如同他们学会了数字运算是为了盘算账目,以免与人交易时受骗上当。但是,阅读作为一种高尚的心智锻炼,他们却略知一二,或一无所知。阅读不应如奢侈之物引诱我们,致使我们在阅读时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我们须端坐一隅,趁我们最为警醒的大好时光去凝神阅读,这样的阅读,才是与读书的初衷相符合的。
休读言情小说
我认为,当我们能识文断句之后,就应去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要永无休止地去重复字母歌和单音字,别在四五年级留级,终身坐在最低年级教室的前排。大多数人能够读懂或是听懂别人阅读就心满意足了,或许仅领悟了一本好书《圣经》的智慧,因此在一生的其余时间只去读些所谓休闲的书,生活过得单调乏味,虚度了光阴。
在我们的流动图书馆里,有一部数卷的作品名叫“袖珍读本”,我以为它是一个尚未去过的镇名吧。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好像水老鸦和鸵鸟一样贪婪,消化能力很强,即使在饱餐了一顿肉食和蔬菜烹制的美食之后,仍能将残羹剩菜一扫而光,生怕浪费掉了。倘若其他人是供应这种美食的机器,这类人则是不知饱足的阅读机器。他们阅读了九千个关于西布伦和赛芙隆妮娅的爱情故事,全都是讲述他俩如何相爱,爱得如何死去活来,史无前例,以及曲折的恋爱历程。总而言之,他俩如何艰难相恋,如何爱情遭到不幸,跌倒了又爬起来,怎样再续恋情!某个可怜的不幸之人是如何爬到教堂的塔尖上的,他要是没爬上去就万事大吉了,接下来就是,他既然已鬼使神差地爬上尖顶,那快活的小说家就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让人们都围拢过来,聆听他卖关子,噢,天哪!他怎么又下来了!在我看来,这些作家最好将所有小说中的痴男怨女一律变形为风信鸡人置于尖顶之上,就像他们常常将英雄升上星座一样,让他们在尖顶上随风旋转,直到锈掉为止,千万别叫他们下来搞些恶作剧,骚扰了老实本分的人。下一次,若是小说家又敲响了钟声,即使是教友会的聚会所被大火一烧而光,我也会稳坐钓鱼台的。
“一部中世纪的罗曼史《偷情舞会》,由著名作家特尔·托坦恩所著,月月连载,读者甚多,欲购从速。”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阅读起来眼睛睁得有小碟子大,好奇得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胃口也是极好,不怕胃壁损伤,正如四岁小孩,坐在小凳子上,读着两美分一本的封面烫金的《灰姑娘》——照我看来,他们读完后在发音、音调、语气等方面没有一点长进,更不用说他们在表现与渲染主题方面学到了什么写作技巧了。结果是读得两眼呆滞,思想颓废,智力下降。
愚钝的读书人
最好的书,那些所谓的好读者往往也不屑去读。我们康科德的文化算什么东西?在这个城镇上,只有极少数人例外,大多数人对于最好的书,甚至是英国文学中非常优秀的作品,都觉得兴味索然,他们对英语可是能读会写的啊。即使毕业于各地的大学,或所谓的受到自由熏陶的人,对英国的古典文学也知道甚少,乃至全然不知,至于铭记着人类智慧的巨著,比如古代经典作品和《圣经》,谁想阅读是不难得到的,但也浅尝辄止。
我认识一个伐木工,他人到中年,也时常读一份法文报,他说并非是为了读读新闻,他是不吃这一套的,而是为了“不间断地学习法语”,因为他生在加拿大,我便问道,他认为在世上他能做的最好事情是什么。他答道,除了学好法语外,还要下功夫学习和提高英语水准。大约这就是大学毕业生普遍要做或想做的事情吧,他们订阅一份英文报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假如一个人刚好读完了一本或许是最好的英文佳作,又有几人可以与他谈谈读后感呢?或又假设一个人刚读完了一部希腊文或是拉丁文的古典原著,这本书即使所谓的文盲也懂得去赞美它,但他完全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谈谈心得,只能三缄其口啊!千真万确的是,在我们大学几乎找不出这样一个教授,如果他对一种难学的语言已能运用自如,便会相应地去把握希腊诗人恢宏的睿智和诗意,并能抱着交流的意愿,去给那些机敏而又脱俗的学生传授这种知识,至于说到神圣的经典,或者说人类的《圣经》,这个镇上有谁能告诉我它们的书名?大多数其实并不知道,除了希伯来民族之外,其他的民族也拥有自己的一部《圣经》。任何一个人,都会为拣到一块银币而煞费苦心;但是这里就有金灿灿的文字,古代的最睿智者说出的语言,它们智慧的珍贵价值为历代所公认。然而我们读到的却只是简易读本、初级读本和教科书,离开学校后,就只读些“小册子”和故事书,它们可是专门写给孩子们和初学者看的。因而,我们的读本,我们的谈吐和我们的思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准,只与俾格米小矮人相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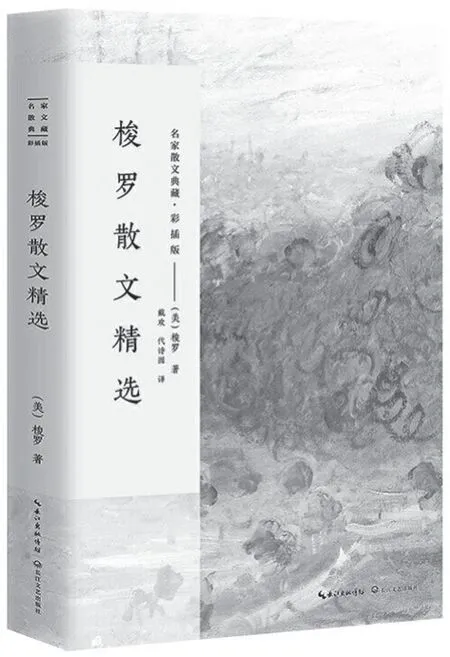
我盼望能结识一些比康科德这片土地上长出的更加聪颖的人,他们的姓名在这里闻所未闻。难道我会听说过柏拉图的名字,却从未拜读过他的大作吗?仿佛柏拉图是我的同乡,而我却与他素昧平生;仿佛他是我的贴邻,而我从未聆听过他的话语,或者倾听过他饱含智慧的言谈。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他的《对话录》,充满了他不朽的智慧,就闲置在我们近旁的书架上,却遭到我们的冷遇。我们全都是文盲,简直是缺乏教养,格调低下。我认为,在此情形之下没必要将两种文盲细加区分,一种是我同镇人中的目不识丁者,另一种则是能读书识字,却只能读读儿童读物和极为简单易懂的读物,我们应该如古代圣贤一样令人敬仰,但我们首先得知道他们有何处值得受人敬仰。我们都是一些人微言轻的人,我们的智慧的飞翔,却难以超越日报栏目内容的高度。
开卷有益
并非所有的书卷都如它们的读者一样愚不可及,可能书中的一些话恰能切中我们的时弊,如果我们真的聆听了,而且完全明了这些词句,它们对我们生活的裨益,将胜过清晨和阳春三月,或许能使我们旧貌换了新颜,有多少人是读了一本书,从而令他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本书,若能阐释我们的奇迹,又能显示未来的奇迹,那它就真是为我们而存世了。就在今天,我们难以启齿的话语,也许在书中某处已经言明了。这些困扰着我们,弄得我们迷惑不解而狼狈不堪的问题,一切智者也同样遇到,无一例外,每个智者已力所能及地,以各自的语言和各自的人生来解答了这些难题。况且,拥有了智慧,我们才能学会慷慨行事。
在康科德郊外,在某个田园,有个寂寞的雇工,他有着第二次的诞生和独特的宗教体验,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相信自己沉浸于悄无声息的肃穆之中,拒绝外物的亲近,或许他认为书中尽是些虚妄的言辞。但是数千年前,琐罗亚斯德就走过了与那位雇工同样的心路,有着同样的历练,可是也聪慧过人,悟出了自己的历练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就能相应地与乡邻交往。据说他创立了祭奉神灵的礼仪。那么,让那位寂寞的雇工谦逊地与琐罗亚斯德相互通灵吧,并在一切圣贤的自由影响下,与耶稣基督通灵吧,让“我们的教会”滚到一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