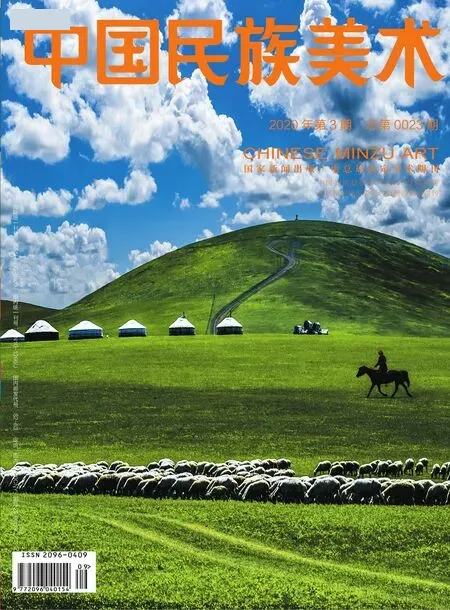油画中的蒙古族女性形象审美特征及精神表达
文/图:德德玛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2019 级博士研究生

虎仔 金高 油画 66cm x 126.8cm 1986 年
蒙古族作为我国传统的北方游牧民族,有其特定的风俗习惯。正如“地域环境具有基础性潜在的影响力”[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特定的风土人情,“蒙古民族居住在远离海洋的蒙古高原干燥的环境中。但是欧洲地图一直把他的部落标记做‘水蒙古’,或者突厥语‘Sun Mongol’。一直待到17 世纪末,欧洲地图上都是这样标示的,但是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名字和蒙古人赋予水的地球母亲滋养生命的雌性力量之间的联系”[2]。蒙古族女性的内在共性特征,也和她们生活的地域环境和游牧文化有很大的联系。本文将蒙古族女性的共性特征归纳为三类。
一、如水般滋养万物的母爱
在蒙古族人的眼中,河流像母亲一样滋养着万物。蒙古族女性也像水一样滋养着生命,蒙古族的母亲形象不只是局限于对自己的孩子的爱,还有对其他的孩子,恰如罗曼·罗兰曾说:“母爱是一团巨大的火焰!”那么,蒙古族的母亲更像是宽广深沉的湖水。电影《额吉》,还有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讲述了蒙古族女性宽广的母爱故事。20 世纪60 年代初,内蒙古收养了3000 名上海孤儿,蒙古族母亲用自己的母爱诠释了大爱无疆 。“生命”一词用蒙古语来说就是“艾敏”,艾敏河的镜头从头到尾在影片中一遍又一遍的出现。象征着蒙古族母亲像河水一样滋养着生命。除了爱孩子,蒙古族女性的母爱还表现在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畜群和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爱。在草原上生活,畜群们生下小畜,有时难免会出现母畜不愿意抚养自己孩子的情况,这时,蒙古族女性会为它们唱劝奶歌来唤醒它们的母性,甚至会拉起马头琴,有时候会唱得母畜潸然泪下,即使不是自己亲生的小畜,也会欣然接受。在描绘蒙古族女性形象的画面中,常见蒙古族女性或母亲,抱着小羊羔等小畜,给它喂养牛奶等。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蒙古族女性的母性特点是博爱的,是像水一样滋养万物的。蒙古族题材记录电影《哭泣的骆驼》,正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牧民家中的母骆驼,因为产下小骆驼时痛苦的经历,不愿意喂养她的幼崽。这时牧民家中的女主人专门从远方请来了马头琴师,伴着她动人的歌声唤醒母骆驼的母爱。母骆驼听后感动得潸然泪下,欣然接受了自己的孩子。”
二、勤劳朴实

挤马奶 金高 油画 76.2cm x 101.5cm 1985 年

垛草的妇女 妥木斯 油画 175cm x 175cm 1984 年(中国美术馆藏)
除了母亲的角色,蒙古族女性作为家族里的一员,勤劳成为了蒙古族女性的又一共性特征,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首先是社会环境,蒙古族女性是家庭的后方主力,家里的一切杂物事,饮食起居无不包含在蒙古族女性的日常劳动中。“鞑(靼)人的妻子、儿女、日常用具以及所需要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车子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妇女经营一切买卖,家里的日常事务也都由妇女来管理。”[3]在一天的草原生活中,蒙古族女性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一大早就要起来挤牛奶,然后为一家老小准备早茶,之后要制作各种家庭所需生活用品,例如奶制品、肉制品,还有亲手缝制蒙古袍等等。由此可见,蒙古族的妇女在家里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古今,在牧区的蒙古族男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放牧,蒙古族女性则承担着辅助甚至同样的任务。在暴风雨雪等恶劣的天气来临的时候,蒙古族女性也承担着找回畜群,安顿好它们的工作。在我国的油画作品中也经常可以见到蒙古族女性劳作的身影,例如妥木斯的油画作品《垛草的妇女》中所描绘的正在劳动的蒙古族女性形象,让观者从画面中感受到了蒙古族女性的勤劳,也透出一些和男性相同的能力与担当。
三、珍爱生命,随遇而安

蒙古的山 朝戈 油画 124cm x 86cm 2006 年
对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随遇而安的性格也是蒙古族女性的显著特征,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向何方?走向一个更实在的人生,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社会。”[4]正如蒙古电影《小黄狗的窝》中,牧民家的小女儿因为在山洞里捡来一只不明来历的小狗,受到父亲的指责,因为惧怕这只狗和狼有过瓜葛进而引来狼群侵袭家畜。这时影片中小女儿的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表明了她的态度:“他会来我们家,搞不好是注定的!”(影片18 分39 秒处)电影中女主人公多次提到小黄狗与家人的缘分,体现了蒙古族女性对事物的接受、包容和顺其自然的态度。蒙古族导演巴音的电影作品《诺日吉玛》,正是道出了蒙古族女性的这一份人情味。电影讲述了30 年代抗战时期,在草原上捡回两位身负重伤的敌我两方的士兵,在精心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同时,还要竭尽全力阻止他们再次相互厮杀的故事,战争是残酷的,但是电影中的蒙古族女性对生命平等的尊重和珍爱,让人感动。

远方 朝戈 布上坦培拉 76cm x 53cm 2003 年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了蒙古族女性从小就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她们大都在生活中扮演着和男性一样重要的角色,同样受到尊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蒙古族女性必须在生活中参与大量的劳动,要从事所有家务,劳动量很大。稳重、踏实、勤劳是蒙古族女性的共性特征,遇上恶劣的天气,蒙古族女性必须依赖自己来完成劳动,例如赶牲畜回圈等,体现了蒙古族女性独立自理的能力。“文化是有适应性的,不同的文化都是适应不同的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产生的,所以说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产物。因此就会有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平原居民的定居农业文化,江河海边的渔业文化等。”[5]分析我国表现蒙古族女性题材的绘画,除了作为母亲哺育孩子的画面,大部分都是蒙古族女性劳动的场景,例如照顾畜群、打草、挤奶、等待牧人归来等等。“无论如何,当艺术家们希冀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及其内在气质并将它们在画面上表现出来时,这些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细枝末节都是万万不可忽视的。”[6]这些生活场景经过艺术家的精心提炼和描绘,转移到画面中,真实地再现了蒙古族女性的生活状态。
1.母亲哺育孩子
女巫一词和大地女神在蒙古语里是一个词:巫都干,其本义都有创立者的意思。“蒙古族称天公地母,认为天是阳性根源,赋予生命,地是阴性根源,赋予形体。”[7]画家笔下表现的蒙古“额吉”的形象,总是能以其真挚的情感,感动观众。例如,金高的作品就表现了蒙古族母子之间的亲情关系,在《爱》和《虎仔》这两幅作品中所刻画的温馨场景,就充分地表现了蒙古族女性温暖、善良的心灵。《虎仔》描绘了母亲与孩子温馨的瞬间,母亲身着黄色基调的衣服在视觉呈现上对整个作品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爱》同样表现的是母子之间的关系,白色的画面并没有让人们感觉出丝毫的寒意,温暖人心的气息溢满整件作品。《绿色摇篮》这幅作品画面中母亲手里拿着正在编织的毛衣,坐在床上,用一只脚轻轻勾住摇篮,双眼充满爱意地望着摇篮中的孩子,表现了蒙古族女性温柔的母爱。

等待醉归丈夫的好力堡妇人 龙力游 油画 112cm x 145cm 1995 年
2.挤奶
挤奶是草原上蒙古族女性必须具备的一项生活技能,这关系着家里的奶食来源,同时,奶食品也成了牧民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描绘蒙古族女性挤牛奶的作品很多,例如龙力游的《等待成长的季节》,画面中站在中间回眸一望的蒙古族女性和远处正在挤牛奶的蒙古族女性全部身穿布里亚特地区的长袍,因为在牧区,又是日常生活场景,所以并没有佩戴布里亚特头饰,而是头扎亮色头巾。除此之外,在牧区,蒙古族女性还会挤马奶、挤羊奶,金高的《挤马奶》就表现了蒙古族女性挤马奶的生活场景。
3.打草
打草是草原上一项劳动生产内容,以此为题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妥木斯的《剁草的妇女》,画面中的蒙古族女性,身穿白色长袍,右手用一直木叉子剁草,神态悠然自得,仿佛一阵清风吹过,化解了劳动的辛劳。除此之外,妥木斯表现打草的作品还有《剁草》,同样描绘了蒙古族女性打草的场景。
4.等待
除了描绘蒙古族女性劳动的场景之外,还有一种蒙古族女性生活状态的定格画面,就是等待,画面中的蒙古族女性右手轻轻抬起,左手提着奶桶,眺望远方,等待牧人归来。这样的画面具有永恒的诗意。就像电影《诺日吉玛》中的女主人公,经常站在草原的高处向远方眺望,等待他的未婚夫,一等就是很多年。在油画作品中,也有不少描绘蒙古族女性等待这一状态的作品,如朝戈、龙力游都从不同的角度描绘这一瞬间。
朝戈的“等待”,更多的是将这一瞬间的动作化成了永恒的、雕塑纪念碑式的定格画面。2006 年的作品《虹》画面描绘了一位侧身站立的蒙古族女性,她的右手半弯着举起,仿佛在遮挡着阳光,又仿佛是在和远方打着招呼。她的目光眺望远方,神态淡然又若有所思。身后的一片雨后的彩虹,远处倾斜的山坡,使主人公处在一个居高临下的高度上。画面中的蒙古族女性穿着传统的蒙古长袍,简单梳起并自然下垂的马尾辫。而这幅作品还有一个幅是描绘男性的,就是1989 年的作品《红光》,有着类似的姿势和状态。2006 年的作品《蒙古的山》,画面主要描绘了蒙古族女性,她身穿蓝色蒙古袍,面部呈现在高原日光下劳动所呈现的红铜色,画面中的蒙古族女性,神情淡然,几乎没有表情,显得十分安静,左手手背轻轻依靠在脸颊上,手臂与地面平行,这一刻,仿佛是一瞬间,又仿佛是雕塑般的永恒。斑驳的蒙古长袍和轻轻擦拭汗水的动作仿佛是泄露了蒙古族女性朴实勤劳的天性。远处有山,但是与画面最前面的大面积女性形象比较,显然是十分渺小的。正如题目中描述的,《蒙古的山》,在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而是这里的一位女性,或妻子或母亲。从心理层面来讲,蒙古族把母亲在心里的位置或许看得比物理意义上的山还要高大。朝戈的作品《虹》和《蒙古的山》以及2003 年的作品《远方》均以相同的姿势描述蒙古族女性在草原上等待这一生活瞬间。其次,龙力游的《等待醉归丈夫的好力堡妇人》和《别列古台又喝醉了》从另一个角度,诙谐地描绘了蒙古族女性对家人的等待之情。
四、结语
蒙古族女性的内在共性特征呈现出的是一种富有自然气息的淳朴母爱,坦率直爽、勤劳、坚韧、博爱等内在特征成为画家在绘制蒙古族题材的绘画时最常见的一种形象。这些具有共性的相貌外形与内在的性格特征,使之成为油画艺术家们表现蒙古族女性形象时力求还原的形态。
注释
[1]宋生贵.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121.
[2]杰克.威泽佛德.最后的蒙古女王[M].赵清治,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19.
[3][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肖民,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69.
[4]周国平.在维纳斯脚下哭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0.
[5]杨圣敏.民族学是什么[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
[6]康笑宇.由民族题材绘画引发的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4):64.
[7]平常.中国女性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8):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