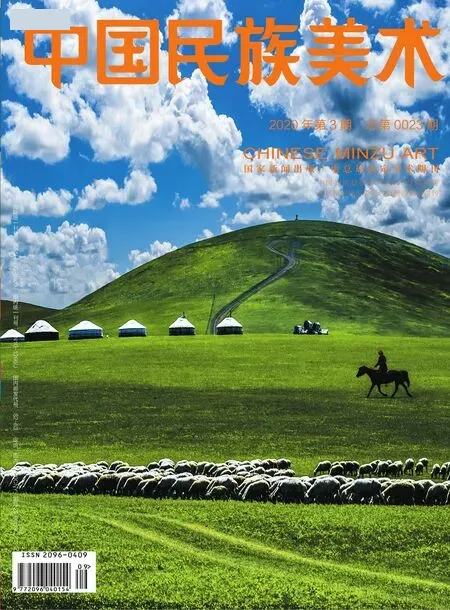武山拉梢寺摩崖石刻大佛座具中动物造像新探
文/图:汪宝琪 宁夏大学美术学院2018 级硕士研究生
卯芳 副教授 宁夏大学美术学院
拉梢寺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西北部的鲁班山上,有渭河横穿其中,形成了向东连接关中、向南紧邻巴蜀、向西控制甘南、向北遏制陇坻向的锁钥之地,而拉梢寺就位于正中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拉梢寺”意为“在崖壁堆积树木开凿出的窟寺”,窟顶摩崖石刻开凿于莲包峰南壁一处高约60 米的弧形崖面上,窟区总平面呈“L”形,最长端超过300 米。崖面石胎泥塑浮雕有一佛二胁侍菩萨、大佛座具下有七层动物、植物相间组成的装饰性石刻,以对称性构图原则共同组成了一幅遍布崖面的“佛说法图”。

拉梢寺石窟平面图(采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于拉梢寺摩崖石刻造像,学界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吴荭《北周石窟造像研究》和乔今同《武山洛门镇的古代石窟》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拉梢寺北周造像基本情况。董玉祥、藏志军《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提出拉梢寺摩崖大佛佛座具中,石刻的莲花、卧狮子、卧鹿以及大象组成的六层大佛座具有着丰富的装饰效果,在国内其他摩崖石刻中并不多见。[1]杨森的《拉梢寺大佛题记考跋》则是从大佛发愿文石刻碑的断代来分析了相关历史。[2]美国学者罗杰伟《北周拉梢寺中的中亚主题》通过对比国内外的动物形象与拉梢寺佛座上的动物形象,提出拉梢寺石刻造像具有中亚波斯艺术因素,并指出:“大佛佛座,以六层图像支撑中央大佛,在北朝佛教艺术中乃是特例。”魏文斌和吴荭《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北周供养题记反映的历史与民族问题》中详细讨论了民族问题。[3]尽管学界在相关论著都已认识到了武山拉梢寺摩崖石刻中大佛座具上卧狮、卧鹿、立象与仰莲等动植物相间装饰具有紧密丰富的独特性,但都没有从佛教文化的本源去揭示的这种大佛座具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摩崖石刻大佛造像座具
拉梢寺摩崖石刻造像坐佛为释迦牟尼,坐佛通高34.75 米,面形丰圆,大眼宽眉,躯体很是健硕,脖颈稍有粗短,身穿圆领披肩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坐台上,双手上下重叠,手掌掌心向上放置在腹部,禅定印。结跏趺坐也称之为金刚跏趺坐,令二掌仰与二股之上,各为吉祥,故常安此座,转秒法轮。[4]佛身色彩主要以朱砂色为主,胁侍菩萨的石刻造像位于大佛的两侧,以站立姿势在旁,分别为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左侧文殊菩萨通高27.25 米,头戴三瓣莲式宝冠,脸容方圆,颈短肩宽且圆润,上身穿偏衫,左手伸于腹前,双手捧着盛开的莲花造像,右手上举与右肩之上,掌心朝外,手持莲花的茎部,整个菩萨身体向大佛倾斜而立,寓意虔心听释迦牟尼说法,站立于底坛台上。右侧普贤菩萨高为26.75 米,与左侧的文殊菩萨面容、姿态基本相同,其宝冠和面部有后代重修的痕迹。整个石刻造像给人以憨厚、大方、朴实的感受,这便是典型的北周造像风格。
该处摩崖石刻造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大佛佛座。坐具是自上而下浮雕七层动植物相间图像组成,高约17 米、宽17.55 米。整幅座具的构图分别由双重仰莲莲瓣、卧狮、卧鹿、立象、双重覆莲相见的七层纹样组成。因年代久远,部分浮雕色彩已脱落,但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的色彩效果依然震撼,按照造像各个形态及装饰物的不同色彩依然浓淡相宜,气韵生动,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艺术魅力。

拉梢寺1 号佛、菩萨像 北周(采自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

拉梢寺石胎泥塑佛座(采自丝路明珠拉梢寺)
大佛座具自上而下:第一层为双重仰莲,莲花象征着佛法,外层莲瓣以朱红色为主,内层莲瓣则以石绿彩绘,设色丰富且和谐,在印度佛教出现后,便有了释迦牟尼的七步踏出七朵莲花的典故,故在后世讲经说法时,佛座多为莲花纹样,这一点在“成佛的《法华经》中”进一步证实;第二层为卧狮,原共有九头,现存五头,因在唐末宋初重塑时在佛座中部开凿了一长方形尖拱顶浅龛,龛内塑有一佛二菩萨,左右两侧各开一小龛,故此破坏了四只狮子及第一、三层的部分仰莲;现存座具中的五只卧狮,身高1.8 米,宽1.75 米,形态各异,有张嘴露齿、闭嘴温顺、狮子外形卷毛竖耳、半张嘴发怒的,其毛发与脸型各不相同,双腿前伸并爬于地面,左侧两只侧面朝左、右侧三只侧面朝右,卧狮的石刻线条简约而生动,毛发处理得相当简练,雕刻法以阴刻法为主,每只狮子间隔较小,重叠排列,只露卧狮的前半身,设色主要以朱砂、胭脂为主,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造型技法处理,进而描绘出卧狮身体上肌肉健硕、动态凶猛、强悍;第三层为双重仰莲,与第一层仰莲不同的是莲花的瓣头雕刻的略往下翻,似有盛开之势,花心顺着凹进的山崖也凹了进去,莲瓣上也带有翻卷纹的线条,逐渐与上层仰莲结合,有了层次渐变的视觉效果;第四层为卧鹿,共有九只,基本上是三只为一组,中间一只为正面,左右各有四只为侧面,卧鹿食客形象身高2.0 米,宽1.75 米,卧鹿的鹿角以竖起状姿势呈现,嘴角露着长短不一的长牙,每只卧鹿造型虽都是双腿前伸、跪卧于地的姿势,但动态不一,最中间的一组三鹿头顶被唐末宋初的佛龛造像部分破坏,大多色彩已经脱落,中间一鹿呈正面像,眼睛视角也在正前方,看着很是生动。鹿的雕凿线条较为圆转、光滑,每只鹿都有细微的变化,有的耳朵高竖,有的脖子向前伸,好似在往前一只鹿身旁依偎,鹿的动态造型大小不一,排列顺序与卧狮相似,身体重叠排列,设色比较丰富,有土红、朱砂、石绿为主色调,搭配成条形纹饰来突出卧鹿的身姿矫健,一眼望去,卧鹿时而温顺,时而调皮,时而又凶猛不已,变化莫测;第五层是双重仰莲,其花瓣形状更加圆润了一些,与前两层莲花瓣不同的是根部为黑色(根据专家考证研究,本色应是深红色,在后期氧化后深红色变成了黑色)瓣头的色泽也比之前颜色深,内层瓣头的颜色比外层的颜色浅而清亮,装饰效果明显,与当代的“3D”装饰效果可以媲美;第六层大佛坐具是由九只立象组成,保存得较为完好,立象通高3.05 米,宽1.70 米,中间一只为正面,左右各四头为3/4 侧面,笔直站姿,大耳下垂,象牙都是朝前,象鼻着地(正面立象则五官对称,象牙左右平衡,微微打开),鼻尖略微上卷,其设色简单而不失华丽庄重,以朱砂、土红设色为主,五官基本运用凹凸染法,立象造像风格写实,体型粗壮肥硕,虽站立于一排,但高低错落有致、形态各不相同,雕刻技法成熟,线条方中带圆,立体感突出具有很浓郁的犍陀罗造像风格;第七层是很长的一组双重覆莲,表皮颜色已脱落,裸露在外的是基本雕刻轮廓,莲花瓣头朝下,花瓣比前三层更大更宽,底层莲瓣托举着整个压面的石刻造像,包括大佛两侧的胁侍菩萨,菩萨赤足站立于最底层的莲瓣上,场面宏大而雄伟。
二、大佛座具中动物造像的象征因素
拉梢寺摩崖石刻大佛座具中的卧狮形象,象征着人群中的首领,狮形象象征佛陀。在古代印度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东汉时期被国人所接受并绘制在壁画题材中,在佛教经典中,《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录:“作狮子吼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据记载,拉梢寺首次开凿时间为北周明帝武成元年,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艺术的盛行带动了石窟造像卧狮的出现,在佛菩萨造像前的狮子,具有听经护法的作用,造型特点较为真实,同时受到了西域以及中亚文化的影响,说明北周时期的题材和艺术雕刻吸收和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涵,造像形成了质朴、敦厚的特点,卧狮昂首挺胸,以静为主,既温顺有凶猛,身体呈蹲坐式姿态,充当着佛法的护卫者形象。《大智度论·七》:“佛为人中狮,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狮子作为文殊菩萨的坐骑,代表着力量与智慧。《玉芝堂谈荟》曰:“释家以狮子勇猛精进,为文殊骑者”,在敦煌瓜州榆林窟第三窟就可见“文殊变”的说法图;在佛陀的本传故事中,卧狮不仅在弘法方面有象征意义,在世系、修行等方面也各有代表。
大佛座具第二组动物造像为卧鹿,鹿在佛教中代表法论或象征着释迦牟尼,在大佛石刻说法图中刻画出卧鹿虔诚听法的造型。卧鹿个个独角竖耳,前腿屈,中间一只鹿为正面,左右两侧卧鹿对称排列,是一个标准的“对称性构图”,代表祥瑞,寓意吉祥,“鹿”行菩萨道,为佛之前身,这在梵文鹿野苑中就有证实。[5]鹿野苑是一片鹿群出没的原始森林,释迦牟尼在悟道成佛后,第一次说法收徒,便称为“初转法轮”。在萨尔那特考古博物馆藏的五世纪的《释迦八相图》中就有双鹿的形象,“八相”在佛教中的术语是“八相成道”,表示释迦牟尼从出生、转法再到涅槃的一生,总结成了八件重要的事情。八相图左侧第一列的石刻“初转法轮”中有三尊如来像,主尊释迦牟尼的正下方中央是法轮,法轮左右两侧是卧鹿与卧狮,卧鹿造型很是虔诚,双腿跪卧于地,成抬头挺胸姿势,身体紧靠莲座,形似认真听释迦牟尼说法,两侧动物形象也是对称而坐,井井有序,鹿野苑便是图中石刻的双鹿暗示释迦牟尼成道后初次说法的法会场所。武山地区当时虽然是北周鲜卑政权,但也是各民族长期杂居的地区,所以对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可以兼容并蓄。
摩崖大佛座具中保存最完好的动物浮雕是底层的立象,站姿、大耳下垂、双牙前伸、鼻尖略上卷,正面立象在中间,两边各四只呈对称状分布,这是典型的中亚佛教造像风格,在印度初期佛教美术中,以佛教遗迹印度巴尔胡特为主的佛塔中有释迦牟尼的事迹“调伏醉象”,并记载于众多佛教经典中,主要讲释迦牟尼一行人行至罗阅城,阿闇世王欲以醉象踏杀释迦,反而释迦以五指幻化出五狮降伏醉象。在《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第二》中记载六牙白象为佛的化身,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负,无漏无染,称之为白。在释迦牟尼的一生中大象的说法多样,有乘象入胎,也有乘六牙白象等说法。在敦煌瓜州榆林窟第三窟“普贤变”的说法图中,可见普贤菩萨在骑着白象诵读《法华经》。榆林窟第25 窟中唐时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普贤菩萨骑象的妙像,普贤菩萨手持梵箧半跏趺坐在白象的莲座上,白象四蹄踩踏莲花前行。立象位于大佛座的最下端,宽厚硕实的身躯承载着整个大佛佛座,在佛教中被赋予着很深的意义。

拉梢寺1 号佛座象 北周(采自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
三、大佛座具中动物造像的文化内涵
拉梢寺因其独特而神秘的地理位置,又处于秦州与中原地区的接壤地带,因而佛教艺术与佛教文化受到了多元化影响。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展,受中亚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大佛坐具下的动物形象出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面貌。大佛座具下的卧狮、卧鹿、立象动物石刻造型简洁古朴且不失动感,其中大象性情温顺而又力大无比,在佛教故事中,象有吉祥、圆满等寓意,立象托举着整个大佛座具,造像风格为印度犍陀罗造像风格,与北周时期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后场面盛大而宏伟。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天降祥瑞是古代对当朝天子的赞许与肯定,也是帝王的象征词,代表着长长久久。在三组动物中,狮子造型的艺术风格有着很明显的中亚艺术的特征,由于北周时期当地民众大多为少数民族,北周与西域交流的影响,卧狮形象更加壮硕质朴。狮是百兽之王,整副动物座具形态生动,层次分明,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亚文化、印度文化于一体,为北周佛教造像艺术奠定了基础,也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做好了充分的历史铺垫。
大佛座具下的卧狮、卧鹿、立象石刻数量各为“九”。为什么座具下的三种动物数量都是九呢?众所众知,“九”是一个特殊的数字,在中国佛教文化中代表着吉祥,起初是龙形,后演变为阿拉伯数字模样。在佛教数字中对“九”使用比较广泛,如以偶数和“九”的积为主设置尊数和手数,例如十八罗汉、三十六手观音、一百零八手观音等,都喻有九的加倍数有着吉祥之意。在释迦牟尼胸前的万字符也是按照“九”的变形“十”字设计为四个顶端屈曲延伸的旋转叶,看着即可随风旋转,寓意无限生命力。“九”作为数之极,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最典型的代表为九五之尊。同时,“九”的谐音体是“久”,也具有长长久久、终极的涵义,即象征极致到轮回的寓意。

普贤变(采自数字敦煌)
综上所述,拉梢寺摩崖石刻造像中大佛动物座具通过吸收北周时期的绘画技法,将雕刻技法与彩绘完美结合,使得石刻造像座具上的每种动物造型健硕、简洁清晰。这种装饰独特的佛像座具的出现是在佛教文化背景下,实际上是围绕着释迦牟尼本生故事的典故而创作,象征着威武忠诚、吉祥、功德圆满的卧狮、卧鹿、立象以护法的身份出现在释迦摩尼说法座具中。追根溯源,动物浮雕座具是起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象征主义的造像传统。这些动物形象都与释迦牟尼佛有着密切关系,动物特征很是灵动,有些为佛的化身,有些是佛的象征,有些为佛的坐骑。“印度佛教多以台座、菩提树、法轮、等象征来证明佛陀的存在。”大佛座具,整个座具呈左右对称的构图分布,每层莲瓣与动物浮雕是从佛座中心向四面八方发散而成,是典型的“对称性构图”,这种构图在佛教艺术中很普遍,而正面中间的佛、卧狮、卧鹿、立象形象都是以“正面律”的形式出现,成为了整幅浮雕的视觉焦点,这类构图形式被巫鸿称为“偶像式”,侧面的菩萨、卧狮、卧鹿、立象等动物构图形式则属于“情节式”。总而言之,拉梢寺的动物座具石刻继承了古印度法人佛教造像风格,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又融入了北周造像的艺术风格,也正是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融形成了一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才形成了拉梢寺自己独有的“个性”。

文殊变(采自数字敦煌)

释迦八相图 5 世纪(萨尔那特考古博物馆藏)
注释
[1]董玉祥,藏志军.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J].文物,1985(5).
[2]杨森.拉梢寺大佛题记考跋[J].敦煌学期刊,2005(2).
[3]魏文斌,吴荭.甘肃佛教石窟考古论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8.
[4]胡庆红.合水石窟与石刻造像[J].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4).
[5]刘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 窟释迦八相图图像解说[J].敦煌研究,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