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
杜骏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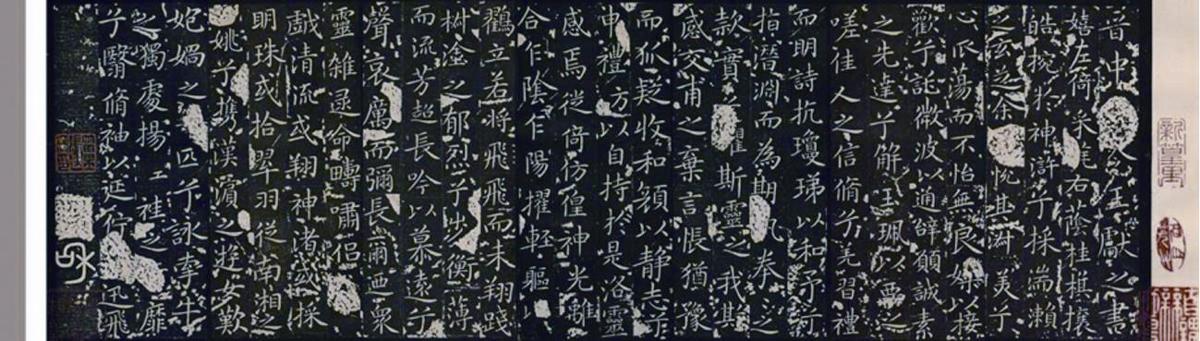
从时间的深处回溯,
我遇见金陵的桃叶渡,
它安坐东晋,
就在秦淮河与青溪的汇合处。
我遇见秦淮河水正值壮盛,
桃叶古渡,位于南京江南贡院以东,现仅存“桃叶渡碑”和“桃叶渡亭”。
秦淮河,为长江下游右岸支流。古称“龙藏浦”,汉称淮水,唐以后改称秦淮,由东向西横贯南京主城,注入长江,被称为南京的母亲河,历史上极富盛名。
青溪,为三国东吴在南京东南所凿东渠,亦名九曲青溪。年久湮废,今仅存入秦淮河的一段。
整日里波涛汹涌,
我遇见渡口上闪现着他,
一袭白衣,
白衣下的王献之,
字子敬,小名官奴。
和想象的一样,王献之
美风神,
褒衣博带,宽衫大袖,
和想象的一样,
他总在接送桃叶,在桃叶渡。
于是我以雉为贽,
深施一礼,
问子敬
这渡口是否真的是因她而名,
而一切故事又由她而起?
王献之笑而不语,
只看着水面上荡漾的春风,
而后,低声唱道:
“桃叶复桃叶,
桃树连桃根。”
这是他写给桃叶的歌,
王献之(344年-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东晋书法家、诗人、画家、官员,“书圣”王羲之第七子。
《晋书》上说:“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其行止气象,由此可知。

古秦淮河,曾浪涌波翻,其宽度也是后世秦淮河的数倍,与现今的清幽之象迥异。早年,在内秦淮河河底,考古部门曾发现南北朝时期的商船残骸,由此可见,那时是何等的水深湍急。
所幸我还记起,便悠然接诵:
“相怜两乐事,
独使我殷勤。”
大约,是千年的际会吧,
刹那间岸上的花都开了,
王献之
他点点头仰视天空,
似乎心事重重,
无心敷衍他人的样子,
但我却知道,他一向高冷,
小时候,
他曾和两个哥哥去拜访谢安,
徽之、操之闲话甚多,
只有献之,辞色清淡。
三兄弟走后,
有人问谢安道:
“王氏兄弟相比,谁好?”
谢安说,
王献之难得,
因“吉人辞寡”,值得赞叹。
又一次,献之和哥哥共在一室,
忽遇家中失火,
哥哥倉皇而逃,
传说,王献之的爱妾桃叶,经常在此渡口往来,亦时常为之心悸,于是,王献之在渡口亲自迎接,并为桃叶写下许多缠绵悱恻的情诗。
一说,桃叶为建康城的卖砚女,且为一位文采斐然的奇女子。《玉台新咏》里收录了桃叶的《答王团扇歌》三首和《团扇郎》等诗篇,其一如下:
“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
诗句质朴动人,一至于此。
中学课本里,有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大意是:黄门侍郎王子猷兄弟三人一同去拜访谢安,子猷和子重大多说些日常事情,子敬不过寒暄几句罢了。三人走了以后,在座的客人问谢安:“刚才那三位贤士谁更好一些?”谢安说:“小的最好。”客人问道:“何以见得?”谢安引《易·系辞下》说:“贤明的人话少,急躁的人话多。”
就此而言,谢安在王献之很小的时候,就已是他的知音,后来更成为他的伯乐。
《易·系辞下》里还说:“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大约指的就是谢安这样的人吧。
献之却呼左右进来,缓缓扶出,
神色恬然。
还有人传说,
献之睡在书斋的那一晚,
曾对夜盗置之不理,
到末了,才提醒道:
“偷儿,请留下祖传的青毡”
俱往矣。
我想起献之的文采,
也是美而惊心的寡言,
大约,料定了读者自有默契
抑或,是只顾自家意兴,
他写山阴道之行:
“山川自相映发,
使人应接不暇。”
只寥寥数语,
便已道尽眼中珍奇。
读子敬文章太久,
知道他的故事太多,
于是,
我这久远后的陌生人,
在东晋
《晋书》记道:(王献之)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兒,氈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王献之有文集十卷,始见于《隋书·经籍志》注文记载,称已亡佚。《新唐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有《王献之集》,《全晋文》收录有其文,《全晋诗》录有其诗。
可叹的是,王献之的传世名篇,只寥寥数句:“云生满谷,月照长空。潭涧注泻,翠羽欲流。浮云出岫,绝壁天悬。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这山阴道,是在绍兴城偏门外,与东跨湖桥相接,是绍兴西南通向兰亭的官道,原为一条石板铺砌的驿道。道旁有远山近水、小桥凉亭,晴雨冬夏,无不相宜。
王献之的文字流传后,山阴道声名远播,历代吟咏不绝。唐羊士谔《忆江南旧游二首 其一》:“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杜甫《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不识山阴道,听鸡更忆君。”宋陆游《病中怀故庐》:“我家山阴道,湖水淡空濛。”
羁绊于这贵重的奇遇,
如醉梦般沉迷。
于是,
见面后的每一天,
我都在这古渡口候立。
第六天,向晚时分,
我提起苏子瞻的诗句: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我问献之以为如何,
他居然难得地赞许说:“很好,
此生难免行色匆匆,
际遇在己,
而不在人”
说这句话时他还不知道,
自己行将早逝,
只四十三岁,
留下一千六百年的回忆。
一念在此,
悲伤难喻,
我去拜访他在乌衣巷深处的府邸。
那时已是第十一天了,

苏轼第二次被贬杭州时,遇老友钱穆父过杭州,两人得以重逢,此时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已经过了三年了。再次离别,苏轼以《临江仙》为钱穆父践行: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悵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太元十一年(386年),王献之病逝,年四十三岁。
酒酣耳热之际,
我问:
“你与令尊王羲之并称二王,
只不知高下若何?”
献之岸然道:
“自当不同,
足下有所不知,
昔年谢公也曾问过,
我也曾如此回答。”
我笑道:
“我确实知道此语,
可那时,谢安不赞同你的自诩,
曾说:别人不这么看。
而你却说:别人哪里知道?
子敬啊,
别人说你名列书中四贤,
莫非也不知你?
后世有唐人张怀瓘,
评阁下书法为第一等,说你挺然秀出,
说你情驰神纵,
还说你有若风行雨散,
说你于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晋书》记道:
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王献之以行书及草书闻名,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与张芝、钟繇、王羲之并称“书中四贤”。
唐人张怀瓘在《书估》中评其书法为第一等。王献之亦善画,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目其画为“中品下”。
张怀瓘说, “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后人如此厚爱,
莫非他们也不知你?”
献之正色回答:
“当然,
他们又哪里知道?
爱我,则由我,
非我,也由我,
他们又哪里知道呢?”
我喟然叹道:
“子敬啊子敬,
旁人说甘苦自知,
又有人说冷暖自知,
唯独你是于自身一切定评,
皆由自知矣。”
第十五日,
与王门子弟欢宴。
我又问献之,
“据说你见朋友着白色衣服,
便在衣上尽兴书写,
何以见我衣白多时,
孙过庭《书谱》转述说:
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

《宋书》卷六十二传《羊欣传》记道:
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
大意是:羊欣十二岁时,王献之任吴兴太守,很赏识他。王献之曾在夏天来到乌程县官署,羊欣正穿着新绢裙午睡,王献之在他的裙子上写了几幅字就离去了。羊欣原本善于书法,由此书法就更有长进了。
又是上好的袍襦,
却不动笔?”
献之黯然道:
“我既已知道,
足下自来世来,
我却往前世而去,
我与你甚相敬,
只世相意趣大异
又何以题衣裙?”
刹那间
我汗出如雨,
想起太极殿竣工时,
朝廷有意请子敬题榜,
不料他断然回绝。
要知道
那还是谢安转告,
而那时,
献之还在谢安公府里任长史,
他却依旧如此不假辞色。
我问献之此事时,
他曾告诉我:
王献之题书于裙的佳话,也载于唐张怀瓘的《书断王献之》:
欣着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而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

《世说新语·方正第五》:“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箸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
“书法是风流雅事,
又岂可为世俗所役,
否则,士大夫又与工匠之流何异?”
想到此节,我忽然领会,
这等话,如今已成绝响,
而他这样的人,如今已不复见矣。
世人爱王子敬,
爱他高迈不羁,
爱他风流蕴藉,
爱他清清峻峻。
而我,复又想起今日,
想起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后人,
题书敬畏于权贵,
著文干谒为功名,
于是,我不禁喃喃自语:
“唉,我辈卑微若此,
辗转红尘,一旦死去,
又有何面目于地下见你?”
献之闻言,
轻声慢语地问我:
“鬼神之事莫名,
生死之事尤不可谈,
世人凡遇不可解,皆称道灵异,
在史书里,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太元年间(376年—396年),太极殿落成,谢安打算让王献之题写匾额,以作为流传后世的墨宝,但难于直言,试探道:“曹魏时陵云殿匾额没有题写,就被工匠们误钉了上去,取不下来,只好让韦仲将(韦诞)站在悬挂的凳子上书写匾额。等匾额写罢,头发都变白了,衰老得仅剩一口余气,回到家告诉子孙们,此后再也不能用这种方法题写匾额。”王献之明白谢安的意图,正色道:“韦仲将是曹魏大臣,哪会有此等事!如果真有此事,正说明了曹魏德薄而不能长久。”
对世俗而言,为国之殿堂题匾额,是何等荣耀,但在深具士大夫气质的王献之看来,书法,本风雅事,岂能为人所役使呢?
王献之并非不近人情。张怀瓘评论说,王献之喜欢主动为人作书,但是“人有求书,罕能得者,虽权贵所逼,了不介怀”。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代书家的贵重传统——只是今世早已不存。
这里,难得之处还在于:王献之如此轻慢,谢安居然不以为忤,甚至有称许意。王献之、谢安的故事,大约就是高迈入云的魏晋风度吧。

莫非,此刻,
你我已在黄泉之下乎?
又或者是人生并无生死,
只有来去?”
我肃然答道:
“还是如我前时所诵,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如此而已。”
說罢,我看他若有所思,
忽然想起这是一句谒语,
这时,
山河失色,
树下风起,
于是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对献之谈起他死后的桃叶渡。
我谈起后人对他书迹的敬爱,
谈起课本里对他文字的称誉,
而桃叶渡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上巳节”,时任会稽内史的右军将军王羲之,召集筑室东土的一批名士和家族子弟,共四十二人,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今浙江省绍兴市西南)举办了首次兰亭雅集。谢安、谢万、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名士与会。会上共得诗三十七篇。
孔子看待鬼神之事的观点是:敬而远之,即保持敬畏之心,但也不要有过于亲近的念头。《论语·雍也》里记道: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这大概是中国人的普遍态度了。
那一年,王徽之和王献之都病得很重,王献之先去世。一天王徽之问侍候的人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听到子敬的音讯?这是已经去世了!”说话时一点也不悲伤。
然后,王徽之就要车去奔丧,一点也没有哭。王献之平时喜欢弹琴,王徽之便一直进去坐在灵座上,拿过王献之的琴来弹,琴弦怎么也调不好,就把琴扔到地上说:“子敬,子敬,人和琴都不在了!”说完就悲痛得昏了过去,很久才醒过来。
过了一个多月,王徽之也去世了。
那些传说并未休止,
总有一天这里将日日夜夜笙歌不息,
舟舫往来,
樯灯辉映,
晚生的李贺、李商隐,
甚至李白、王士祯、朱彝尊,
他们都会来感怀往昔,
在桃叶渡上临迹赋诗,
向他吟咏致意,
一时,这“桃葉临渡”,
竟成就了十里繁华,千古佳胜。
再后来,
从有渡无桥到有桥无渡,
斯文不再的朝代里
再也无人来此仰怀附丽,
岸边将惟留秋风落叶,
几许旧碑陈碣,
残存流水落花的记忆。
献之听罢,
也只是长叹一声,道:
“光阴无穷而人生如朝露,
天地无穷而万事皆在一隅。


清朱彝尊《临江仙》:“白鹭飞边舟一个,萦回几曲方洲。晚凉重过曝衣楼。笼灯迎竹外,摇橹到沙头。烟火空存桃叶渡,依然兰月如钩。十年霜鬓不禁秋。可怜新蝶梦,犹恋旧蚊帱。”
现代词人沈祖棻《临江仙》:“画舫春灯桃叶渡,秦淮旧事难论。斜阳故国易销魂。露盘空贮泪,锦瑟暗生尘。消尽蓼香留月小,苦辛相待千春。当年轻怨总成恩。天涯芳草遍,第一忆王孙。”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纳兰性德的《南乡子·烟暖雨初收》:
“别自有人桃叶渡,扁舟,一种烟波各自愁。”
生何以欢,
死不足惜,
只有我来,我见,我具此心而已”
于是,
我又问献之,
“倘若《桃叶歌》
曾遍响于江南吴声乐府,
后来却又销声匿迹,
你是否会觉得少些意趣?”
子敬道:
“不然,我为桃叶写
未有后人时,有桃叶,
未有桃叶时,已有我,
未有我时,早有人性。”
我对曰:
“千百年后,纵然物异人非
但此心依然在人世里,
而人之情感,无增无减,不变不易
可谓不朽矣。”
王献之《桃叶歌》,有论者以为,诗句颇有些昵而佻,实际上,《桃叶歌》原是乐府吴声流韵,本就以真纯有情为要;史载,《桃叶歌》至南朝陈时犹“盛歌”之。
《桃叶歌》也一直保存在明乐的乐曲之中,至今日本的明清乐中还有这首歌曲。
“桃叶临渡”何以竟成千古佳胜?《桃叶歌》何以久传不衰?此中,绝非只是风流佳话,而是有来自人性深处的、毫不做作的感情。
那些美好天然的,才是爱情文学的源头里最宝贵的。
《古今乐录》评《桃叶歌》赋诗的起因:“缘于笃爱,所以歌之。”而这一点笃爱,镌刻于王献之那样的风骨,才如此让人难忘。
千百年后,我们已无从还原王献之的情感生活,更无从知道桃叶的本事。
也许桃叶终究是一场文学的传说,而史书里的王献之,确曾先后娶郗道茂及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为妻。其中,郗道茂出身名门,父亲郗鉴是东晋名臣。两人为表姐弟,自幼青梅竹马,成婚后更是感情深厚。
不料,婚后第七年,王献之接到一道圣旨,皇帝命他尽快与郗道茂离婚,然后择良辰吉日迎娶新安公主,因为公主暗恋王献之已有多年。
即使如此,王献之也多次拒绝此事,并告诉公主,他和妻子郗道茂已许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请她和皇帝不要强人所难。
为了断绝公主的念头,王献之不惜忍痛烧残双脚。不料新安公主也极为痴情,誓死要嫁给王献之。最终,为王氏家族命运计,王献之忍痛与郗道茂离婚,迎娶新安公主。
于是,斜阳残照里,
又一次,我们在渡口驻足,
王子敬再唱起《桃叶歌》,
而临别的我,又再对他应和: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世说新语·德行三十九》记道:很久以后,王献之临终病笃,请道士来家消病祛灾。道士问子敬:“你觉得你这一辈子犯过什么错误?”,王献之答:“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意思是,我这一辈子几乎没有后悔之事,唯一让我愧疚和懊悔的,就是跟妻子郗道茂离婚。
王献之所赋《桃叶歌》三首:《其一》“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其二》“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连两乐事,独使我殷勤。”《其三》“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王献之临终时说的那十二个字,才是他真正的《桃叶歌》。
而我们,今天怀念起王献之,也许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一世的万丈烟尘里,再也不会遇到他那样的书法家和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