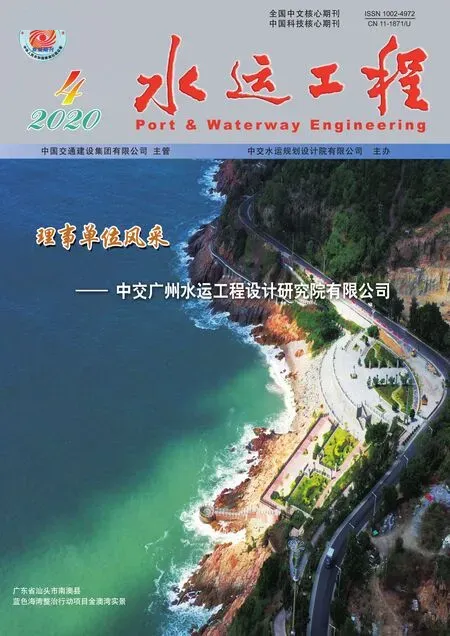长江干线水运量和承载能力研究
冯宏琳,张 艺,韩兆星,孙 平,徐 力,魏雪莲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28)
长江干线是我国横贯东中西部地区水路运输大通道,素有“黄金水道”之称,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我国正在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1]。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护好长江水资源及环境、科学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开展了长江干线水运量和承载能力研究。承载能力研究在资源环境学科较为广泛和普遍,在水运行业国内外研究均较少。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长江经济带确立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导向,我国学者开展了一些相关探索性研究。徐湘文等[2]将长江中游航道货运承载能力定位为航道所承载的总货量最大值,提出了基于OD货流矩阵的算法;刘怀汉等[3]提出了多目标协同下的长江航道承载力研究构想。在此构想下,马驰[4]研究了长江下游航道承载力指标与评价方法,赵艺为等[5-7]研究了长江航道承载力概念、影响因素内涵及体系构建,均尝试通过多目标多因素综合确定航道可开发的最大尺度和通过能力。本文基于已开展的长江干线航道规划标准研究,深入分析了长江水运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提出了以环境容量约束为条件的长江水运承载能力内涵和算法,可为确定今后长江干线航道合理运输规模和航道发展规划标准提供技术依据。
1 长江干线水运基本情况
长江干线航道自云南水富至长江口,全长2 838 km。上游水富至宜昌1 074 km,目前水富—涪陵可通航500~3 000吨级船舶,涪陵—宜昌三峡库区段可通航5 000吨级船舶。中游宜昌—江西湖口900 km,目前宜昌—武汉段航道可通航3 000~5 000吨级内河船舶,武汉—湖口段可通航5 000吨级海船。下游湖口—长江口864 km,目前湖口—芜湖段可通航5 000~1万吨级海船,芜湖—南京段可通航1万~2万吨级海船,南京—南通段可通航3万~5万吨级海船,南通—长江口段可全天候双向通航5万吨级海船。为提高运输效益,交通部门近年来开始根据水位季节性变化情况,按月、旬向社会发布航道维护水深,利用中洪水期通航更大的船舶,并开通了城陵矶—芜湖海轮航道。
2016年,长江干线水运货运量达22.1亿t,2005年以来年均增长8.6%。其中,江海直达运量为12.9亿t,占总量的60%左右;海进江运输占绝对主导,2005年以来海进江运量规模和运输范围进一步提升。沿江企业生产所需的80%的铁矿石、83%的电煤和90%以上的集装箱运输是通过长江水运完成的。长江水运在长江经济带煤炭、金属矿石、水泥、矿建材料等大宗散货运输和集装箱、汽车滚装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支撑和促进了沿江产业密集带的形成和发展。
长江干线分布有上海、武汉、重庆3大航运中心和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以及16个全国主要港口,拥有13个吞吐量超过亿吨的大港。长江干线完成的水运货运量、货物周转量约占区域全社会货运量的15%和45%,长江水运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中东西向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长江干线水运产生的环境影响
长江干线水运利用天然通道资源,在解决大量物资运输需求的同时,实现社会物流成本、土地占用、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综合效益最优,是最经济节能环保的绿色运输方式。一艘5 000 t长江货船载货量相当于1列由100节重载车皮组成的火车或100辆载质量50 t的重型卡车的运能。水运每吨公里能耗是铁路的12、公路的114,污染排放量是铁路的11.2、公路的115。
长江干线水运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包括对水生态和水生物的影响、岸线资源的占用以及废水废气等污染排放。与沿江工业、农业、城镇生活产生的对长江水生态、水环境以及大气环境等影响相比,长江干线水运产生的影响甚微。据不完全统计,长江全流域年废水排放量超过300亿t,其中与港口和船舶相关的废水排放所占比不足510 000。
水运对水生态和水生物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航道整治阶段和船舶运营阶段。航道整治需要临时或永久占用局部水域,对部分水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繁殖等活动产生一定影响。“十三五”期长江干线航道整治项目占用相关保护区水域面积不足2.5%,不会造成生态功能的总体退化,通过严格落实环境保护规定,并采用增殖放流、生态修复等措施影响可进一步减弱。船舶运营中螺旋桨可能会对大型鱼类水生物造成伤害个案,与非法捕捞、非法采砂、大型涉水工程建设对长江水生物带来的不良影响相比微乎其微。随着长江干线船舶大型化趋势发展,近年来营运船舶数量和密度呈明显下降态势,对鱼类水生物影响总体可控。
港口码头建设会占用一定的岸线资源。截至2015年底,长江干线港口码头利用岸线约占自然岸线总长度的15%。2016—2017年,在长江经济带领导小组推动下,沿江各省市陆续制定了非法码头专项整治方案,对沿江非法码头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域内的码头开展了整治工作,共整治恢复自然岸线146 km。
水运产生的污染主要来自运营船舶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排放性污染。2016年长江干线共接收船舶含油污水6.9万t、船舶垃圾2.5万t,全线5个固定洗舱站提供洗舱服务约270艘次。目前,交通行业正在大力推进港口岸电、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受处置等环保设施建设,长江干线水运产生的排放性污染有望持续改善。
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实施以来,长江水运强化绿色发展顶层设计,严格执行国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相关法规政策,大力建设生态航道、绿色港口,切实开展码头岸线专项清理整治,严格防控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排放,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目前长江干线水运环保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局部航道建设存在与鱼类自然保护区的矛盾;船舶违规使用燃油和违规排放的现象依然存在;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仍然不足;推进长江水运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3 长江干线水运发展面临的形势和需求
未来长江经济带将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建陆海双向全方位开放格局,在我国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中发挥好引领示范和战略支撑作用。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长江干线水运量将保持平稳增长,能源原材料等大宗散货仍然是主要货种,但增速趋缓;集装箱、商品汽车滚装等运量增长加快,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2035年预测长江干线水运量将达36亿t,其中江海直达量为21亿t,煤炭、金属矿石、矿建材料、集装箱货运量分别为5.9亿t、5.3亿t、5.7亿t、7 200万TEU。货运船舶运力增速放缓,船型继续向大型化、标准化发展,船舶安全环保技术性能显著提升。
4 长江干线水运承载能力
4.1 水运量和承载能力的内涵
长江干线水运(货运)量是指在长江干线水富—长江口区间,航行的船舶(包括内河船、江海船和海船)在一定时间(通常指1 a)内实际运输完成的货物质量。
“承载能力”字面原指某一事物“承”与“载”的能力,一般指空间上的最大容量或力学上的最大限度。目前,长江干线水运承载能力在学术理论研究上尚无明确的科学定义,本文引入资源环境学科领域的承载能力概念,考虑长江水运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影响,界定长江干线水运承载能力的内涵是:在一定环境容量条件下,航道上所容许通过的船舶数量或货运量之和,即一定环境容量条件下的航道通过能力限度。
航道通过能力不同于航道内实际发生的水运货运量,它反映的是单位时间或特定时间段内能通过航道某一区段(或某一地点)的船舶或货物潜在的最大运输能力。常用计算公式方法有西德公式、苏南公式、长江公式等,本文选用适用于天然航道的长江公式[8]。
4.2 承载能力研究思路和计算方法
从长江水运产生的环境影响来看,航道建设维护期、港口建设运营期产生的影响可通过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制度和重大工程修复补偿措施加以避免或大幅减轻。运营船舶产生的排放性污染由于是流动性污染源,给全面治理和防控带来一定的困难,今后随着航道条件改善、船舶性能的提升以及监管覆盖力度的进一步强化,将得到逐步改善。
考虑未来长江干线水运发展不增加总体环境负担,设定承载能力的环境容量条件为船舶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长。船舶排放污染物主要有船舶废气中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船舶废水中的生活污水、船舶残油、化学品洗舱水以及船舶固体废物垃圾。经分析,选取了船舶氮氧化物、船舶残油和船舶垃圾作为废气、废水、废固的3个主要控制指标,明确了环境约束条件,引入船舶密度公式(式(2)),建立了航道通过能力(式(1))与船舶污染物排放控制即环境约束项条件(式(3))之间相关联的长江干线水运承载能力的算法,即:
航道通过能力计算公式(长江公式):
W=31.536×106CPF1F2F3F4/T
(1)
船流密度计算公式:
(2)
环境约束项公式:
(3)
式中:W为航道双向通过能力;D为航道双向船舶密度(艘a);N为船舶氮氧化物;Q为船舶含油污水;L为船舶垃圾;C为上、下行货运不平衡系数;P为标准船队载质量(t);F1为年通航期系数;F2为非标准船队影响系数;F3为港口、航道、运行调度产生运输不平衡影响系数;F4为考虑非运输船舶通过控制段的影响系数;T为标准船队安全通过计算断面的时间;t为船舶通过断面间的运行时间;n为氮氧化物排放因子;w为断面船舶平均功率;q为船舶含油污水产生系数,依据船检规范和实船数据选取;l为单位船员垃圾日产生量;r为船舶对应船员数量,依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选取;N现状为船舶氮氧化物现状值;Q现状为船舶含油污水现状值;L现状为船舶垃圾现状值。
基于未来长江干线各段航道规划推荐通航标准,选取宜宾、万州、三峡、武汉、安庆、南京、长江口共7个典型断面,预测得出船舶吨位结构和船舶密度,通过公式组迭代试算,计算得出长江干线航道通过能力和水运承载能力以及分别对应的船舶污染物排放指标值,见表1、2。

表1 长江干线航道通过能力和水运承载能力计算结果
注:长江干线全线能力根据各断面航道通过能力,考虑运输组织、运距等因素综合测算。

表2 长江干线不同运输能力对应的污染物排放值
在推荐的长江干线航道标准和预测的船舶运输组织条件下,采用长江公式计算长江干线航道设计综合通过能力为58.9亿t。航道在达到此通过量时相应的船舶污染物排放指标与2016年现状比,除硫氧化物大幅降低外(降低95.6%),氮氧化物、船舶残油、船舶垃圾、生活污水分别增加48.1%、66.3%、12.1%、11.8%。
假定船舶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长为环境容量约束条件,计算得出长江干线承载能力为36.7亿t,基本能够满足预测2035年的长江干线水运需求量。从船舶污染物排放具体指标来看,与2016年现状相比,船舶残油增长为零,氮氧化物、船舶垃圾、硫氧化物、生活污水分别减少10.8%、36.4%、97.8%、36.3%。
5 结论
1)考虑长江水运量平稳增长、船舶标准化大型化以及船舶密度降低等总体发展趋势,基于长江干线航道规划推荐标准,预测未来船舶吨级结构和不同船舶密度,并结合船舶油品质量强制提高等技术因素,计算得出了未来长江干线航道通过能力和一定环境容量条件下(假定为船舶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长)的水运承载能力。
2)如果考虑环境容量允许适度增长,或进一步优化船型和运输组织、改善提高船舶技术性能以及清洁能源应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进步等措施的强化,长江干线水运承载能力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3)研究认为,未来长江干线水运承载能力合理区间为36.7亿~58.9亿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