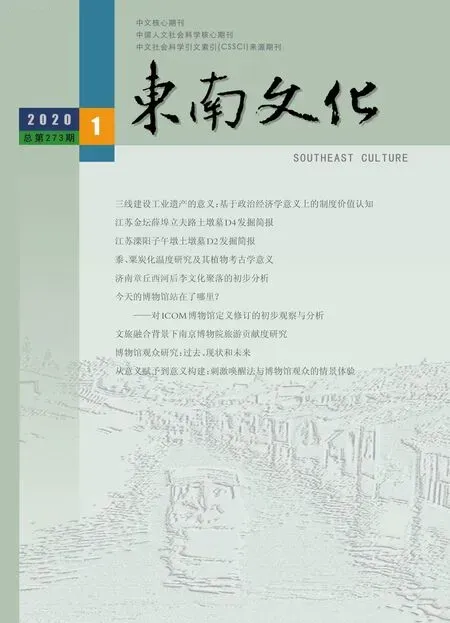济南章丘西河后李文化聚落的初步分析
张 溯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012)
内容提要:济南章丘西河遗址目前经过了三次考古发掘和勘探。遗址面积巨大,是一处典型的后李文化聚落。遗址沿河分布,具有开放性、季节性、迁徙性的特点。其开放性的布局、小型化的经济单元与其渔猎采集和初级种植饲养两合的经济形态是相适应的。西河人在捕捞、采集、栽培季过着季节性半定居生活,与章丘小荆山遗址存在区别。
西河遗址是后李文化典型聚落之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龙山三村西约400米处,东距城子崖遗址约1600米。20世纪90年代曾被称作“龙山三村窑厂遗址”[1],因遗址西靠巨野河支流西河,后来被称为“西河遗址”。该遗址于1987年山东省文物普查时发现,被当作唐宋时期的遗址。1991年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广饶县博物馆王建国于西河遗址断崖上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陶片,从而引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重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很快组织人员对其进行了勘探和发掘,收获了一批年代较早、特征鲜明的遗迹和遗物[2]。1997年和2008年,为配合102省道的拓宽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3]。2005年11月,为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河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聚落布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章丘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以确定遗址分布范围、聚落布局、文化堆积情况,并初步查明后李文化房址的分布区域、规模和数量,是否存在墓地和环壕等遗迹[4]。此外,城子崖博物馆也曾多次调查该遗址,并曾在遗址的西北部采集到后李文化时期的磨盘、磨棒等遗物。这些考古工作为分析西河遗址的文化特征、年代分期、聚落布局和社会形态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
一、历史地理环境
章丘市地处泰沂山北麓,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北冲积平原交接地带。其南为泰沂山脉,东为长白山,西有巨野河,北为小清河、黄河,从而使该地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境内面积约1700平方公里。这一区域的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地面坡度0.23~0.9%,海拔高度30~75米。发源于泰沂山北麓的巨野河、绣江河和漯河自南向北贯穿全境。境内的山前冲积平原拥有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自然条件优越,是人类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
章丘最早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5]。经过80余年的考古工作,章丘地区建立了完整清晰、先后承袭的文化谱系,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到周秦汉等历史时期的遗址均有发现。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巨野河、绣江河和漯河三条古河道两岸。普查发现章丘区内约有120余处遗址,是山东地区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西河遗址位于泰沂山北麓的冲积平原上,遗址地势平坦,海拔55米,属典型的河旁台地遗址。巨野河的支流西河源于泰山之阴,自南向北流入小清河。西河在遗址西侧蜿蜒曲折。现在的西河有陡峭的断崖,这是由于数千年来河流冲刷河道下切形成的,七八千年前,该地当为平缓的河漫滩。西河北流约1公里,与流经城子崖遗址的关卢水汇合,入巨野河。经城子崖周边区域考古调查,在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遗址52处,其中史前遗址包括后李文化遗址1处[6],大汶口文化遗址5处,龙山文化遗址14处,岳石文化遗址8处(图一)[7]。西河遗址(后李文化为主)、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为主)、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春秋为主)和东平陵城遗址(战国、汉代为主)[8],彼此相距仅几公里之遥,为不同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

图一// 西河遗址位置及周边遗址分布图(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超提供的城子崖周边区域考古调查遗址分布图改绘)
二、考古收获
西河遗址作为一处遗存丰富、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后李文化聚落,为探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十余年来,西河遗址共经过三次发掘,一次较为详细的勘探(图二)。
(一)发掘收获
1991年7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砖厂征地范围内布探方19个,发掘面积450余平方米,清理后李文化房址2座(编号F1、F2),其中F1保存较好。出土一批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此外,在断崖上还发现了3座残房址[9]。
1997年,为配合山东102省道(以下简称102省道)的修建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河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区位于第一次发掘区南偏西约150米处。揭露面积1350平方米,清理后李文化房址19座(编号F51—F69),灰坑9个。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有釜、双耳罐、壶、圈足盘、碗、钵、匜形器、拍子、支脚和陶猪等;石器有斧、锛、镰、锤、研磨器、磨盘、磨棒、支脚、砺石等;骨器有锥、簪、针等[10]。
2008年,为配合102省道拓宽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区域紧邻2007年发掘区的北侧,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第二次发掘区的边缘,因此可以将两次发掘区的平面图进行拼合。本次发掘面积1070平方米,清理后李文化房址8座和灰坑10个。房址面积较大,个别达到70余平方米。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釜为主,此外有少量钵、碗、罐、圈足盘、匜、壶、拍、支脚等;石器有锤、斧、锛、磨盘、磨棒、支脚等[11]。
(二)勘探收获
为了解遗址文化堆积情况,2005年1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详细勘探。由于遗址环境较为复杂,人为破坏现象严重,地表附着物多样,因此采用分区勘探的方式进行。根据遗址的分布形态和既有保存现状将遗址分为A、B、C、D四个探区。在每个探区内,确定勘探基点,采用5×5米排孔的方式进行普探。对于文化堆积较丰富的区域,采用梅花孔加密,以确定遗迹范围。勘探过程中详细记录探孔土样和遗迹的埋藏情况。工作结束后,使用全站仪对整个西河遗址进行了测绘,实际勘探面积约71 000平方米(图二)。
勘探结果表明,西河遗址范围东至龙山村以西约100~200米,西至巨野河,南至胶济铁路,北至砖窑取土场北断崖以北约50米。整个遗址分布在西河东岸200余米的范围内,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
通过勘探和发掘可知,西河遗址存在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周代、汉代、唐宋和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后李文化为主,其他时期仅有少量遗迹(以墓葬为主)和遗物,未见文化层。如2008年发掘4座龙山文化墓葬和数座晚期墓葬,2005年勘探发现有周代陶窑1座,但均未找到相对应的文化层。这可能是因为原来遗址地势较高,上部文化层已被破坏造成的。现今后李文化的地层埋藏并不深,一般在40~50厘米左右。
后李文化遗迹以房址、灰坑为主,多分片分布,可分成若干个片区。勘探共发现房址26座(F001—F026),集中分布在A、B两个区。A区位于102省道以南,南至胶济铁路以北约100米处,西至废品收购站,东至龙山三村以西约100米处,地表附着物为麦苗。该地地势平坦,勘探面积约27 000平方米。发现房址12座,分布于从102省道至往南约130米的生产路之间。其中有5座位于探区西北,分布较分散;另7座偏东,分布较集中,大致可以分成东西两排。
B区位于102省道以北,北至西河,东至砖窑取土场西断崖,西至南北向生产路。该地为苗圃,地表种植椿树、刺槐等树木。勘探面积约15 500平方米,发现14座房址。12座分布于靠近东部砖厂50米内,另2座稍偏西,其中F009位于砖厂西断崖。
C区位于B区西侧,两区之间有南北向生产路相隔,处于西河河道“几”字形拐弯处。地势微隆起。勘探面积约19 000平方米。没有发现后李文化遗迹现象。探区西部探到有少量红烧土和夹砂灰褐陶片。地层深度一般在1.4米左右到生土,北部部分探孔深达2米不到底,多为周代灰坑。
D区位于砖窑取土场北侧。地势微隆起,地表为麦田。勘探面积约9500平方米,没有发现遗迹现象。不过西距砖厂断崖90米和130米处都探到夹砂红褐陶片,个别探孔发现灰色炭粒。
勘探发现的房址面积多在25~36平方米左右,房址内堆积多为灰褐填土,夹杂较多的红烧土、草木灰、炭粒,并发现有烧土面和灰土面。遗物有红褐色夹砂陶片,个别房址堆积内发现有兽骨、砾石、碎石块。
(三)年代分析
西河遗址的测年数据有三批。1991年有4个数据:F1内采集的3个泥炭数据为距今7974、7908、7726年;T11第4层采集的泥炭距今8411年[12]。后经重新校正,F1内的3个数据集中于公元前6100—前5900年[13]。1997年发掘获得7个测年数据,除个别稍偏晚之外,其他数据集中于公元前5500—前5400年前后[14](表一)。第二批数据后经孙启锐重新校正,大多数位于距今7800—7500年前后[15]。2008年发掘获得11个炭化样品,被送至北京大学进行AMS测年(表二)。其中F303①样品的3个数据明显偏晚,当是受到晚期物质的干扰,应予排除。其余9个数据可分两组,其中8个来自炭化种子和果实的测年数据较早,在公元前6070—前6030年之间;另外1个数据偏晚,为公元前5720—前5625年之间。H358中出土的炭化种子测年结果为公元前6075—前5900年[16]。
发掘区内所有的后李文化遗迹均开口于③层之下,而1997年于④层中所采集的样品测年为距今8411年,样本可能与后李文化没有关系,且④层下没有发现遗迹单位,孙波也认为④—⑥层属于自然堆积[17]。过去有学者认为西河遗址的上限可能到距今8500年,甚至早至9000多年[18],目前看来这一观点缺少足够资料的支持。西河遗址的上限当以距今8100年为善,其下限,应在距今7300年,甚至更早,遗址的繁荣期在距今8000—7700年前后。
三、聚落布局分析
西河遗址面积较大,近20万平方米,但是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相比,在遗迹分布和分区上存在较大差异。遗址内有遗迹的地区分布在几个片区,且遗迹以房址为中心,间有灰坑,未发现其他遗迹。其他区域也发现少量陶片,但是遗迹少有发现,推测为活动区。在这些区域里可能也存在我们没有探到的遗迹,但这种情况即便有,应该也是极少的。因此,排除掉可能漏探的情况,这个区域的功能就值得重新思考。也就是说,现在所估算的20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应该代表了一个较长时间段内西河人的活动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城子崖周边区域系统调查所发现的龙山二村遗址,该遗址位于龙山二村西南1公里处,中心地势隆起,四周较为平坦,地表为麦田。其西部被砖厂取土破坏,南北长300、东西宽2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调查发现有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汉代陶片[19]。龙山二村遗址位于胶济铁路之南,西河遗址位于铁路之北,两者之间有一块洼地,原来很可能是连在一起的,只是后来取土和修筑铁路被分隔成两处。如是,则西河遗址的面积应该在40余万平方米(图三)[20]。当然,两者也不一定是共时的,有可能是古人沿河迁徙居住所形成的不同居住区,类似于月庄遗址。月庄遗址南北长1400、东西宽约330米,面积46万平方米,跨月庄和张官两个自然村。过去曾经将月庄遗址和张官遗址作为两个遗址,后来发现遗址基本是连在一起的,亦是人群沿河迁徙所选择的不同居住片区[21]。
西河遗址沿河分布,聚落布局相对分散,可分成三、四个片区,其中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即1997年和2008年的发掘区及其周边(图二、图四)。该地地势较高,近乎三面临水,环境优越,适宜人类居住和生产生活。三次发掘共清理32座房址,绝大部分为圆角方形,均为半地穴式房址,大多数房址没有发现柱洞,台阶式或斜坡式门道位于南侧偏西。面积较大的房址穴壁和居住面经过烧烤等处理。这组房址处于一个层位上,可视作一片具有共时性的社区[22]。
根据房址的面积、结构和功能,1997年和2008年发掘的27座房址可以按照有无灶分成两类。
1.有灶房址
11座。这类房址面积一般较大,按灶的数量分为三灶、双灶、单灶,三灶房址占大多数。
(1)三灶房址
7座,面积较大,在30~75.8余平方米之间,多在5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F306面积75.8平方米。灶呈三角形排列,每组灶有3个石支脚,呈三角形向内倾斜,半埋入地下筑成,有的灶上还放置有陶釜,有的灶底部可见挡火的灶门石。
这类房址制作较讲究,居住面多涂有一层黄膏泥,并加以烧烤,形成较硬的烧结面。内部空间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功能区:灶区、睡眠区、储藏区、工作区。睡眠区一般2~4平方米,位于房内一角。储藏区多位于东南角或西北角,发现有数件大型陶釜和支撑陶器的支垫石或陶片。工作区多位于灶址周围,一般发现有陶容器、石质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
(2)双灶房址
2座,面积分别为28、38平方米。局住面平整,局部经烧烤或铺垫一层草木灰。两灶呈东西向或南北向排列,其中一组为主灶,均由三个石支脚和一个灶门石或挡火陶片组成。釜、壶、碗、钵等陶器多发现于灶北部。储藏区一般位于房址东南部,发现有大型陶釜和垫片。
(3)单灶房址
2座,面积分别为25、30平方米。居住面或穴壁经过烧烤,中部为灶,由3个石支脚组成,有的也用陶支脚代替。储藏区位于东南部或西北部。居住面上发现有石斧、石磨盘或兽骨、兽牙等。
2.无灶房址
16座。除个别房址外,大部分房址穴壁和居住面没有加工痕迹。房址面积一般较小,大多数20平方米左右,只有4座达40余平方米。这些房址位于有灶房址之间,且居住面多未经加工,当为有灶房的附属建筑,并不适合居住。房址内多出土石磨盘、石磨棒、自然石块、兽骨、陶拍等遗物。如在F60居住面上发现大量陶片、石块,有的石块3块一组呈三角形排列,当是放置陶釜的支垫;F302中发现石块、石磨盘、石磨棒和大量釜、罐、圈足盘、钵的陶片;F303中则出土石磨棒和陶拍。这种房址当为制陶、制骨和加工石器的手工操作间,也作为储藏室使用。
1997年和2008年发掘区内共发现4组打破关系的房址,其北部B区的房址和南部A区的房址则少有打破现象,分布也较为分散。这说明,该区域是一个片区的中心。这显然是因为该地具有更为理想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水,更有利于获取水中的动植物资源。同时,这些具有打破关系的房址,并不存在于有灶房址之间,而多在无灶房址或有灶房址和无灶房址之间。有灶房址之间并无打破现象,说明这些房址很可能是同一时期并存,片区内有统一规划。有灶房址可分成南北两排,并有两两成对现象。如F304和F306、F62和F63、F67和F66,这些房址均为三灶房址;F68和F61,均为双灶房址;F58和F53,均为单灶房址。在勘探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房址成对现象。如在B区的F003和F004,F006和F007;A区的F014和F015,F019和F020,这些房址周围相对空旷,房址多成对出现。
从房址内的分区和出土遗物分析,有灶房址属多功能房屋,这与后世的房址功能不同。人们在房内炊煮、饮食、加工、储藏、睡眠、制作骨器和石器等。每座有灶房址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有灶房址均为多功能空间,但是,并不能以房址空间大小来确定居住多少人,因为睡眠区并不大,而且储藏、加工坚果和农作物、饮食均在一个空间内,仅够一个大家庭数人使用。两两组合的房址可能是为了解决更大范围内的生产如采集、种植、狩猎等所需劳动力而采用的合作模式。因为人群组织能力有限,不可能组成后世那样的如氏族一类的大型社群组织。而且蒸煮食物的效率有限,这样一个小型经济单位共同从事生产活动,按主干家庭[23]生产消费是较为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两个主干家庭组成经济合作单元,当然这一时期单元之间的关系多是血缘的。可与之对比的是西河遗址西北20余公里处的小荆山遗址,其时代与西河相当且稍晚。在遗址中发现有环壕和墓地,墓地有3处,分别位于环壕内、外侧沟沿、环壕外,墓地分布分散,并没有统一的公共墓地[24],且每一处规模都不大,保存最好的3号墓地仅21座墓葬,分成3排。一排墓葬应该对应一个主干家庭,相当于西河遗址一个有灶房址。三排共20余座墓葬,构成一个扩大家庭。这也说明后李文化并不存在大型的社群组织,其人口组成以从事狩猎采集和初级饲养栽培的合作单元构成,相当于一个扩大家庭的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同居住,死后葬于一处。
动植物遗存分析表明,西河聚落属于渔猎采集和初期农作物种植加家畜饲养的两合经济形态。2008年发掘过程中,我们在所有的遗迹单位中都采集了浮选土样。吴文婉对发掘所采集的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后发现,202粒炭化种子(果实)来自18个科/属/种,种类丰富,包括稻、粟、豆科、禾本科、狗尾草属、稗属、牛筋草、莎草属、薹草属、藨草属、藜属、苋属、菊科、野西瓜苗、罂粟科、葡萄属、桑属、山桃。其中稻、粟、豆科、藜属、苋属、葡萄属、山桃是人类食物的来源。食物来源以采集为主,开始栽培并驯化某些粟类作物[25]。值得一提的是发现炭化稻米74粒,集中出土于H358,经鉴定属栽培稻。这种现象说明,稻米很可能是外来的,而不是当地种植,否则应会分布于更广泛的遗迹内。一般认为稻作农业南方起源较早,在江苏泗洪韩井、顺山集,安徽淮北石山子、宿州古台寺、小山口都发现有与后李文化相似的文化遗存[26],后李文化所发现的水稻遗存当来自于淮河地区[27]。
西河遗址三次发掘共获得动物遗存9279件,可鉴定标本5197件。经宋艳波鉴定,动物种属包括牛、麋鹿、斑鹿、小型鹿、猪、小型犬科、蚌、螺、鲤鱼、草鱼、青鱼、鳖、鸟、竹鼠、小型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等,以大量的鱼类、鹿、猪、鸟类、软体动物为主,猪可能经过驯化,其余均为野生动物[28],说明渔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比重。
西河遗址属于以采集渔猎为主、植物栽培为辅的生业经济。研究表明,在稳定的定居农业产生之前存在一个渔猎采集和初级栽培饲养并存的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这使人类不得不广泛获取资源以满足生活所需[29]。这种低水平的生业经济方式不能满足全年的生存需要,因此,在春季时,人群选择水草丰美的河湾地渔猎采集和种植,待秋天收获之后离开,回到山林从事狩猎活动。西河遗址中许多房址内保存有大量陶釜,有的还有较重的石磨盘和磨棒,可能这些工具是适宜该地使用的季节性用品,不方便带走。
四、结语
巨野河河道蜿蜒曲折,西河聚落紧靠河岸,沿河1.4公里范围内都有分布,面积达40万平方米。目前,山东共发现后李文化遗址15处[30],最西缘为长清月庄遗址,最东缘为诸城六吉庄子遗址,大多数遗址位于泰沂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地带。这些遗址均滨河而居,坐落在黄土状堆积的台地上,沿河流方向是遗址的长轴,从而使聚落平面上呈带状。在山前平原地带的河边选址聚居是后李文化聚落分布的普遍规律,这反映出后李文化先民对河流与山地多样性资源的依赖,也是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体现[31]。渔猎、采集和初级种植饲养为后李文化先民主要生存来源,属广谱类经济形态[32],对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
西河遗址规模巨大、文化堆积单薄、居址分片分布。居址呈现断续分布的现象,当是人群沿河迁徙的结果,当然也有两个或更多居址区同时存在的可能。这显示西河聚落属于一种松散的开放性结构[33]。房址保存相对完整,并存在两两组合的现象,当是小型化经济合作单元的反映。这种经济单元相当于一个扩大家庭,人口从数人到二三十人不等,又以血缘关系的远近分成二、三个主干家庭。主干家庭居住在一个或两个临近的房子内,死后则葬在一起。参考小荆山墓地[34],一个扩大家庭(相当于一个小家族)葬于同一个墓地,主干家庭葬在一排。小型化的经济单元与其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因为这种低水平食物获取方式,当扩大家庭进一步发展时,主干家庭就会分裂出去,从而维持人群的小型化。整个聚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自然也不存在大型社群组织。
经考古勘探,西河遗址没有发现环壕和墓葬。就现有资料看,小荆山遗址是后李文化遗址中唯一的环壕聚落[35]。在已发掘的后李文化遗址中,只有小荆山遗址、后李遗址[36]、月庄遗址[37]发现有后李文化墓葬,其他遗址均未发现。小荆山遗址靠近山区,墓地分散于数处,月庄遗址的时代则较晚。西河聚落为季节性使用,暖季人群来此采集、种植和捕捞狩猎。而当采集种植季节结束之后,人们分散至山林从事狩猎等活动。房址内的大型储藏器也被遗留下来,方便随身携带的完整石器则少见于房址内。下一个暖季到来,人们回到故地,重修旧居或筑造新的居址,因此使西河遗址形成不同的居住片区和开放式的聚落布局。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小荆山遗址背靠长白山,可以兼顾平原、河流和山地多种不同的资源来源,具有更为优越的地理环境,这也使其比西河遗址具有更稳定的定居性,环壕、墓葬应是这种定居生活的反映。或许这也是西河遗址的房址大多没有柱洞,而小荆山遗址的房址则普遍存在柱洞的原因[38]。因为小荆山遗址的居民种植农作物、采集和狩猎都可以在聚落周边完成,因此注定更早地迈入稳定的农业社会。
章丘西河后李文化聚落为分析距今8000年前后山东地区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农业的起源、聚落结构和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早期人类为适应不同的环境而采用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迈入农业社会提供了多样性的标本。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龙山三村窑厂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2]佟佩华、魏成敏:《章丘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94年2月20日第3版。
[3]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0期;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城子崖博物馆:《章丘市西河遗址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4]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西河遗址勘探资料。勘探工作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玉富、张溯和章丘市博物馆孙涛带队完成。勘探遗迹编号为三位数字,即从001开始编号。
[5]傅斯年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6]笔者赞同孙波的观点,认为调查发现的龙山二村遗址与西河遗址当属于同一个遗址,即龙山二村遗址属于西河遗址的一部分,西河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与月庄遗址相当。
[7]朱超、孙波:《章丘城子崖周边区域考古调查报告(第一阶段)》,《海岱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8]同[7]。
[9]同[2]。
[10]同[3]a。
[11]同[3]b。
[12]张学海:《西河文化初论》,《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05—806页。[14]同[13]。
[15]孙启锐:《后李文化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吴文婉等:《章丘西河遗址(2008)植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17]孙波:《后李文化聚落的初步分析》,《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18]同[12]。
[19]同[7]。
[20]图中所示为西河人活动的区域,在河西没有发现相应的遗存,因此,这些人群可能来自东边长白山或南边泰山北麓。
[21]a.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2003年发掘报告》,《东方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b.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2003年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南大沙河流域系统区域调查主要收获》,《东方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
[22]同[17]。
[23]社会学中所称的主干家庭指成年男女及其子女、父母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再加旁系亲属构成扩大家庭,若干具有祖源关系的扩大家庭构成一个家族。
[24]同[17]。
[25]同[16]。
[26]a.栾丰实:《试论后李文化》,《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b.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县博物馆:《江苏泗洪县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27]也有可能某些后李文化聚落中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目前还缺少更多的资料支持。现在这些发现更像是来自外地而在本地消费。
[28]宋艳波:《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年。
[29]靳桂云:《后李文化生业经济初步研究》,《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30]长清月庄遗址、万德遗址、历城张马屯遗址、盛福庄遗址、章丘西河遗址、摩天岭遗址、小荆山遗址、茄庄西遗址、绿竹园遗址、坡上(小坡)遗址、邹平孙家遗址、张店彭家遗址、临淄后李遗址、潍坊前埠下遗址、诸城市六吉庄子遗址。
[31]同[17]。
[32]同[29]。
[33]同[17]。
[34]济南市文物处、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省章丘小荆山遗址第一次发掘》,《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3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小荆山后李文化环壕聚落勘探报告》,《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
[36]济青公路文物工作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2期。
[37]同[21]a。
[38]a.同[35];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