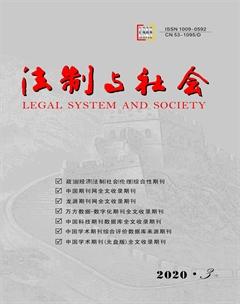调解书适用“拒执罪”探微
陈神
关键词调解书 “拒执罪” 法院
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审判背景下,我国许多民事诉讼案件及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通过调解结案的。调解申请执行、执行中拒不执行调解书的情形与判决的相关情形一样屡见不鲜。然而,依据当前法律有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的规定,拒不执行调解书的刑事归责存在缺位。这不仅妨碍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司法执行工作,更使诸多据不履行调解书的拒执行为无法得到应有的法律评价与惩治。
一、法律渊源
从犯罪构成分析,调解书属于拒执罪的“犯罪对象”。有关“拒执罪”的犯罪对象,主要有如下法律规定:
(一)刑事领域
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限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何为上述“判决、裁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进行了审议,最终形成的报告在1998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二)民事领域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第3项规定拒执罪的适用可以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支付令。”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调解书是拒执罪的犯罪对象。之后,随着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的出台,上述意见被废除。但2015年解释并未再规定拒执罪中判决裁定的范围。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评析
调解书能否适用拒执罪主要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不同观点。
否定说主要依据是我国刑事领域的上述相关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及禁止类推解释对否定说提供支持。肯定说则认为调解书能适用“拒执罪”。依据是不仅在规范层面,我国曾以民事司法解释的方式肯定过调解书可以适用拒执罪;而且依法理分析调解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及拒执罪的相关构成,排除调解书在拒执罪中的适用也是不合理的。
笔者认为,调解书适用拒执罪有较大的合理性。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与民事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刑法法益考察,对调解书的拒不执行侵害的法益正是拒执罪所保护的法益,法律理应予以规制。调解书是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合议。从法益侵害的实质性上看,拒不执行当事人“诚信”合意达成的调解书较拒不执行判决而言有着更为严重的危害性。
在现行规范层面,调解书不能适用拒执罪无疑是当下的主流。规范的矛盾体现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废除之前民事与刑事两个领域就拒执罪的不同规定。民事与刑事在同一问题上冲突以何者为准并没有相应的处置规则。这使调解书能否适用拒执罪在规范层面的非伪性得到一定证实。反观我国立法倾向于支持调解书本身不能适用拒执罪,概因为如下原因:
法院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定位应溯及法律社会学上社会司法与国家司法的划分。法律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尤根·埃利希对社会司法现象概括性描绘:“各种各样的仲裁法庭、社会法院、荣誉法院、卡特尔法庭、信托法院、工会法院和会所法院都是由社会自己建立和维持的法院,它们的裁决主要以非法律规范为基础。。因此,ADR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在西方属于社会司法,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主体系社会组织及裁决依据系社会规则。拒执罪保护的重要法益之一即法律的权威性、人民法院正常的司法活动。若将法院调解视为纯社会司法的范畴,那么我国立法认为调解书不能适用拒执罪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调解书并未包含拒执罪所要保护的上述法益。但回到埃利希对社会司法的最初描述,显然我国的法院调解并不与西方的上述模式一致。随着法院调解制度的逐渐发展,我们也早就理清法院调解与其他社会机构调解之间的差别。法院调解绝不可能是“纯司法”活动,至少是一种“准司法”活动。因此,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在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在使当事人有敬畏法律权威性的感知方面与判决并无二致。我国当前对调解书本身不能适用拒执罪立法的观念应该根源于对法院调解上述定位的桎梏。
正由于上述对调解定位的传统态度没有改变,接下来的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及“禁止类推解释”就使司法实践无法将调解书本身适用拒执罪。
二、调解书在拒执罪中的应然定位
(一)法益之保护分析
对于拒执罪本罪的犯罪客体,有观点认为是国家的审判制度;。也有认为是人民法院的正常活动秩序;有人强调是司法机关的裁判活动的权威性;还有人主张是司法机关执行判决、裁定的正常活动。主张复杂犯罪客体说的学者认为,基于犯罪客体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分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侵犯了国家审判活动秩序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无论对本罪的犯罪客体做何种表述,均无法脱离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而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显然是法律规定的司法活动的最终结果之一。故对调解书与判决书在适用拒执罪时采不同态度缺乏正当的理由。
(二)立法意图探究
反观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拒执行罪规定的裁定。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作出机关不是人民法院而是仲裁委员会、公证处,且法院对于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有审查的权力,可以对其不予执行,因此这类执行文书必须在作出相应的执行裁定后才能成为拒执罪的犯罪对象。而调解书的制作主体为人民法院,立法解释中之所以将依据调解书制作的执行裁定列为拒执罪的客体则可能因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不仅仅限于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主体。上述立法解释的用意可以解释为为了明确依据调解书制作的执行裁定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而不是为了将调解书排除出本罪的犯罪对象。同时,从更深层面上考之刑法的立法意图,追究拒不履行调解书的刑事责任,也符合犯罪化的正当依据。我们应当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社会危害性的“严重性”加以判断和予以把握。就恶意逃避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且情节严重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