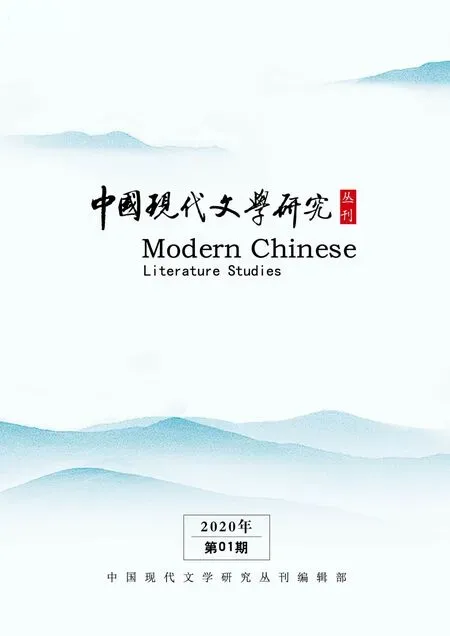民初政治小说《极乐地》的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鲁哀鸣的《极乐地》是民初政治小说中的杰作,其价值主要体现为:第一,通过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引入,《极乐地》把近代政治小说中的理想叙事推到了“主义”化的新阶段;第二,《极乐地》基于无政府主义立场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造了清末政治小说寄希望于未来的乌托邦叙事模式,建立起运用思想理论来处理现实的传统,对后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启示作用;第三,《极乐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充满悖论,既有强烈批判,也有悄然借鉴,这既有别于清末作家的立场,也不同于革命文学家的态度。总体而言,《极乐地》无论叙事模式,还是问题立场,抑或是文化态度,均蚀刻着近代政治小说运行的轨迹,是近代政治小说演进中的一个重要标识物。
鲁哀鸣的《极乐地》是民国初期影响较大的一篇政治小说。1912年10月,小说由人道学社出版发行,后于1919年再版,1921年第三版,可见其影响之大。《极乐地》以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寓理想于未来的乌托邦叙事,成为清末政治小说在民初的继承者,但与此同时,它在处理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又重建了现在、未来与过去这三维时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与192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生发出某种微妙的关联。如果说天空中星座的划分往往取决于人们确定并勾勒出的几个关键点的话,那么,厘清从清末政治小说到《极乐地》再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几个关键点的叙事关联和逻辑钩沉,或许能为近代文学提供某个尚未被人关注的思想星座。
一
《极乐地》主要叙述了主人公白眼老叟领导的“金钱革命”及其失败之后再次革命的故事。陷入绝境的白眼老叟意外地来到了“快乐地”,并被岛上繁荣和谐的社会景象深深打动。回国之后,他便以此为目标,联合同人继续革命。小说最后以天下大同的愿景作结,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未来姿态。
小说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那座被称作“快乐地”的孤岛。它酷似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桃花源”,兼具化外之地、自成体系、偶然而遇等诸多“桃花源”因素,但“快乐地”并不是“桃花源”。第一,“桃花源”“复古”,而“快乐地”“向新”。《桃花源诗并记》中的生活叙事,基本上都是对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的仿照;“快乐地”的生活叙事则多面向未来,那里的现代化程度实非过去和当时的中国所能比拟。第二,“桃花源”神秘自闭,不可再度接近,而“快乐地”却开放,完全可以复制。“桃花源”只出现了一次,此后便无迹可寻,它之所以备受古人推崇,和它的完美与神秘有莫大关系;“快乐地”上的岛民则愿意和外来者交流,甚至愿意把“快乐地”作为白眼老叟的退守之地,白眼老叟不仅把它当作人类生活的一种理想范型,而且还把它当作解救现实危机的有效方案,既理想,又及物,这才是“快乐地”的可贵之处。
“快乐地”的及物特征,使得它较“桃花源”更容易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在世目标,这又使它与清末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其间的区别就是:清末政治小说多止步于方向上的积极引导,还不曾提出具体的方案,《极乐地》则已不再满足于为世人指出一个笼统的方向,而是在认真地做着将“方向”落在实处的工作。譬如,作为清末政治小说的代表,《新中国未来记》就很少触及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新石头记》也在未来制度的建设上鲜有创见,但《极乐地》不仅表现出对制度建设的兴趣,而且对如何破除传统伦理对人身的束缚,已有一整套的可行性方案。很明显,借助对理想目标的精确定位,以及对诸项步骤的详细介绍,《极乐地》把对未来的种种思考开放给现实人生,它将抽象的乌托邦方案具体化为系统的社会学说,大大革新了清末政治小说的乌托邦叙事模式。
《极乐地》之所以能较清末政治小说提出更翔实的理想方案,主要是因为它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缘故。首先,小说的作者鲁哀鸣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和愤愤等人组织了民初的无政府主义党派——社会党,发表《社会党缘起及约章》《社会党纲目说明书》,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小说中“快乐地”的先人陈锐“千万不可立君、立官”①的遗嘱之于“消灭阶级”的主张,“快乐地”中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的诸项社会制度之于“无远近”“无亲疏”②的理想,等等,均可从《社会党纲目说明书》中一一找到对应之处。其次,《极乐地》发表之时正值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批判民国政府的文章如安真《政府乎?盗薮乎?》、叔鸾《中国革命原论》、迦身《无政府之研究》、师复《无政府浅说》等,通过在原理上对民国政府有效性的质疑,已取得与时人社会心理相呼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别所倡导的主张如心社的《心社意趣书》、社会党的《社会党纲目说明书》、晦鸣学舍的《〈晦鸣录〉编辑绪言》等,也以对未来社会详尽的说明,获得了可以凝聚时人思想的向心力。如果抛开具体的主张不谈,只从逻辑的层面来看,无政府主义此时不仅宣泄了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时人应该“怎么办”的具体路径,这正是民初无政府主义“顺势得到人们的重视”③的根源,而《极乐地》也是这一“时势”所造化的文学结果。
《极乐地》所凭借的“时势”转瞬即逝。尤其在1920年代以后国内军阀战争此消彼长、变化迅疾的新“时势”面前,无政府主义应对现实问题的无力之感更被无限放大,这不仅连带出人们对其自身理论不足的重新思考,而且也使人们开始期待更具“吸引力”的“新”思想的出现,其中的道理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除了继续重复乌托邦梦想以外,别无新意,在渴求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那里,无政府主义必然遭到冷落。”④马克思主义以具体有效的“‘阶级革命’的策略”,吸引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蒋光慈《短裤党》中李金贵对社会主义的期冀,胡也频《到莫斯科去》中素裳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等等,已说明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吸引的程度。这是近代政治小说中理想叙事在《极乐地》之后的又一次变化,但支持这一变化的同样是“时势”力量,与《极乐地》对清末政治小说的突破有着相似的逻辑。
综上所述,在这段跨度并不太大的时间里,政治小说中的理想叙事完成了两次转变,一次是由乌托邦思想向无政府主义的转变,一次是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极乐地》居于这两次转变的中段,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纯粹的思想讨论已难以应对民初的现实问题,人们便主动摒弃乌托邦思想,转而去寻找“新”思想,王汎森把这一寻找过程看作由“‘思想时代’到‘主义时代’”的转变。⑤在第一次转变过程中,《极乐地》通过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引入,把近代政治小说中的理想叙事推到了“主义”化的新阶段,它预示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更加趋于理性的时代即将到来;在第二次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更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特别是此时苏俄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具有直接的资鉴意义,所以,在谁更具有“吸引力”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十分明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统领,正是作家们在新时代里对“新”思想的正确选择,但是在如何运用“主义”去处理问题,以及如何在具体创作中呈现“主义”的层面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又难以脱离《极乐地》的叙事传统,反而与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鲁哀鸣与同时期大多数政治小说家一样罗列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对生活于斯的时代状况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最终使《极乐地》从一众政治小说中脱颖而出的,并不是它对政治的义愤宣泄,而是它对问题根源的审慎分析,尤其是从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所提出继续革命的方略,以及诸项制度建设的具体方案,更使它在民初的小说中显得非凡。
首先,鲁哀鸣将民初政治失序的根源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主要是以财富多寡为表现形式的不平等。展示政治的芜杂黑暗是民初政治小说的重要主题,李涵秋《广陵潮》、恽铁樵《村老妪》、觉迷《不倒翁》、损公《董新心》等作品从不同方面涉及了这一主题。这些小说擅长揭露政治弊端,但是却流于现象描述,鲜有深入的社会剖析,因而也就缺少了某种历史深度。和它们相比,《极乐地》的长处在于对现象根源的探寻。小说认为,金钱是造成社会差异的终极原因,富人通过金钱垄断穷人的生计,穷人则因为失去生计而不得不俯首于富人。人的“贪欲”便由此滋生出来,特别是那些本应承担社会职责的政府官员们,他们更是拼命地攫取金钱,以及与“金钱”同价的“美女”“美衣”和“美食”⑥,根本没有“替人民尽个完全的义务”⑦。政府官僚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裂隙因不平等而发生,也因不平等而加剧。
《极乐地》试图对社会情境进行历史判断的自觉意识,与作者自身政治理念的驱动有紧密关系。前文曾述,作者鲁哀鸣参与过社会党的组建。社会党所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核心要义即是“平等”,并在其《社会党纲目说明书》第一纲第一目开宗明义地宣布:“人生之幸福,劳动之结果也。顾劳动则贫者为之,幸福则富者享之,世界不平等事,宁过是耶!消灭贫富阶级之术多矣,莫善于共产。”⑧鲁哀鸣对此解释道:“劳逸平均,住室、用具、穿衣皆是一样,是为平等。”⑨显然,《极乐地》中人与人之间应该绝对平等的论断拓印了作者所从属的党派理念,小说之所以会借助社会平等学说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并表达明确的价值判断,正可在此找到确然的答案。
其次,为解决不平等所导致的政治失序,《极乐地》提出了继续革命的主张。与很多政治小说中主人公遭遇挫折即失落、消沉的叙事不同,白眼老叟始终葆有革命热情。尽管一些另有打算的“革命者”从内部瓦解了革命的大好局面,但是白眼老叟并不气馁,因为他坚信只要理想社会未能实现,“新”的革命就必定会再度崛起,“我在世间存在一日,就做一日社会革命的事业,务必拯救人类到快乐地的景况”。⑩他从“快乐地”回到国内,先后遇到“自由”“抑强”和“愤愤”等人,并一起组建新的政党伺机“做事”,正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与代言人,白眼老叟的终极目标是取消政府,因此,他既不以民国政府的合法性为意,也不完全否认它的历史有效性,而把它看作走向理想社会的“中间物”,其中的分寸感正像曹世铉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他们在无政府主义运动进行方法上,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忠诚于无政府主义原则,继续进行对于共和政体的斗争,向最终目标进行;还是先把共和政体认定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所需要经过的阶段,暂时承认其存在,然后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⑪像白眼老叟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不对民国政府抱有幻想,对它的承认更是在“暂时承认其存在,然后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层面上成立的,所以当看到民国政府里官僚阶层的种种丑态时,白眼老叟的革命热情非但不会因此消歇,反而会因此受到激励,进而以此为动力,发出“推倒不良政府,组织共产事业”⑫的号召。
最后,小说在“快乐地”展示了实践理想的具体方略,这些方案也都带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印记。“快乐地”推崇绝对的平均:“我们这里生下一个人来,教养一样,读书一样,服役一样,作工一样,养老一样,吃的、穿的、住的、玩的、要的都是一样,那里还有不公不平的事呢?”⑬“快乐地”强调人的职责意义:那些作工较轻的人们常常会自觉地去帮助那些作工较重的人们,其中的原委就像岛民陈生所说,他们“拿着全岛的事业当他个人的事业,拿着全岛的东西当他个人的东西”,这一乐于助人的现象显然超越了“热心”所能解释的范畴,这里的人们将它作为日常“习惯”⑭,其实早已内化为每个人心中的伦理自觉。
从对现实问题的根源探索,到继续革命方略的提出,再到对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展望,《极乐地》以清晰的逻辑表达了它处理民初政治失序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见解。如果说清末政治小说将现实危机做了虚拟化处理,将叙事重心全部放在了可然层面的话,那么,《极乐地》则没有完全接受它们对未来世界的空想,它一方面不认同无媒介地运用乌托邦想象来回应现实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则对那些容易被流于空洞言说的乌托邦思想保持警惕。所以,无论是对现实问题的剖析,还是对革命方略的探索,《极乐地》都将叙事重心凝聚在了“种种的手段”之上,大大强化了清末以来政治小说的现实品格。
十多年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与现实更为切近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骤然引爆,但令人惊奇的是,它们的叙事策略,并没有脱离《极乐地》式的以理论烛照现实的叙事模式。当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样信赖政治学说之于现实的指导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做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析和判断,如在《少年漂泊者》中,蒋光慈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佃户汪老二一家人之所以生活贫苦,全在于“称雄于乡里的”刘老太爷,“做恶为祟,任所欲为”⑮;二是对革命做出基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号召和鼓励,如在洪灵菲《流亡》中,沈之菲认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农工利益,民主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他提出了“惟有不断地前进,才得到生命的真诠”的革命主张⑯。显而易见的是,在解释和回应时代问题的叙事策略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表现出与《极乐地》惊人的一致性,尤其在探索社会理想如何实现这层意义上,它们都遵循了大致相同的逻辑原则。当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并非源于《极乐地》,更没有必要追溯到清末,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在叙述策略的转化上所存有的逻辑关联,而正是因为《极乐地》的存在,这条潜在的逻辑关联被隐隐地凸显了出来。
三
近现代政治小说多聚焦于现实问题,并努力于种种现代方略的探索,但在显豁的现实维度和未来维度之外,它们也尝试去思考过去,进而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立场与叙述策略。事实上,在这些小说中,无论是建构理想国家,还是分析现实困境,传统文化都始终在场,并与现在、未来形成绵密复杂的对话,只是受制于现实问题、理论方案的差异,它们对传统文化的立场并不统一。在这个并不引人注意的思想脉络里,《极乐地》显示出了它耐人寻味的历史意义:第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缺陷和不足,理性分析它与中国当前现实之间的历史关系;第二,保持与西方文化的距离,试图创造一个基于传统文化自发而来的现代社会。《极乐地》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扩大了它与清末政治小说之间的距离,却增强了它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关联的契机;而在另一面,《极乐地》对“快乐地”模式现代化社会的高度评价,则加大了它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间的分歧,但是却与清末政治小说中的文化自信取得了共鸣。对于《极乐地》如此悖论性的叙事姿态,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归类于之前或之后的文学,但正是这一鲜明的叙事姿态,却可为人们理解近代政治小说的演进,提供明确的标识作用。
《极乐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激烈的,这主要表现在“攻击传统圣贤”和“抨击家庭制度”两个方面。传统圣贤在小说中并不是被赞誉的对象,而被看作专制主义,进而是人与人之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制造者。正因为如此,“快乐地”的先祖们烧尽了从中国带来的圣贤之书,“不许读在中华带过来的书,把从前那些圣人所著的书都烧干净”,为了不留下祸根,他们“把它烧得干干净净”,“一本没剩”⑰。“快乐地”的先祖们在七百年前就捣毁孔子的祀庙,并在其遗址上砌出茅草厕所,以区别于由黄金盖起的普通厕所,彻底断绝了对圣贤的敬仰。《极乐地》也抨击了传统家庭制度。小说讲述了作为家长的父亲和母亲,总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物品一样去任意支配和处理的故事,尤其是对于女孩子,家长们总会把她们或者“生下来就弄死”,或者“抱到人家去作童养媳”,或者“卖给人家为娼”,全然没有意识到她们也是一个“人”。白眼老叟的妻子哀氏在小的时候就被缠足,长大后“两脚不便,虽是个完全人,实在是个废人”⑱,足见传统家庭制度对儿女们迫害的程度之深。
吊诡的是,鲁哀鸣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却又和儒家大同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以“无政府党是大同主义”19谈论将来的分配制度,以“人类进化到大同的地步”⑳谈论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实现,以“世界大同”谈论国家的消亡,等等。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党纲目说明书》开篇即说:“科学进步,真理大昌,人类平等,地球大同之社会主义,必有达目的之一日。”㉑他们对儒家思想的使用并没有停止在词语比附的水平上,而是将其运用在了对未来想象的架构中。《社会党纲目说明书》第二纲第二目有“家”的说明:“幼者之生,为继续现社会而生也,现社会自宜公育之;长者之老,为经过现社会而老也,现社会自宜共奉之,是之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世界于是焉大同。”㉒其中对“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说明,明显取自《礼记·礼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㉓此外,在《极乐地》的理想叙事中,“举出个能干人来作头目”㉔之于“选贤与能”,“把银子堆在大马山上”㉕之于“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全岛连一个废人也没有了”㉖之于“盗窃乱贼而不作”,等等,也都是《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具体演绎。
如此对待传统文化的悖论态度并非始于《极乐地》。清末作家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宋儒责人太甚,动不动要讲天理、人欲,讲天理的,不准有一点人欲”㉗,但他们更想从中汲取思想养料,吴趼人《新石头记》中“文明境界”强调那里的人从小就接受传统道德的培育,即是证明。他们看重传统文化,主要考虑的是在面临西学侵入之际,作为主体的中国究竟该怎么办的问题,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复古。作为区别,《极乐地》的主旨或许并不在于证明传统文化是否真的恶劣,却真心希望由此能唤醒民众,以开辟出一条可达致理想社会的新路径。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体现在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但《极乐地》悖论式的态度已被单纯的批判所取代。在这些小说中,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礼教”等词语,被简化为落后的、需要被革命的文化符号,如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在接受新思想之后,就把他的家庭当作旧思想的代表,并最终与之决裂;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认为革命家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家,就在于他不能向旧礼教妥协;等等。以如此鲜明的二元结构来处理过去与未来关系的做法,已经完全不同于清末政治小说,也不同于《极乐地》。罗志田在谈论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时曾说:“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由于新旧本身已成价值判断的基础,守旧一派不仅不能成为主流,也确实提不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很难从复旧中展现出一个比当下更好的未来。”㉘正好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提供了有效说明。
可以看得出来,从政治小说发表的1902年始,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1920年代末,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今天的读者很难将吴趼人“恢复我固有之道德”㉙的观念与郭沫若“不希望你们成为个时代的落伍者”㉚的倡议联系在一起。但是,鲁哀鸣“要想改良社会,非从根上解决不可”㉛的主张,在此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缓冲力量,通过对它的理解,人们在阅读时的惊奇之感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进而这些在以前很难被放在一起讨论的各类小说创作,也会因《极乐地》的存在,而有了可以被同时讨论的空间和可能。
结 语
清末政治小说纵论国家愿景,其叙事视点重在未来,但关涉现在和过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也兼有未来信仰和传统批判。《极乐地》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以自身的文学表达,向人们提示了近代政治小说中这个内涵丰富的三维时空的存在,依靠它的中介存在,这些小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时空中处理问题的相通性被显示了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极乐地》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积极引入,不仅改变了清末政治小说对未来众说纷纭的喧哗局面,而且建构起运用“主义”去处理现实的新叙事方法,进而形成了它的双向性格。近代政治小说前后的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但是如果适时地让这篇小说介入其中,我们相信它会对缓解人们在阅读时的惊奇之感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极乐地》应是人们认识和了解清末以来政治小说的重要视点。
如今,20世纪整体文学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现代文学已向近代开放了它的边界,这使得许多近代文学作品的价值都得到了发掘,鲁哀鸣的政治小说《极乐地》也应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们不应遗忘或者忽略这篇小说,理应把它放入20世纪的文学史中,给予其历史的考量和评价。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