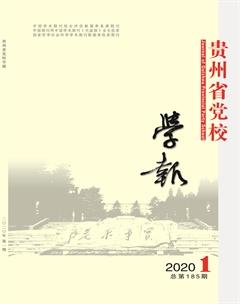中国监察权规制的理论脉络追溯
摘要:中国自夏朝进入文明阶段或者说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深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文化影响,尤其是当时主流统治思想的影响,监察权的规制所表现出来的性质、特点、方式等都有所不同。历史上“神治”“礼治”“德治”“法治”“宪治”和“党治”等思想在中国监察权规制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些思想既表现出相互融合的特征,又依次发挥过主导作用,具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为我国监察权规制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监察权;权力规制;监察理论;监察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20)01-0088-06
新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权位高权重,成为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的“第四权”。如何合理、科学规制监察权,寻求各种权力之间的重新平衡,已经成为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诉求。中国古代有关监察权规制的实践和理论学说,尽管部分理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些权力规制方法所蕴含的哲理仍然值得深入探讨。因此,在当前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为了进一步规范监察权的行使,有效防止监察权力过分膨胀,需要对有关监察权规制的传统理论资源进行系统梳理。
一、监察权之“神治”
据史料记载,原始社会到殷商、西周时期曾经历了一个比较长久的神权政治、神判法阶段。商朝的神权法思想盛极一时,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发生变化,针对神权法思想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便结束了“神本位——任意法”时代。[1]31当时的监察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监察权高度集中于君王,但是监察权的规制受到神缘本位、神权政治、神判法的影响,打上“神治”的烙印。
夏朝统治者利用宗教鬼神进行统治,将君主的权力(包括监察权)说成是神授的,把法律的制定说成是天的意志或意思表达,而法律的实施则是“恭行天罚”。《尚书》中记载,“有夏服天命”。[2]159夏启征伐有扈氏时,认为是由于他“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剿绝其命,是“予惟恭天之罚”的结果。这些记载虽然大多涉及军事领域,但说明夏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把统治权说成是秉受天命而为,极力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夏代统治阶级的监察权受制于依据神的意志所制定的“神权法”。比如,《尚书·洪范》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柳诒徵论道:“国事分为五权,天子一人一权,卿士若干人一权,庶民若干人一权,龟一权,筮一权”。五权之中,三可二否,皆可行事。[3]129
商代的统治者迷信鬼神,这一时期“天讨”“天罚”思想发展到了高峰。《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把“上帝”、鬼神看得高于一切,凡是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向其请示。商王假托神意,把实施刑罚说成是代天行罚。商代的《官刑》是懲治官吏犯罪、违法与失职的专门法律,对卿士与邦君等奴隶主贵族具有严格的约束力。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此外,《史记·殷本纪》说:“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可见,商朝统治集团都把自己的统治权说成是神的意志,任何触犯当时法律的行为,包括滥用监察权的行为,都被统治者视为悖逆鬼神天帝的元恶大罪,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西周统治者继承发展了商朝的神权法思想。周人以臣下的身份夺取了被称之为“上帝”之子的商王的统治之后,从商人迷信神祗而亡国的教训中悟出了道理:“天不可信,民不可轻。”当时把“德”看作是“天”与人间的重要枢纽,因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这种学说的基本理念是:“天或者‘上帝是至上神,它不是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为天下所有民族共有;天要把天命交给哪个民族,要看这个民族是否具有‘德,也即是否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天把天命授予有‘德的民族,该民族的祖先便可以匹配‘上帝‘在帝左右”。因此,“以德配天”君权神授说在为周王朝的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有力论证的同时,也对周王的监察权形成了制约,如果周的政权脱离了天下人民,同样会被人民抛弃,被有“德”的民族代替。
二、监察权之“礼治”
夏商周三代的“礼”的历史,既是一部相互损益沿革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制度化的历史。[4]特别是在西周初年,经过“周公制礼”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礼治”体系。当时国家治理的运行逻辑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5]。而《说文解字·示部》也记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此时的“礼”还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种行为规范,祭祀所得到的启示是不可违背的。
改革论坛谢时研:中国监察权规制的理论脉络追溯“礼治”思想作为先秦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等方面,当然也包括监察方面,都按照“礼”的面貌来支配,对君王的权力发挥着重要规制作用。正如《孟子·离娄》中言尧舜之世:“君尽君道,臣尽臣道。”早在尧舜禹时期就有“谋于四岳”的拾遗补阙制度,针对重大政务,尧舜要咨询四岳的意见,而舜在设官分职问题上也要“谋于四岳”。夏代“三正”“四辅臣”“六卿”“三老五更”等号称辅弼的宗亲贵族,负有拾遗补阙的谏诤责任。此外,夏朝设立了监察之官“啬夫”,用来检束群吏或百姓。
西周时期,“礼”的基本精神是“亲亲”“尊尊”。在家国一体的奴隶社会,“亲亲”“尊尊”是规制监察权的主要方式。以“礼”为表现形式的各类习惯法,对监察权进行规制。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礼·天官·大宰》载:“以八法治官府。”说明西周对政府官员的职权行为和活动原则等都有了明确规定,而且西周统治者对官吏要求也非常严厉。《左传·禧公十一年》周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国语·晋语四》卫国宁庄子也说:“礼,国之纪也。”以上说明当时的礼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制监察权力的重要规范。但是,西周的“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各级贵族不仅享有“礼”所规定的特权,而且即使越礼犯法,也一般不受刑罚。
春秋时期,传统的宗法等级观念和神权法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抨击,“礼”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开始式微。战国时期是法律与礼制冲突的时期,“法治”思想开始兴起。战国时期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6]。汉朝以后,统治集团试图协调“礼”与“法”的关系,开始实行“礼法结合”,经过“引经决狱、以礼解律、导礼人律”,而《唐律疏议》标志着“礼法”的全面结合。
三、监察权之“德治”
西周时期的统治者极力推崇“德治”,“德”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资格、品质,也是统治国家、规制权力的基本方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郑国子产认为,“德,国之基也”。要求统治者必须时时了解人民苦疾,力求做到“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隐痛)”“怀保小民”[2]191。因此,君王等其他监察官员行使监察权时要把民心的向背作为重要考量,为了保“国之天命”,必须“明德”。
孔子在继承西周“礼”、东夷“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富而后教”的“德治”思想。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因而,作为君主要重视严以修身,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8]儒家主张用“仁礼”精神洗涤官吏内心的私欲,用“忠”的道德价值观念去激励官吏们勤奋工作,用民意作为重大事项的决断依据,这些思想对于规制监察权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而他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奉行“王者之论”,即“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9]。荀子的吏治思想,旨在使官员受到皇帝的监督和考察,为官者应该谨慎行使权力,做到无恤亲疏,无偏贵贱。
汉代贾谊提出了“君明、吏贤、民治”的思想。他说:“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10]贾谊还认为,作为君主要做到“明”,德治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按“仁、义、礼、信、公、法”行事,如此才能慎于政事。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政治经济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吸取其他各派思想,主张以“德主刑辅”为核心,以法家思想为缘饰,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哲学基础,成为封建正统立法思想,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古代监察权规制的“德治”基础。
宋朝朱熹认为贤者乃治国的关键,他在《论语集注》中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11]《朱子语类·朱子五》曰:“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在《四书五经》的注释中提出,“贤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12]。因此,朱熹强调君主应该注重修身正心,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最根本的大事,并主张任用有德有能者,只有做到举用贤才,才能更加有利于治国安邦。
四、监察权之“法治”
国内学界大多认为,中国古代“法治”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监察权所依之法,在此阶段经历了“神权法”到“人治法”的转变。法家以“人性恶”为理论假设,提出“依法治国”和“法、术、势”相结合,主张“刑无等级”“以刑去刑”,推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些“法治”思想对于有效规制皇帝、丞相、御史大夫等官员的监察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李悝撰写了《法经》,并用法的形式予以巩固。他主张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制定并严格执行对罪犯的“罚必当”的措施,打破过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法经》的《杂律》内容包罗甚广,其中就有“金禁”的规定,也就是有关官吏受贿的禁令。《杂律》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因而,《法经》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原则,也是当时魏国监察权规制的重要依据。《法经》深刻影响了秦律,乃至汉律的制定和发展,在中国古代法律史具有重要地位。
商鞅受李悝、吴起等人思想的影响较深,潜心研究“以法治国”,主张“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据说,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被商鞅处以劓刑。可见,商鞅十分重视吏治,强调一切决于法。正如章炳麟《訄书·商鞅》所述:“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覈其宪度而为治本。”正因如此,秦国变得秩序井然,老百姓变得守规矩。而在《商君书·慎法》载:“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欲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总而言之,商鞅的法治思想非常注重对君臣权力的制约,强调以法学之鸷维护民生之本。
韩非是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于一体,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认为君王统治权是一切事物的决策中心,强调君王运用严刑峻法来御臣治民。他指出:“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13]同时,在官员(包括监察官员)职务约束方面,法家的“术”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从职务方面规制权力的规定包括“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的官僚任免和考课手段。
秦朝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吏治”方面的有关制度已初步定型,并积极运用到实践。为了强化对官吏的权力规制,秦代朝廷提出了要守法毋私,审当赏罚,不得“居官善取”“贱士而贵货贝”和“受令不偻”。1975年出土的云夢秦简《为吏之道》规定了为官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凡为官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韯(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14]79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要养成官吏应有的品格和作风。比如,《为吏之道》当中还规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夬(决)。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毋重,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见(谏)勿塞”[14]80。《为吏之道》的思想内涵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法家单一的“治世”思路,而是将法儒道墨诸家学说有机融合,体现了以法为本、综合为治的特点。
五、监察权之“宪治”
晚清时期,西方宪政思想开始传播到国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要求开国会、设议会、立宪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们极力宣传“民权”思想,要求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权利制约公权,这些思想为监察权的“宪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严复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百无一可”,专制之君是“无法”之君,专制之国是“无法”之国。他在《原强》中说:“设议院于京师,而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里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可见,他注重发挥议院的作用,把设议院视为当时中国之救国图强的良药。
康有为指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政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今变行新法,因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其末,无当也。”[1]278因此,他主张引入了依宪治国的理念,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尤其是他提倡民权思想,强调地方自治和公民自治。
梁启超针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思想主张。其核心理念就是要变君主的“独裁”为资产阶级的“群治”。他以“英国的立宪政体”为典范,认为“宪布宪法、召集国会”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章太炎主张监察机构独立,建纠察院或都察院。在考察了西方的监察制度后,他认为西方的监察多附于国会,实质上是一种虚伪的监察。他认为监察官员应该通过考试产生。章太炎说,“今使其人皆出于考试,考试及格,则使之互选,选举已定,则政府加以任命,以先有考试,故选举不能妄投,以先有选举,故任命不能随意”。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总统及政府对监察官员的操纵或控制,使监察官员对总统及各级官吏更好行使监察权力。章太炎在《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中强调:“给事中,御史所以必分者,何也?曰,一以监督政府,一以监督官吏,监督政府者,事未成而制之,监督官吏者,事已成而弹之,其事务不同,有不能合一者也。”[15]
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提出了“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理论”。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认为,司法独立,监察当然也应独立,“从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裁判官员的纠察权反而隶属于其他机关之下,这是不恰当的”。[16]1906年11月15日,他在东京会见俄国社会革命党魁该鲁学氏等时指出,希望在中国实行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府。民国初期,孙中山在继承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思想,最终确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的政权结构。
六、监察权之“党治”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后,目睹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思想涣散、为官不仁、脱离组织等严重问题,尤其是一些曾经追随其多年的老国民党员思想出现了严重蜕化变质,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革命性。孙中山认识到党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国家,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17]。因此,他提出了“党政分察”的监察思想。当时关于“党政分察”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在党政两个系统都设置监察机构,分别行使监察权,两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有联系。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率先建立党的监察机构及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孙中山提出了“弹惩一体”的主张 ,即监察机构具有弹劾与惩戒的双重职权。他认为,“弹惩一体”有助于防止行政干涉监察,更好发挥监察效能。
1928年6月,胡汉民、孙科的《训政大纲》提案,导致后来整个“训政”时期,只有执政的国民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被剥夺了合法地位。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党务组织系统与行政组织系统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从而导致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治控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转变。此外,蒋介石还利用孙中山的“一党制”理论主张,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法西斯论调。因此,蒋介石的“党治”与孙中山的“党治”有着本质区别,两人在监察权规制的“党治”理论主张、实践运作方面也是截然不同的,绝不可以把他们混为一谈。
结语
总之,监察权规制思想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于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作用。通过对中国监察权规制的理论脉络梳理,可以为监察权力运行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使得当前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能够超脱时代的局限性,更好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重心。监察权规制思想的历史流变,是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当时国家治理的智慧与理念。诚然,中国古代的监察权规制思想所蕴含的合理性元素,仍然值得我们辩证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2]尚书[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3]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9.
[4]徐忠明.“禮治主义”与中国古代法律观念[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1):40-60.
[5]左丘明.春秋左传:上[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302.
[6]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545.
[7]论语[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144.
[8]孟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106.
[9]荀子[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121.
[10]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93.
[11]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127.
[12]四书五经:上册[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23.
[13]韩非.韩非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72.
[14]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二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5]马克敏.略论民国时期的监察思想[J].新西部,2007(10):239-240.
[1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9.
[1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4:43.
Xie ShiyanAbstract: Since the Xia Dynasty entered the stage of civilization or class society, supervisory power,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the form of political power organization and the system cul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mainstream ruling ideology at that time,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ways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supervisory power are different.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supervision power regulation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ideas of "rule by god", "rule by rite", "rule by virtue", "rule by law", "rule by constitution" and "rule by part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supervision power in China. These ideas not onl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 integration, but als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urn, and have their own exhibition logic, which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supervision power in China.
Key words: supervisory power; power regulation; supervisory theory; supervisory system reform
責任编辑:王廷国 李慧 孔九莉 李祖杰 邓卫红 刘遗伦 余爽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