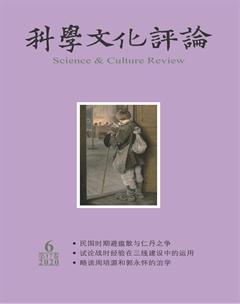试论战时经验在三线建设中的运用
刘洋
摘 要 探讨三线建设开展中借鉴战时经验的问题。提出三线建设开展遵循了为战争服务的逻辑,虽然借鉴了工业化建设经验,但采取的是延缓工业发展保证国防安全的策略。三线建设组织方式借鉴“集中领导、各方协作”战争经验,而不是按照常规建设方式展开,也不符合典型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征; 三线建设的展开过程虽然适当参考了工业化建设经验,但主要是按照备战需求依赖战时经验,体现在搬迁和建设过程之中。
关键词 三线建设 战时经验 工业布局
三线建设是1964年开始进行的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学界重点关注三线建设的起因和得失评价等专题①。在三线建设开展方面,陈东林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1],董志凯研究了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特点与经验[2]。三线建设的提出是基于备战压力,其开展过程中也具备着强烈的战争色彩,表现为充分借鉴战时经验。本文基于已解密的档案材料和公开出版资料对此进行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实施“赶超战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工业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的经验,也自然而然地应用到经济建设中,认为“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经济建设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3],充分争取外援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策略就是战时经验的体现。毛泽东把“搞不搞三线”等同于“愿不愿意革命”,还说:“斯大林同志不建三线,没搞民兵武装,最后很被动。”[4]可见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确立在当时来说也是出于备战的需要,并非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常规路径上延伸。本文认为,三线建设开展虽然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验,但也遵循为战争服务的逻辑,重点是战略退守,是牺牲、延缓工业发展保证国防安全。三线建设组织方式充分借鉴“集中领导、各方协作”战争经验,而不是按照常规建设方式展开,不符合典型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征; 三线建设的展开过程虽然适当参考工业化建设经验,但主体是按照备战需求,充分发挥战争经验,这体现在搬迁和建设的过程之中。
一 借鉴“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战时经验
在制订、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框架下,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开展方式逐步确定。三线建设的实施和开展方式充分借鉴“集中领导、各方协作” [5]战争经验,具有特事特办的色彩,并未束缚于“三五”计划的框架内。
在建设目标上,1964年10月,中央确定“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国家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6]。此后的國家计委改组、确定“三五”计划,都是围绕建设“战略后方工业基地”这个目标。“三五”计划基本方针由“先抓吃穿用”转变为集中搞三线建设,改组后的国家计委提出“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以及“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7]。三线地区投资比重提升,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西南地区投资预算约占全国的1/4,四川省1966年基本建设投资约为全国的1/6; “二五”计划时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是1:0.89:0.57,而“三五”计划时期则变为1:1.11:1.30([8],页11)。
三线建设以非常规方式迅速展开。如同三线建设流行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设方式一样,在选址和布局上也是边选址、边布局、边组织,按照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方式展开。按照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国家计委任命程子华为联合调查组组长,负责组织研究调查计划,并决定先派几位副主任各自率领工作组分赴各大区进行考察[9]。国防工业办公室党委组成10个选厂工作组,总指挥为国防工办负责人赵尔陆,工作组先后出发去大三线地区选择厂址[10]。冶金部、铁道部、煤炭部等14个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下设冶金、煤炭、电力、铁道等12个专业组,重点考察攀枝花等三线建设重点项目[9]。成昆铁路建设也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李井泉任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吕正操、刘建章、郭维城、彭敏任副总指挥负责筑路的具体指挥工作[11]。1964年下半年,经过考察选厂工作队在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勘探后,大体确定了三线地区的工业布局。
另外,三线建设的组织方式上充分借鉴战争时期经验,以“指挥部”形式整合地方和中央部委人员, 以期“集中领导、各方协作”, 提高运行效率。中央和“小计委”负责集中领导,制订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决定建设项目,审查实施方案。由中央有关部委与有关省、区的领导干部组成的西南和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是第二个领导级,负责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审定建设项目方案和施工计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西北局三线建设指挥部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主任[12],西南建设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四川省第一书记李井泉主任[5]。第三个领导级是建设项目的现场指挥部,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所在地区相关部门组成,负责实施建设计划,保证建设项目完成。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大型项目,现场指挥部下面还设立分指挥部,管理、协调各项配套设施建设[13]。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和物资部在三线建设中也是打破常规,协同工作。决定三线建设新的工厂和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决定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工作,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全国工厂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 物资部负责三线建设的物资供应([14],页1201)。为避免工作步调上混乱, 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工办、文教办公室组成5人小组,负责规划搬迁工作[15]。1964年11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批准1965年第一批搬迁西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名单[16],对于迁出企业的车间或设备、人员数量,迁入地点和将来的生产什么产品都做了明确要求。
从上述的组织方式可以看出, 三线建设借鉴“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战争经验,特事特办,充分调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防公办和文教办公室以及地方各方面力量。中央、小计委——西北、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建设项目的现场指挥部,这种三级分权的管理体制,充分整合各方面力量,打破条块分割壁垒,采取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常规组织方式,而是带有强烈的军事化特征。
二 借鉴战时经验进行搬迁
三线建设的开展过程虽然适当参考工业化建设经验,但向三线地区进行搬迁并非按照经济建设规律开展,而是集中全国力量,特别是一、二线企业的牺牲和支援,搬迁过程也有着战时特色。
1965年8—9月间的全国搬迁工作会议明确,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坚决地快搬、早搬,决不能松劲动摇[17]。会议确定:(1)国防尖端工厂、重要的军工工厂及其必要的协作配套工厂,有关国计民生的骨干工厂,生产全国短线产品和三线缺门产品的重要工厂,以及全国独一无二的重要工厂和关键设备,都应逐步搬到内地; (2)有些大型企业,由于规模过大、设备过重,迁建所需时间很长,如果搬迁对备战影响太大,可以采取先分后搬、分期分批、逐步转移的办法。做好搬迁准备工作,一旦情况紧急,立即全部搬走; (3)不宜搬迁的冶炼工厂、化工厂、炼油厂以及国防工业中少数火工、炸药厂等要积极备战,加强防空措施,即使在战争的情况下也要坚持生产; (4)有些企业担负着短线产品的生产任务,为了多生产短线产品,可以不搬。对搬迁项目的布点问题,提出要多搞小城镇的方针,实行大分散、小集中,以达到战略隐蔽的目的,具体布点时,要兼顾国防安全和经济合理。少数国防尖端项目,必须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有的甚至还要进洞。一般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的建设,应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地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17]。
1965年9—10月间,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缩、搬、分、帮”的方针。“停”即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 “缩”即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 “搬”即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 “分”即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几迁往三线,要求“一分为二”的工厂(或车间)的关键设备或专用设备,应该首先满足三线的需要,有两套的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坚决搬走,优选满足三线需要挑选优秀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成套输送([18],页122—123); “帮”即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停”“缩”“搬”“分”“帮”,使得一、二线地区做出了巨大犧牲。例如,在上级确定搬迁后,上海新中动力机厂350机型生产线和求新造船厂柴油机车间立即停止建设,在短时间内把人员和设备一起迁到四川武隆山区[19]。除此之外,还提倡“三老带三新”,即: 三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具体任务包括: 为新厂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为新厂提供设备和材料、为新厂承担试验研究工作提供技术资料和投资初期必须的备品备件,使新厂投资后能够很快出新品。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也在搬迁之列,要求同国防尖端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勘察设计单位和高等院校分期、分批地迁到三线地区([20],页131)。截止1965年9月,中央确定第一批从一线搬往三线的214个项目,计划迁出职工约48000人,设备约6700台[17,18]。根据陈东林的研究,三线建设时期全国由内地迁往三线地区的项目和企业约520个[8,14]。由于缺乏大规模搬迁的经验、时间仓促,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没有制定通盘周密的搬迁规划、内迁厂布点不完全合理、工厂搬迁后没有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协作关系、职工生活福利没有统一规定等。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可否认的。经过三线建设,在中国三线地区初步建成了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地区的1.25万吨卧式挤压机、3万吨水压机、20辊带轧机、2.8米宽的冷、热轧扳机和200毫米冷轧钢管机,都是最新最大最精密的压延设备; 形成的高温合金生产能力相当于当时全国的总和,已经拥有的机械加工能力接近当时东北的水平[21]。
在备战压力下,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表现出浓厚的战时特征。如董志凯所言,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特色为低投资、紧运行,即不同于日本侵华战火中企业被迫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也不同于21世纪西部开发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运用了在战争环境与和平建设中长期形成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调动能力[2]。集中全国力量按照战争需求进行搬迁是备战的需要,在此过程中战时经验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分为二”与“停、 缩、 搬、 分、 帮”的方针体现了战争中形成的无偿支援精神; “好人、好马、好枪炮”体现了在战争中形成的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牺牲精神; 短时间内高质量的搬迁工作依赖的是战争中形成的强大的调动动力和动员能力。
三 借鉴战时经验开展建设
三线建设虽然是一场工业布局的调整, 但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备战”色彩。“边备战、边建设”的指导方针强调要突出国防、保证备战[22],战时经验自然也体现在三线建设之中。
1. 布局原则:靠山、分散、隐蔽
三线布局如何适应战争的要求?当时要求必须要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这是从战争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 对三线地区的新建企业有着很大影响。“远看像村庄,走进是工厂,不见人影动,只闻机器响”这句顺口溜形象描绘了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原则建厂试图达到的效果。按照战争的需求,当时的工业布局存在的问题是: 相比后方基地,沿海比重大; 新建工厂过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上; 工厂大多是综合性大厂。当时认为这样的国防工业布局经不起敌人的突然袭击,因而三线建设布局要从战争观点出发,应当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达到在热核大战的情况下,打不烂,炸不垮,能坚持生产。
“靠山、分散、隐蔽”,关键在于分散。要缩小工厂规模,多布点; 离开城市、平原,分散布置工厂; 以产品为对象,地区成套。除此之外,还根据战争需要提出很多的具体要求,例如不要选在水库、大桥、大寺庙、大工厂等明显目标附近;不要选在强烈地震区、滑坡地区和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地区; 应尽量利用山的阴影来破坏建筑物的阴影, 以免敌机利用建筑物的阴影做侦察对象等。在战争环境下,采取专业化和地区配套的方案能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但这种布局和建设方式对国防工业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2. 内部协作:“小而分”
在经济建设上,“小而分”与“大而全”是两种不同企业建设思路。“大而全”,就是建设全能厂、大厂的含义。这种建厂思路受到苏联影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工厂都是大型、全能的,这也影响到之后中国的建厂思路——在苏联设计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自己设计、新建的一些工厂也采用了同样一套办法。一些老企业也逐步变成全能厂([23],页344)。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开始反思苏联“框框”影响的问题,认识到这种做法“并不合乎经济核算”[24],是用落后的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进行现代化的生产。这样,就产生了采取专业化和协作的方式代替“大而全”的建设思路[25]。
按照设想,三线新建设的工厂是“小而分”,不是“大而全”,新建和扩建的工业企业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专业化和协作的方针,不再发展全能厂[23, 26],必须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少占地,少用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打破苏联落后技术的束缚”[27]。要求把三线地区的配套工厂建成,做到按大区成套,每个大区、省、自治区在战时都能够独立作战、地区配套,既有巩固的后方生产基地,又形成全国的合理布局。用“小而分”取代“大而全”,有经济建设上的考虑,显然也是战时经验影响的结果。
3. 不削弱农业:“三不、四要”
三线建设中,对于遷建、新建企业与农业关系问题,国家提出了“三不、四要”。“三不、四要”,是指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用刷锅水,不占一亩良田好地,不拆一间民房、不迁一户社员。贯彻执行“三不、四要”,体现的是工业支援农业的方针。具体要求是,在选定厂址时,要坚决改变过去在平原地区建厂规划“棋盘式”“方块块”的老框框,根据山区地少不平的特点,采取沿山就坡,按地形随高就高,随低就低的原则,进行“瓜蔓式”“阶梯式”的总体规划,宁肯分散建设,道路、管道工程绕过良田好土,宿舍建筑在荒山坡上,增加工程量,加大建设投资,也要力争少占或不占良田好土[26]。当时反复强调建设三线不能削弱农业,“三不、四要”原则反映了这种认识。搞好农业,也是为了能够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能够发展生产、坚持战争,三线地区各部门也要求严格控制从农村抽调劳动力,尽可能节约基本建设用地[22]。
4.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本是战争时代的用语。在经济建设中,这个说法是指国家建设项目集中,财力、物力使用集中。当时认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能有效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 歼灭一个少一个,歼灭一批少一批,有效地缩短战线,便于集中力量赢取时间; 可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在一个项目的建设上,也坚持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例如,上海动力机厂全部搬到重庆市郊(改名为浦陵机器厂),从迁建施工到试车投产总共只花了2个月时间,被当做打歼灭战的典型。陵川机械厂采取按工艺流程分区分批打歼灭战的方法,整个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投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取消了此前甲乙方承发包制度。建立了由建设、施工、设计等单位和地方党委组成的现场党委,实行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工负责、协同作战,也是用战时经验取代经济建设。
5. 打破常规的建设方式: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
1964年11月,毛泽东提议在召开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之前,“发动所有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28]。这个指示,拉开了设计革命的序幕。设计革命运动开展过程中,既把设计工作出现的一些问题与苏联影响联系在一起,同时开始体现“备战”为中心的思想,例如“要有战争观念”“要实行专业化和协作”等[29]。设计革命引发了合作方式的创新——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
在大协作的视角下,不同部门过去的合作方式被看作是互相等待、互相制约、互相扯皮的旧制度。按照正常的合作方式,地质部门先出勘探地质报告,然后设计部门跟进进入设计阶段,然后提出设备清单和施工图,施工队再进场施工。而按照新的合作方式,设计人员到现场和地质、施工部门三结合,实行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争取做到初步设计和地质报告同时提出,并事先向施工单位交底,为施工创造条件。设计革命倡导的“下楼出院”“三结合”等与三线建设的需求合拍,也体现在三线建设当中。不按照经济建设方式进行项目合作,而是设计人员与地质、施工部门共同合作,这种为实现急迫目标而打破条块分割的处理方式,显然也是战时经验的体现。
四 小结
在尽量短时间内实现赶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国实施赶超战略出发点是为了经济实力尽快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而防止战争保障世界和平①。然而战争压力始终伴随着中国建设,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②被摆到首要位置,中国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
在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在逐渐积累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充分借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丰富经验。三线建设开展过程遵循为战争服务的逻辑,虽然借鉴了工业化建设经验,但更主要借鉴的是战时经验,这既是执政经验的路径依赖的结果,也是由三线建设的备战性质决定的。毛泽东曾说: “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30]除了备战的逻辑,三线建设还有经济建设的目标,因而要按照经济建设的逻辑展开,还要依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累的经济建设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走过了一段从向苏联学习到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历程,也曾尝试利用科学技术赶超带动工业化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集中领导、各方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战时形成的历史经验仍是可以借鉴的宝贵财富,但存在着从战争逻辑到经济建设逻辑的路径转换问题。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曾出现过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失误的教训。在三线建设的研究中,也应从战时经验如何转换为经济建设经验的视角开展深入探讨。本文对三线建设中借鉴战时经验的特性进行了总结,认为虽然三线建设被当作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战争与经济建设有着不同要求,很难实现既加强国防又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备战压力下以战时经验开展经济建设,我国工业建设发展史中的这段艰辛历程值得总结。
参考文献
[1]陈东林. 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2]董志凯. 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10): 9—16.
[3]胡绳主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355—356.
[4]房维中, 金冲及主编. 李富春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64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4.
[6]许嘉璐.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第15卷)[C].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252.
[7]国家计委.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71.
[8]陈东林. 三线建设始末[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9]单兰山口述. 随程子华调查大西南三线建设[J]. 百年潮, 2010, (6).
[10]郭常福. 航空工业三线基地选址[A]. 王春才主编. 中国圣火[C]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36.
[11]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等机构的决定[A].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C]. 北京: 中央财经出版社, 2011. 348.
[12]朱彦云. 试论1964—1990年甘肃的三线建设及调整[D]. 西安: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16.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中国工业五十年: 新中国工业通鉴(第5部1966—1976.10)(上卷)[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48.
[14]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15]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搬迁工作分工管理问题的通知[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25.
[16]中央西北局转发1965年第一批搬迁西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名单[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09—110.
[17]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纪要[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81—191.
[18]国家经委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92.
[20]国家计委、经委关于科研、勘察设计、文教系统搬迁项目的报告[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31.
[21]川、贵、云三省1970年计划执行情况和“四五”规划几个问题汇报提纲[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266.
[22]谷牧同志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报告[A].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781.
[23]国家经委转发天津市关于设备清查试点情况的报告[A].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24]陈伯达在工业问题第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A].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438.
[25]1965年计划座谈会简报之五: 用革命的精神推行工业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A].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24.
[26]中共贵州省委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简报[R]. 贵阳: 贵州省档案馆,档案号: 61-09-544.
[27]明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方针[A].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30.
[28]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210.
[29]国务院颁发试行关于改进设计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的通知[A].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544—547.
[30]毛泽东. 搞好三线建设打起仗来就不怕了[A]. 陈夕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