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的惰性
雷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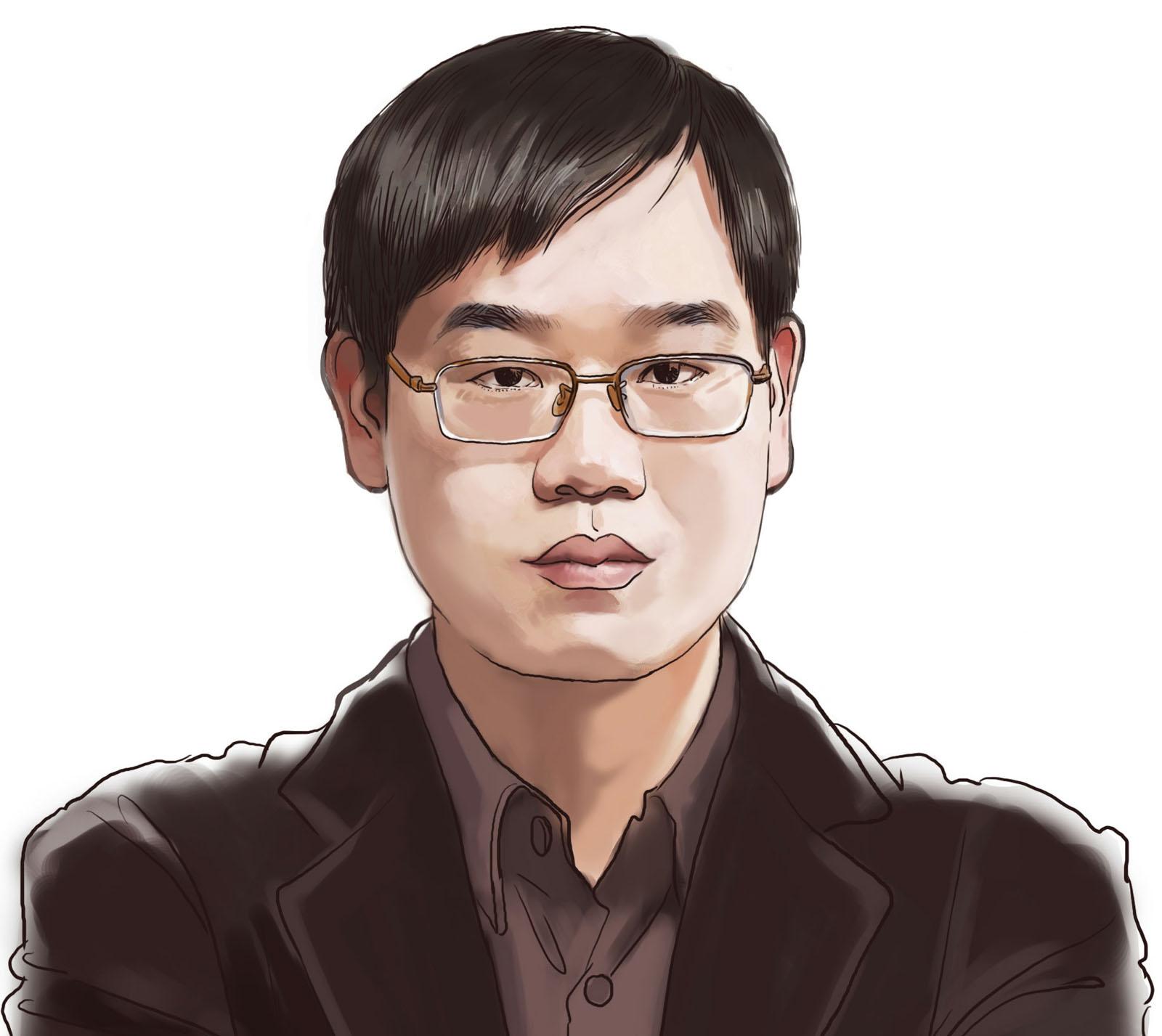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种政府“战疫”表现有差异。这种差异解读,较为流行的是以东西方政治为分界线。有人从中看到了西方政治的傲慢—以为自由民主制可以“包打天下”。我看到的是西方政治的惰性。
美国传染病学家理查德·克劳斯曾说,瘟疫的到来如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人类与瘟疫已斗争数千年,但历史地看,人类社会政治上的每一步进化,都在抵消致命病毒对人类的杀伤力。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人类社会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传染病导致千万级别人类死亡的事件。
那时的政治进化,主角是西方国家。英国19世纪中期建立全国性公共卫生体系,开创了政府治理的先河,后来成为欧洲多国政府模仿的做法。如今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都能找到“英国基因”。
后来,起引领作用的是美国。美国1946年成立的国家疾控中心,是当时世界上首个专门应对传染病流行的政府机构。目前世界上设立了疾控中心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参照了“美国样板”。
传染病防控方面的领先地位与国际政治上的主导角色相匹配,这绝非历史的巧合。从冷战后期开始,美国长期在国际防疫方面扮演领导者角色,这又与美国相比于英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含金量”更高相符合。
欧盟可以说是西方政治进化的标杆,成员国之间人员、信息、资本的自由流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划界的清晰,几乎神话为世界政治的黄金标准。这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但也是西方政治进化“停滞”的开始。
欧美成为疫情重灾区,不是自由民主制的错,但你总能看到政治认知上的惰性伤及治理体系的效力。
这种停滞在岁月静好时“不可见”,危机来临时则异常扎眼。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西方世界既不曾遭遇危及民族存亡的战争威胁,也没有出现动摇国本的国家危机。这种岁月静好孕育了政治惰性。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提了个醒,那么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则是一记重拳。
无论是带有“超民族国家”色彩的欧盟,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社会,自由民主制度都是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一个人类与病毒共存的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政府治理能力不能拖政治进化的后退。
欧美成为疫情重灾区,不是自由民主制的错,但你总能看到政治认知上的惰性伤及治理体系的效力。政治学者郑永年在分析欧洲疫情失控时写道,“对政治权力感到深度恐惧的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里孤独地死亡,也不愿看到一个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
百年前美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提出警告:“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心思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更公正与温和,而不是变得更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写道,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强大、唯我独尊乃至暴虐的政府。他所说的“现代政治”,实际上指的是“西方政治”。因为历史进入“现代”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主角。福山关于西方政治衰落的论述,何尝不是西方政治在进化上的惰性?
从政治进化的角度看,能称得上“现代”的政治,肯定是能因时因势而变、能有效治理的政治。这一点,东西方皆然。
——电影《郭福山》主题歌(男中音独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