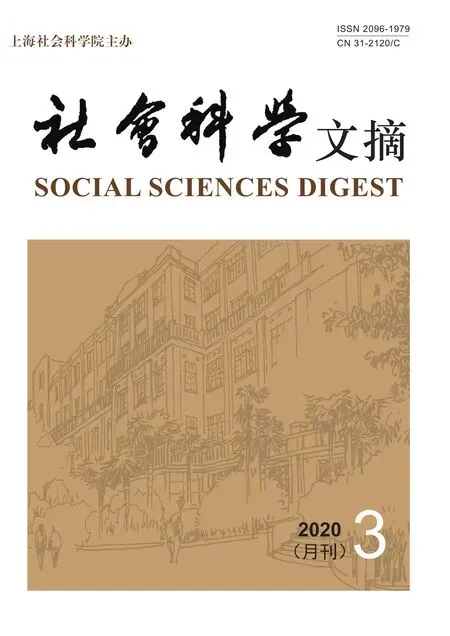对外直接投资、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
引言
2001年后我国政府开始推行支持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OFDI)的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Luo等,2010)。2013年,我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愿景,全面鼓励、支持我国企业开展OFDI。受益于我国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一带一路”愿景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由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力较低的国家跃居至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开展OFDI,表明其对国际市场的资金投入增加,这要求企业具备相应的资金支持。银行尤其是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债务融资是满足OFDI资金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Buch等,2014;连立帅和陈超,2017)。在满足资金需求的同时,债务融资会使企业面临偿债压力。当企业偿债能力不足时,违约等相关的债务风险便由此产生,而且这一问题在OFDI情形下更为严重。一旦OFDI经营失败,大量的债务融资会增加企业的偿债压力,加大债务风险。
企业的债务风险通常取决于企业的负债水平。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负债水平较高但从未违约,而负债水平较低却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形,表明直接采用负债水平衡量债务风险有其局限性,而其中未考虑企业合理的负债水平是以上局限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对于负债水平,负债水平与合理负债水平的偏离程度,即以过度负债衡量企业债务状况与债务风险更为合理。然而,已有研究仍主要关注OFDI与负债水平的关系(Lee和Kwok,1988;Burgman,1996;Chen等,1997;Park等,2013),对OFDI如何影响企业过度负债则缺少相关的经验研究。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可能承担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等政策性目标。为维持这些承担政策性目标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并促进其发展,政府会为其提供隐性担保。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政府会为开展OFDI的企业提供优惠的融资政策,如债务隐性担保等(Luo和Tung,2007;Buckley等,2009)。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可能承担上述政策性目标责任,因而也更可能享受政府的债务隐性担保等优惠融资政策(Morck等,2008)。因此,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承担的OFDI政策性目标与获取债务隐性担保程度差异会导致两者的合理负债水平不同,并进而影响过度负债。本文以2007—2015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的关系。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OFDI意味着企业会增加对国际市场的投资。除正常的投资如满足产能、客户需求与监管要求的投资,以及构建与维护生产、国际营销网络等投资外,开展OFDI的企业需要承担高额的初始投资,包括支付东道国制度、经营环境等学习与调查成本,以及外来者劣势(liabilityofforeignness)导致的前期试错成本(Johanson和Vahlne,2009)。上述投资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OFDI涉及的投资金额较大且投资时间较长,内部资金并不能满足全部融资需求,企业会寻求外部金融资源支持。外部融资来源包括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对股权再融资的限制,且多数开展OFDI的企业未在境外上市,从境内外资本市场获取股权融资的难度较大。在此情况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外部债务融资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融资方式之一,开展OFDI企业也因此较为依赖外部债务融资,而且随着企业对国际市场投资的逐渐增加,对外部债务融资的依赖程度也逐渐上升(Buch等,2014;连立帅和陈超,2017;Lian和Chen,2017)。考虑到OFDI对外部债务融资的依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还会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一方面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债务融资支持(Luo和Tung,2007;Buckley等,2009;Luo等,2010);另一方面,会改善OFDI管理体制,便于OFDI项目资金的跨境流动。自2001年提出“走出去”战略后,我国政府开始调整对OFDI的激励制度、管理体制与资金控制政策。OFDI政策的转变体现有二。第一,推出一系列OFDI的激励政策,全面鼓励与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且为企业开展OFDI提供优惠的债务融资条件(Buckley等,2009;Luo等,2010)。例如,2004年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规定,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安排“境外投资专项贷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信贷优惠利率。Luo和Tung(2007)、Morck等(2008)以及Buckley等(2009)也发现,由于我国OFDI相关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以及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银行会为开展OFDI的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伦晓波等(2018)发现,OFDI使得企业可以利用与OFDI相关的融资优惠政策,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李笑等(2019)也发现政府支持可以缓解企业OFDI的融资约束,从而促使企业开展OFDI。第二,逐渐完善OFDI的管理体制以及对OFDI项目相关资金的监管,前者从相对严格的审批制逐渐转变为相对宽松的核准制、备案制,后者则体现为完善OFDI项目涉及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资金汇出核准制度。
我国政府有关OFDI的融资优惠条件是与OFDI政策目标相匹配的,因此,根据开展OFDI与政策目标的关系,不同企业获取的融资优惠条件存在差异。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担负着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责任,因而更可能承担政策性目标。在OFDI是由政策鼓励与支持的情况下,政府更可能要求国有企业承担与OFDI相关的政策性目标责任。例如,为确保国家资源安全、提升国内技术水平,政府会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境外的自然资源和领先技术。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中承担的责任更大,更可能为此而开展OFDI(Morck等,2008;Wang等,2012)。同时,为保证OFDI目标的实现,政府也会为这些承担着政策性目标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Morck等,2008;Cui和Jiang,2012;Lian和Chen,2017)。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OFDI政策性目标责任,政府更可能为其提供融资支持。例如,在企业开展OFDI过程中,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安全给予隐性担保,并且在OFDI存在经营风险的情况下提供担保与融资支持,帮助企业渡过融资方面的难关。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展OFDI的隐性担保,其债务违约风险更低,因而同等条件下合理负债水平更高,实际负债水平偏离合理负债水平的可能性及程度更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开展OFDI时则缺少相应的政府隐性担保,当OFDI相关的投资导致企业的负债水平提高时,实际负债水平偏离合理负债水平的可能性和程度会更高。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1:相对于未开展OFDI的企业,已开展OFDI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可能过度负债。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7—2015年中国沪、深市场A股全部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首先构建了2007—2015年企业OFDI非平衡面板数据,借鉴Lu等(2014)、连立帅和陈超(2017)的研究,本文将OFDI定义为上市公司是否拥有海外子公司或联营、合营公司。如果上市公司拥有持股比例至少为20%的海外子公司或联营、合营公司,即为OFDI企业,否则不是OFDI企业。其次,参考陆正飞等(2015)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包括OFDI企业在内的全部样本,剔除ST公司样本、样本期间有息债务比率超过1的公司样本及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后,本文共获得2286家公司,共计12710个公司年度样本,其中包括3819个OFDI公司年度样本以及8891个非OFDI公司年度样本。本文中企业OFDI数据手工取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过度负债的衡量
过度负债衡量的关键在于确定合理债务水平。借鉴已有研究(Graham和Harvey,2001;Flannery和Rangan,2006;Frank和Goyal,2009;Harford等,2009;Chang等,2014;Jiang等,2017),本文采用如下分年度Tobit回归模型,确定企业的合理负债水平:

其中,t表示时间,Lev衡量企业负债水平。借鉴Flannery和Rangan(2006)研究,本文采用有息债务比率衡量。控制变量包括产权性质(NSOE)、资产收益率(Roa)、行业负债水平中值(Ind_Lev)、总资产增长率(Growth)、有形资产比例(Tang)、企业规模(Size)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模型(1)拟合出的负债率为合理负债水平,实际负债水平减去合理负债水平即为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EXLev)。借鉴陆正飞等(2015)的研究,本文还设置过度负债虚拟变量EXLev_dum,当过度负债水平(EXLev)大于0,取值为1,否则为0。
(三)实证模型设计
为检验研究假说H1,借鉴陆正飞等(2015)等的研究设计,本文采用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EXLev衡量企业的过度负债,包括连续变量EXLev与虚拟变量EXLev_dum;OFDI衡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本文从是否设立OFDI与OFDI投资金额两方面度量,包括OFDI虚拟变量OFDI1与OFDI投资金额OFDI2;NSOE衡量企业的产权性质。ControlVariables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收益率(Roa)、行业负债水平中值(Ind_Lev)、总资产增长率(Growth)、有形资产比例(Tang)、企业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比(BM)、管理费用率(EXP)、非债务税盾(NDTS)、所得税税率(ETR)、盈利波动性(VEBITTA)、现金流波动性(VCFO)与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own)。为控制年份与行业差异的影响,本文还增加了年度与行业虚拟变量。
研究结论
(一)基本结论
已开展OFDI企业与未开展OFDI企业的过度负债情况无显著差异;相对于未开展OFDI的企业,已开展OFDI非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可能性与程度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由于OFDI相关政策使得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债务担保等方面存在优势,因而开展OFDI非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可能性与程度均高于开展OFDI的国有企业。
(二)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层级与过度负债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实际负债水平偏离合理负债水平的可能性与程度均更低的原因是政府的隐性担保与资源支持等。开拓国际市场,寻求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是我国政府鼓励开展OFDI的主要原因(Luo和Tung,2007;Buckley等,2009)。较低层级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主要关注地方市场,而较高层级政府控制的企业则会关注全国及全球市场,因此,一方面,其拥有的资源更多,开展OFDI的经验更丰富,因而开展OFDI的能力更强;另一方面,在我国OFDI相关政策影响下,其开展OFDI的动机也会更强,即承担的与OFDI相关的政策性任务更多(Luo和Tung,2007;Buckley等,2009;Wang等,2012)。由于较高层级政府控制的企业承担着与OFDI相关的政策性任务,为鼓励这些企业开展OFDI,政府会要求金融系统为其提供融资等资源支持,以实现OFDI相关的目标(Morck等,2008)。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控制国有企业的政府层级越高,已开展OFDI企业过度负债的可能性与程度越低。换言之,相对于政府层级越高的国有企业,已开展OFDI的非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可能性与程度均越高。由于控制国有企业的政府层级越高,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与资源支持越多,其债务融资优势也越明显,与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缺少政府隐性担保等,实际负债水平超过合理负债水平的可能性与程度越高,过度负债的可能性与程度也越高。
(三)技术寻求型OFDI、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
Luo和Tung(2007)指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进行OFDI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了技术寻求或技术探索,以弥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提升企业竞争力。在政策层面上,我国政府亦积极鼓励企业以OFDI的形式实现技术寻求、探索。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扩大开放领域,积极有效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基于技术寻求型OFDI是我国鼓励与支持企业开展OFDI的主要目标之一,因而对于开展这一类型OFDI的企业,其更容易获取与OFDI政策相关的优惠融资条件。由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优惠融资条件,当企业拥有技术寻求型OFDI时,相对于未开展OFDI企业,已开展OFDI非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可能性高于国有企业,而当企业不拥有技术寻求型OFDI时,上述结果并不存在。
(四)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度负债的经济后果
针对2013年以来我国部分企业出现的非理性与盲目对外投资等现象,2016年11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联合表示在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将关注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债务风险问题,并对一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核实。2016年11月29日,外汇管理局率先表态,将配合境外投资相关管理部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打击虚假对外投资行为。2016年12月6日,以上四部门再次表示将关注OFDI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倾向与风险隐患,并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至此,政府部门加强对OFDI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严控OFDI相关债务风险的意图已完全明确。OFDI真实性、合规性审核的意图确定后,银行等金融机构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要求以及后续的指导政策重新调整对OFDI企业的贷款政策,例如,2017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明确要求银行业加强对于OFDI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根据以上分析,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政府部门加强OFDI审查预期会提高OFDI企业的信贷资源获取难度,尤其是过度负债水平较高的企业。同时,由于国有企业OFDI很可能是寻求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政府要求的资源,以及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获取上的优势地位,四部门明确强化对OFDI风险的监管会增加过度负债OFDI企业的融资难度,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因此,相对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非国有企业在此期间的市场反应更差。
政策含义
对于开展OFDI的非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可能导致其面临较高的偿债风险,因此,非国有企业须慎重考虑开展OFDI。政府与金融机构须强化对OFDI经营风险的监控:开展OFDI企业的债务风险需要在事前进行详细的审查、评估,并将其作为是否提供融资的决定因素;事后持续关注OFDI的经营情况,包括OFDI对企业偿债能力、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断评估债务风险,并进而确定监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