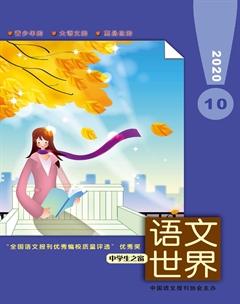秋日的从容
郑朝晖
仲秋时节,农历八月,在我看来应该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了,空气从燠热变得清冽,天空也格外高远起来。这时候,一个人坐着,静静地喝茶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发呆也自有一种清隽的意味,想起曾经走过的种种地方、经历的种种故事,有所思,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和愿望;这样的时候,内心如平静的水面上吹过一阵轻风,看不到涟漪,但是又隐隐有些摇荡的意思。古人说“秋宜怀人”,并非是说一到秋天,大家的回忆细胞就会活跃起来,而是以为在清朗的天气里,怀念也会变成一种享受。于是就想起了辛弃疾的一首《一剪梅》来。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
浑欲乘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杯且从容。
不少人以为辛弃疾大概只会写报国无门的诗词,弄到最后他写什么,大家都会往“报国无门”上去附会,一番穿凿之后,自然诗意全无。而这首《一剪梅》写尽内心款曲,很美,也很寂寞。
辛弃疾在那一年遇到了一个有风有雨的中秋,一个人端着酒杯,自然就想起了曾经的美好的中秋——有月,有花,也有酒。月光将花影倒映在了酒樽之中,再加上丹桂飘香,真的是视觉与嗅觉的美馔了。写美景,角度其实很重要,直接写明月中天,丹桂飘香,花影斑驳,自然也未尝不可,但是,作者巧妙地将这一切都收纳入那杯小小的酒中,因为有酒,自然就会联想到那个饮酒的人,在这个饮酒者的眼中,花也在杯中,月也在杯中,品酒,就是品花品月,三者纠合在了一起,相互生发,花月酒的意蕴自然也就格外凝练而醇厚了,再加上以丹桂的香气来作衬托,在词人眼中,那是一个怎样缱绻的夜晚啊。不过这样的美景,辛弃疾用了一个“忆”字,又让这一切变得邈远虚幻起来,更要紧的是这个“忆”字又带出了“今宵”的情形。今宵如何?酒还是那杯酒,但往昔的一切花月之影却都黯然消退了,只有绵密的雨丝打湿的窗棂。有了往日中秋的记忆,眼前的中秋自然就格外的寂寞与悲凉起来。其实自然界的风雨本身是没有所谓的,重要的是人的心境,此时此刻,词人的注意力都让被雨打湿的纱窗吸引了——窗,在中国古典的艺术里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既是一种阻隔,也是一种联系,那种景物本身的内在张力,让窗总有一种别样的韵味。而且,“一剪梅”的词格让结尾的兩句有一种复沓重叠的感觉,“云湿纱窗,雨湿纱窗”的吟哦中,似乎能够听到词人深深的叹息。
下阕的开首,似乎是一种勉力的张扬——“浑欲乘风问化工”,想象力在这里得到了极大地发挥,很有苏东坡“我欲乘风归去”的开张感,但是这样的张扬,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则是更为低沉的叹息:“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浑欲”,就是全身心的期盼,词人急切地期盼大自然能给自己一个回答,为什么眼前的中秋会如此寂寥如此孤独。这是对上阕中现实处境的一种呼应与承接。不过,这样的期盼,只是一种痴想而已,因为“化工”(大自然)本来就鸿蒙无迹,又到哪里去问询呢?其实人生际遇有时就是如此,起伏跌宕,一定要问清各种缘由,常常只道是惘然而已。人有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惘然中,才异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甚至人的意义恰恰不在答案的获得上,而在对这样的迷惘的真切感受之中。在这种问而不得的困境中,不同的解决方法就体现出了不同民族的个性或者说是哲学态度。比如宗教意识很强的民族,往往就可能将这种困境归结为上帝的意志,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宗教意识并不很强的民族来说,人们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归结为上帝的意志而得到内心的舒缓,相反,我们往往会以凸显生命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态度去对抗不可知的命运。“满堂唯有烛花红”——既然大自然阻隔了对于花月的欣赏,我就转而感受烛花的美好吧,词人就是如此,将眼光从对窗外景色的渴慕,转而投向室内的红烛,虽然在“唯有”之中,还有着那么一点遗憾和寂寞的意思,但是强烈的审美意愿却倔强地以反抗的姿态呈现了出来。并且,以“从容”作为整个咏叹的结尾,“从容”,是一种生命态度,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以从容的态度去对待,表现出人以自身人性的尊严去对抗命运的诡谲的努力。不过,词人用了“且”字,又增添了词句中情感的微妙性。想一想,如果将“且”换成“亦”——“歌亦从容,杯亦从容”又是怎样的情形?“且”字所陈述的并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期盼,一种要求,也隐隐有一种无奈的妥协的意味。
《一剪梅》,从感性的感伤开始,到富有哲学意味的反抗结尾,其意义大概远远超出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类的穿凿,而具有了更为普适的意义与价值。一首好的诗歌不是哲学的宣讲,但是应该足以触发读者某种哲学的联想,而辛弃疾的这首词,在这样一个寂寥的秋日里,就是这样应景地让我们认真地去思考那些超越了感伤的大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