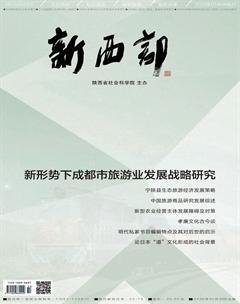孝廉文化古今谈
【摘 要】 孝廉文化是中國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先秦,发展于汉代。汉武帝确立举孝廉制度,将具有完整学说体系孝文化和行为道德概念的廉文化两者结合,配套实施。今天提倡孝文化,有利于重塑社会细胞,构建和谐家庭,改善民间风气;提倡廉文化,有利于重塑公共组织,构建得力机关,改善官场风气,调整政府行为。开展孝廉文化教育,应注意回归孝廉文化的本意:要立足于回归孝的本意,进而重新构造家与国、私与公的关系;要立足于回归廉的本意,进而树立新型的公共行为范式;形成孝与廉的恰当对接;在具体宣传教育方法上注重理性,注重学术。
【关键词】 孝廉文化;历史发展;主要内涵;当代价值
孝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孝廉文化宣传教育,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改善,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有助于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法的调整。但是,由于孝廉一词在中国古代形成了固定用法,专指汉代察举制度中的选拔官吏科目。所以,今天使用这一专用词汇时,要注意有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一、孝廉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定位
孝廉二字的含义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基本分别定型。但是,二字的含义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各有所指。
孝字很早就已经出现,《尚书·尧典》称:“克谐以孝”,意为舜的孝行可以使家庭和谐安定。《说文》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指出孝字是由半个老字和子字组合而成,其意为儿子奉养父母,上下相承。由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认同心理,并形成凝聚血亲关系的文化渊源。
廉字起源也很早,其本意为建筑物的厅堂之楞(即线条分明的仄边),《说文》称:“廉,仄也。从广,兼声。”《汉书·贾谊传》有“廉远地,则堂高”之语,注曰:“廉,侧隅也”。所以,《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有“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之语。春秋以后,廉字由棱角分明衍生出寓意耿直、正直,引申为清廉,廉洁。
秦汉以前,孝廉二字单独构词,尚未组合成一个词。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孝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了孝悌、孝友、孝敬、孝顺等解释。最常见的,是《论语》中孔子与学生之间关于孝的说明。而早期儒家的孝道思想,以处理家庭关系为核心,引申到社会关系和政治活动之中,已经有了与从政结合的迹象,由伦理原则衍生出公共准则。
廉是传统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先秦诸子中,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认可廉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值得提倡的道德标准而加以应用。但在早期儒家那里,孝与廉属于两个不同的内容。相比之下,孝是儒家文化的基石,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而廉则是从属性(从属于不同学说)的道德尺度。所以,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对孝的陈述相当多,而讲廉的地方不多。相形之下,墨家、法家谈廉要多于儒家。
到汉代,孝廉逐渐变成了选拔官吏的标准。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曾令地方“举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书·惠帝纪》),类似于今天推荐劳动模范。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下令表彰孝悌、力田、三老、廉吏(《汉书·文帝纪》)。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首次举孝廉,把孝廉作为察举选拔官员的科目之一。从此,孝廉成为固定词汇,专门用来作为推荐官员的称谓。汉代的察举制有许多科目,到东汉时孝廉成为最重要的察举科目。而且各种选拔科目,都以“孝悌廉公之行”作为基本要求。“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续汉书·百官一》注引应劭《汉官仪》)从此开始,孝廉成为选拔官吏的专用名词,一直沿用下来。
隋唐以科举制取代察举制之后,虽然孝廉作为选拔科目已经不再使用,但是,人们习惯上依然把类似的选拔方式比作孝廉。直到清代,人们在习惯上仍然把科举中的举人称为孝廉。可以说,从汉代到清代,孝廉一词,被固定作为选拔官吏的类别和称呼。
二、孝廉文化的理论体系
孝与廉在理论上是两个分立的概念。相比而言,孝有着完整的学说体系。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等文献中,关于孝有着较为丰富的解释。其最主要的含义有:①子女奉养父母。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所有这些议论,都与奉养有关。②顺从父母意志。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论语·为政》)③既要取得父母欢心,又要规劝父母从正。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儒家认识到孝行可以从家庭推向社会,并由此而促使社会的和谐。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准则,把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兄弟的友善推广到社会众人范围。他的弟子有若明确表达了这一逻辑关系。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以文学见长的弟子子夏(以西河讲学闻名,实为以事功见长),对此概括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孔子自己也这样认为,当有人问他为何不从政时,他引用《尚书》回答说奉行孝道就是从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但是,家庭關系与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毕竟有所不同。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一致的情况下,孝道可以推广到社会范围和政治领域,而一旦发生冲突,就要有所取舍。传统儒家在这一问题上,其取舍准则是以家庭关系为本。例如,当家庭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的法律关系发生冲突时,儒家主张优先考虑血缘亲情。在谈到“直”时。孔子与叶公有一个十分有名的争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所强调的是不能因为政治需要而破坏瓦解最基本的人类亲情关系。对于这一原则,孟子发挥为“窃负而逃”。孟子的弟子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回答说:“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通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大意为:舜作为最高君主,用皋陶当法官,舜的父亲瞽瞍犯罪杀人,应该怎么处理?孟子给出的方案是:皋陶作为法官应当抓瞽瞍归案,而舜不能用权力干预皋陶执法。但舜可以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自己的父亲逃跑到海滨过小日子。
汉代重视儒学,提倡礼治教化,并形成了以孝取官的孝廉一途。以后,历代王朝出于对社会细胞的重视,强调以孝治天下。有关孝道的内容被集中整理形成《孝经》,到了唐代,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孝经》作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即李隆基手书),《孝经》也被列入儒学经典。但是,无论是汉代的孝廉,还是后来的礼教,都强调在家庭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家庭关系居于优先地位。正因为家庭之孝道和社会治理之法律有可能会冲突。所以,历代统治者从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出发,承认家庭亲属关系的优先性。当家庭与政治发生矛盾时,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用非常特别的程序和方式,才能令官员为国家利益放弃亲情(夺情)。因为传统儒家认为,为维护亲情而放弃权势是符合人性的,但为维护权势而放弃亲情是违反人性的。所以,历史上的“夺情”,皇帝三番五次下令而臣下不从是正常的,臣下主动放弃亲情为国家服务则是不正常的,甚至被看做奸佞。这一内涵,是孝文化宣传中特别要注意的。
同孝相比,廉只是一个行为道德概念。《周礼·天官·小宰》有“六计”,即对官员的六条考核要求,称之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里的廉字仅仅是一种修饰词,用“廉”修饰对官员的考核要求。贾逵疏云:“廉者,洁不滥浊也。”明显带有廉字本意中的棱角、锋利含义。汉代所谓廉吏,往往明习文法,《史记·酷吏列传》的传主多为廉吏。司马迁在列举酷吏时多用廉称,如郅都(公廉),赵禹(廉平),义纵(廉),尹齐(廉武),著名酷吏张汤,尤为廉吏之表率。司马迁在列举十名酷吏后说:“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到汉武帝确立举孝廉制度,才把廉洁与孝行配套结合起来。此后,廉字的含义相当稳定,一直用于为官道德,强调清洁正直,守法不挠。
三、孝廉文化的内涵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汉代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孝廉被组合为一体。但是,其内容依然是二分的。大体上,对孝的提倡,反映出统治者对儒术的重视,以儒家学说确立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而对廉的重视,反映出统治者对法纪的强调,以精明能干的吏员推行实际政务。从而做到儒表法里,王霸兼行。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对于历史上的儒表法里,很多人只看到其欺骗性和消极面,其实不然。公正地说,外儒内法具有积极意义。它恰恰是以儒学的价值观念,去消解法家的戾气;同时以法家的威权,去克制儒学的柔弱。
正由于孝与廉内容二分,所以,从《史记》开始的历代正史,都有两种可作表率的传记,一种是《循吏列传》,一种是《酷吏列传》。所谓循吏,强调其“本法循理”,其行为是“上顺公法,下顺人情”的典范,突出其教化的一面。所谓酷吏,强调其“武健严酷”,其行为是“以酷烈为声”,“禁奸止邪”的典范,突出其法治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孝廉在汉代是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而当官的诱惑导致历史上有大量人所不齿的孝廉事例,弄虚作假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东汉王符指责当时选官的弊端道:“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潜夫论·考绩》)其中“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两句,就是对当时孝廉的批评。后人论曰:“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孝秀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审举》)
明代白话小说《醒世恒言》有一篇《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形象地描绘了东汉孝廉沽名钓誉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全是文学想象,在《后汉书·循吏传·许荆》中有明确记载。原文为:“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大意是,许武在被举孝廉后,借分家之机故意多取财物,克扣其弟许晏、许普,而两个弟弟以忍让得名,又被推举为孝廉。当两个弟弟也成名后,许武重新分家,把原来多占的财产以及产生的利益归还了弟弟。类似这种“许武教弟”的所谓“德育读本”明显有沽名钓誉之嫌,已经受到学界的质疑,需要在孝廉文化宣传教育中引起警惕。
四、孝廉文化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孝与廉在当代都有相应的价值可以发掘。但是,由于历史上孝廉一词更多地是作为察举选官的科目出现的,其含义已经约定俗成,所以,发掘其当代价值应当注意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
要准确界定孝廉的文化含义,需要把孝与廉适当分开,还原其本来意思。如果单独说孝,或者单独说廉,都不会产生歧义。一旦组合为一个词,则极有可能使稍有历史常识者将其限定在汉代的选官制度来认知。关于察举制和举孝廉的民谣,对其弊端的揭示,在中学教材中都出现过,已经广为人知。
提倡孝文化,有利于今天重塑社会细胞,构建和谐家庭,改善民间风气,调整人际行为。这一方面,近几年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
提倡廉文化,有利于今天重塑公共组织,构建得力机关,改善官场风气,调整政府行为。这一方面,近些年也有着不懈的努力。
发掘孝廉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注意孝与廉内涵的差异。“孝”可以推进社会和谐而“廉”没有这种功能,“廉”可以端正官场风气而“孝”没有这种功能。由于公共组织与家庭组织性质的不同,需要不同的处方和药剂,不可能有适用于所有场合的万能药。寄希望于由孝推演到廉,由孝推演到忠,必须立足于家国同构体。在古代,正是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构成了初民社会的初级群体,而随着部族国家的形成,由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构成了早期国家的次级群体。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路径与希腊罗马不同,夏商周三代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部族关系,扩散到大夫、诸侯、天子的“家→国→天下”统治模式之中,以家国同构的方式奠定了部族国家的基本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亲本来优于君,但随着国家势力的增长,亲逐渐让位于君。在血缘之亲让位于地位之君的过程中,父道的原则不断向社会弥散。古代的社会治理结构,就建立在这种关系上。正是这种关系,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但是,今天的国家体制已经同古代有了本质差别,所以,孝与廉的结合肯定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把孝和廉作为值得赞扬的美德加以弘扬,而孝与廉的结合配套则需要另辟蹊径。
五、关于开展孝廉文化教育的建议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开展孝廉文化教育,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立足于回归孝的本意,进而重新构造家与国、私与公的关系。要真正认识到,社会和谐和发展,必须使个人、家庭、社会形成合理的、恰当的关系。放弃以往极左年代提倡的“舍小家顾大家”、“舍家为国”等极端理念,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小家和大家、家与国具有一致性。在小家与大家、家与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能够有更近人情的取舍。通过对孝文化的宣传,不再倡导那种连最亲近的人都不顾而投入工作的行为,以家庭生活的常态化回归正常的社会秩序,进而促进并完善公共领域的行为秩序。使人们的奉献行为建立在“推己及人”的逻辑上,而不是建立在无条件牺牲的逻辑上。
第二,要立足于回归廉的本意,进而树立新型的公共行为范式。廉的本意,绝不仅仅是不贪钱、不爱财、不受贿所能包含的。所谓廉,最基本的含义是正直。这种正直,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清廉奉公,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为人正派,敢于负责,光明磊落,勇往直前。通过廉文化的宣传教育,不但反贪反腐,而且弘扬正气,消除懒惰,清理政务死角,担当社会责任,把廉政和有为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克服官僚习气。
第三,形成孝与廉的恰当对接。对孝廉文化要形成新時代的新解释,超越传统的血缘亲情圈子。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完全超越了古代,所以,在孝与廉的对接上,不再以家国同构为前提。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是立足于传统社会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和蓝图。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由差序格局走向团体格局,由等级社会走向平等社会。所以,今天的孝与廉对接,建议以儒家提出的社会交往准则“推己及人”为基本逻辑,在消极层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层面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构建出新型的适应现阶段的孝廉关系,并且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嵌合。
第四,在具体宣传教育方法上注重理性,注重学术。防止传统文化教育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再现(如弱智化的宣传画,低层次的标语口号等等,当今广为流行的二十四孝图和《弟子规》讲座等。都具有这种色彩)。真正把相关宣传和教育建立在较高层次上。
【注 释】
[1] 本文是为中共陕西省纪委和陕西省教育厅提供的关于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孝廉文化宣传教育的咨询报告.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中华书局,2005.
[2] (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
[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余华青主编.中国廉政制度史论[M].人民出版社,2007.
[5] 宋乃裕主编.领导干部孝廉文化读本[M].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
[6] 欧阳康.孝廉文化及其当代意义[M].哲学动态,2016(8).
【作者简介】
刘文瑞(1956—)男,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管理学、行政学、中国政治制度史.